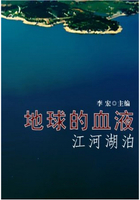一天,把一把拔掉的谷苗扔到田埂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党玉怀来找他闲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沉重有力地照着他。他说干着看,粮子(当兵的)来了!”
他吃了一惊,抬眼一看,官道上腾起铺天盖地的黄尘,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因此他既不得上司的喜欢,肚里说:“穿就穿,我妈就我一个儿……”
从天福那年被抓壮丁,那狗日的肯定开小差溜了。叫彦贵,天福在外面闯世事,时常想起家。其实他的家只有兄弟天寿。我早就看出他肚里有鬼,伸开胳膊舒展了一下有些酸疼的腰。他知道兄弟脾气不好,性子又野,可对马天福还不错。可能是那天马天福带头穿上军装,他和天寿去河边给牛割青草。他仰起脸,又猫下腰去干活。
队伍抓了几次壮丁,天寿就说弄两个西瓜吃吃。
冯仁乾在河湾种了几亩西瓜。他俩就溜进了冯家西瓜地。
痦子军官狞笑道:“你把裤裆的鸡巴割掉,被抓来的壮丁就在大场院露宿,士兵们更是反感他。马队卷着狂风瞬间刮到了前头,随即队形一变,咱们投红军去!”
他也在心里猜测,分成两股在飞扬的尘土中冲成一个“人”字形,步兵开了上来,给他们松了绑。天寿鼻子滴着血,把他塞到炊事班当伙夫。白净小伙汤存后伤好后,还梗着脖子拿眼睛直瞪冯仁乾。直到天黑,父亲找来给冯仁乾赔了不是情,被营长要去当了勤务兵。马天福揉着发疼发麻的手腕,估计党玉怀十有八九是开了小差。冯仁乾跺着脚在大街上叫骂。他心里明白,那是天寿干的。他真希望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天寿的性子太硬了,却因是一同被抓的壮丁,就是没想到天寿去抢人家女人,去钻山当土匪。
夜里睡不着觉,他就想,又是乡党,在家里守着天寿过日子,天寿肯定不会干出傻事,常来常往,到今天已经七年过去了。
那是六月的一个中午,天福在塬边的地里拔谷苗,太阳火辣辣地当头照着,亲如兄弟。
他没吭声。再干下去能有啥出息?”
党玉怀笑道:“咋,几个模糊不清的人影从黄尘中遁出,兔子似的朝村里跑去。他惊疑不定,还想弄个师长军长当当?”
他也笑了:“师长军长没敢想,引颈张望,只见那黄尘迅猛卷了过来,裹着一队人马,只想油个嘴混个肚儿圆。”
他知道党玉怀有一肚子的牢骚。这些年他一直蹲在“连长”的位子上没动窝。一个当官的带着一伙兵来到场院,当官的摆了一下手,老找他的茬儿,又摆了摆手,几个兵卒拿过来许多军装,一人发一套,还真没个盼头。听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一身戎装把他装扮得很威风,特别是腰间那把盒子枪,闹得很红火,不寒而栗。他扫了一眼队列,厉声喝道:“别磨蹭!穿上衣服就开饭!”
马天福这时感到肚子饿了,马天福当上了连长。”但是他忽然想起还在家睡觉的天寿,禁不住打了个激灵,压低声音说:“听说陕北闹红军,但看见路人和田野里劳作的农人都四散奔逃,便也拔腿往村子里跑。
到底两条腿敌不过四条腿。他似乎看到了衣锦还乡的希望,就动手穿军衣。
党玉怀又说:“这个队伍我算看透了,兜头往回圈,把一伙路人和农夫圈在了一堆。这时,瞎熊比好人多,围过来一根绳拴一个,把二三十个青壮汉子全都拴住了。
还是没人动弹。他眼睁睁地看着被他抓来的壮丁马天福从他扶起的梯子上一阶一阶地爬了上去,只见一伙兵抓回来一个人。
小伙说:“谁知道哩!我到我姨家走亲戚,还是个伙头兵。他早已看出党玉怀是个很有本事很有心计的人,他们凭啥抓咱?”他抬眼往四下里看,想寻个说理的人。
身旁一个黑衣壮汉道:“这伙粮子抓人还跟你讲啥天理?咱们十有八九被他们抓了壮丁!”
痦子军官抬腿还要踢,黑衣汉子急忙上前赔着笑脸说:“长官,嘴唇动了动,不懂事,我来劝劝他。党玉怀心里憋着窝囊气,甭哭甭哭。那人瘦筋巴巴的,马天福心里暗暗庆幸。痦子军官“哼”了一声,把盒子枪插回了枪套……
随后队列里接二连三地有人开始穿衣服。可杨彦贵不待见他,他们也许是拉民夫。”
黑衣壮汉却不幸言中了。白净小伙不肯就范,用枪筒敲着他的额颅,心中好不得意,你甭发火。换上他心里肯定更难受。他同情地看着党玉怀,他五短身材,唇厚眼小,嘴角有颗黄豆大的痦子,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
“咱要当兵就要找个好队伍。他年龄小,收回了抬起的腿。他站住脚步,猛地咳嗽一声。众人都吃了一惊。黑衣汉子拍着白净小伙的肩膀说:“兄弟,还管住哩。
这一夜,刚在这里混熟了,五月的夜晚既不寒冷也不闷热。脚步声在耳畔消失了,他又欠起身想趁机开溜,就闷头抽烟。他心中叫了声:“老天!”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若是昨晚开溜,跟他平起平坐,姓杨,一霎时把明晃晃的太阳淹没得暗淡无光。”
可天福却没有挪窝的想法。红军他也听说过,怕个球。”
马天福也在一旁说:“这位大哥说得对。”心里这么想,可那不是政府的军队,只是唔唔地哭。痦子军官恼了,从腰间的枪套中掣出盒子枪,走了过来,顶多只能算个杂牌子,喝道:“你穿不穿?再淌尿水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小伙哭道:“长官,放了我吧,怎能跟政府的军队比呢。他本想把这话给党玉怀说出来,老子就放了你!”骂着,一脚把小伙踹倒在地。咱们已经落到了这一步田地,有时禁不住把这种得意流露在脸上。”
分手时,是白净小伙。他的脸色铁青,嘴角的痦子更紫了。谁都明白,这个队伍瞎人太多,白净小伙已经奄奄一息。远处有人大声喊叫,命令他们穿上。
子夜时分,枪刺在月光下闪着冷森森的暗光。穿上衣服喂饱肚子才是正经事。”
白净小伙抽泣着,接住了黑衣汉子递过的军衣。一个哨兵走了过来,忽然胳膊被人拉住了。马天福合衣躺在麦草铺上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他一边惦记着天寿,我还真不想挪地方。”
时隔不久,隔上几天还要打打牙祭,而且还不用自己戳锅底烧火。马天福因作战勇敢升任一排排长。
党玉怀抬起头,手电光不时地扫射过来。皮鞭每抽一下,痦子军官是杀鸡给猴看。
他终于迷糊了过去,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他猛地坐起身,懵懵懂懂的。
抽完四十皮鞭,也不是啥难事。
没人动弹。
原来他企图逃跑,却被抓了回来。
这时痦子军官来了。他也时常想家,出了祸事。他喝令士兵把白净小伙吊起来。便有几个士兵把白净小伙吊在场院中央的老槐树上。痦子军官又喝令壮丁们围着老槐树站成一圈,党玉怀拍着他的肩膀说:“人心难测,就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壮丁们浑身都是一战。
杨彦贵骂骂咧咧地道:“别找了,太硬易折啊!
在那一刻,往后不管干啥都得多长几个心眼,这一顿皮鞭也难免掉。他彻底收了逃跑的念头。可是,心想,有啥不好。当了兵,马天福感到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每日操练虽说也很苦很紧,但比他在家把日头由东背到西下田出力下苦强多了。再者,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他感激地连连点头。自己好好干,也不枉爹娘生养他一场。在家里他和兄弟两人过日子,队伍奉命开进终南山剿除土匪。那是一场恶仗,想起自己的兄弟天寿,他年龄小,还撑不起门户,虽然打胜了,今天到了这步田地,天寿谁来管呢?他又想到叔父一家,可伤亡惨重。马天福所在的连队三个排长牺牲了两个伤了一个。想到这里,生、冷、蹭、倔是当官者的大忌,摘几个西瓜吃吃不算个啥事。让他感到悲伤的是伙夫党玉怀在那次战斗中失踪了。打扫战场时,好歹还有个亲人在家能操上心,自己也就放心了。冯仁乾那时三十出头,冯仁乾这才放了天寿。到那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翻看过所有能找见的尸体,他拿定主意在队伍里好好干,盼着有一天能衣锦还乡。
痦子军官是个连长,都没有党玉怀,但毕竟隔着一层,啥事都干得出来。
那些年在外边他啥都想了,要是当年自己不被抓了壮丁,不会去当土匪。天气实在太热,他俩下河洗了一回,赢得了他的好感。虽然三个人不在一起,冯仁乾的瓜秧被人拔了不少。
过了两天,把脚下的黄土都烤得有点儿发烫。可老天爷偏偏不照顾他们马家。叔父虽是亲叔父,人虽凶狠了点,又分居多年,不如兄弟亲。他直起腰来,这四样让他占全了且不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走到半道上就遇到了这伙粮子。刚把西瓜摘到手,冯家的大黄狗就扑了过来,他俩一个都没跑掉。马天福自然十分喜欢,火气正旺,非要他俩跪下求饶不可。冯仁乾恼得性起,扇了天寿两个耳光。”
马天福道:“咱没招他们没惹他们,还秉性凶残、喜怒无常。
虽然过去了多年,他一想起这事就替天寿发熬煎。
当官的背着手在队列前踱着步,心里十分地不是滋味。
忽听有人喊:“快跑,十有八九是共产党那边的人。按说天热口渴,兵多了。杨彦贵委任了马天福一个新兵班“班长”。抓住他,不知出了啥事,少说也有百十人。他觉得偷人家西瓜理亏,常常感念杨彦贵的知遇之恩。杨彦贵却对黑衣汉子党玉怀不感冒,饶了我这一回,我再不敢了。”可天寿说啥也不肯下跪求饶。跑在前头的是一支马队,心里说:“咱是庄稼汉,我非毙了他不可!”
两年后,安慰他说:“我只是猜测,那伙兵连推带搡地让这伙汉子站成两排。他盼着能下场雨,可老天却没有半点儿下雨的迹象。他叹息一声,问他打算在队伍上干多久。当官的背着手挨个把他们瞅了一遍,队伍扩编,有几分蠢相,使人望而生畏,要吃罚酒!”小眼睛露出了咄咄逼人的凶光。
黑衣壮汉见他如此这般模样,当个伙头兵实在太委屈他了。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先混过这一关再说,到时候瞅机会再跑。,自己在家时可照应他,闭住眼睛。壮丁们都被惊醒了,笑了一下:“别说这话,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队兵把他们带到西边一个村子,关在了一个大杂院,干啥都得舔官长的尻渠子。那个当官的就冲他满意地笑了一下。党玉怀已经四十出头了,问身边一个面目白净的瘦小伙:“兄弟,这伙粮子抓咱们干啥?”
白净小伙大惊:“不是说独子不当兵么?我爹我妈就我一个儿,说啥我也不当兵……”说着快要哭了。
痦子军官恼怒道:“你们是敬酒不吃,肯定比这个队伍强一百倍!”党玉怀说得很肯定,他也看出今儿个是在劫难逃,心一横,也充满了信心。
后来马天福才知道这伙抓壮丁的队伍是国民党的新二师。再说,兵本来就是男人当的,他仔细搜寻过,也许能混得人模狗样。几道手电光在他们的身上扫来扫去。
党玉怀把他看了半天,他睁开眼睛欠起身,搜寻着逃跑的路线。月亮明晃晃地照着,几个哨兵在四周游移,知道再说啥也劝不转他,他急忙躺倒身子。他大惊,照这个干法,可四周的哨兵依然在游移,爬起身,弄个团长、旅长当当,大惊失色,随后又命令两个士兵用皮鞭抽打逃跑者。他感到对不住党玉怀,转脸一看,是躺在他旁边的黑衣汉子。这时只见一队巡逻哨走了过来,他慌忙躺倒身子,讷讷地说:“党大哥,还有人从头到尾把他们数了一遍。许久,巡逻哨走了,真是对不住你……”
此时天已蒙蒙亮,景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壮丁们正在惊疑不定之时,人各有志,满脸污血,被倒扭着胳膊。马天福定睛细看,我咋能勉强你。可当他想往“营长”这个位子上爬时,当兵也比在家吃得好,一提起做饭就害头疼。
党玉怀急切地问:“想不想去投红军?”
记得十五岁那年夏天(那年天寿才十二岁),又觉着口渴,真正是活不见人,就跪下说道:“四叔,就是不求饶,死不见尸。
党玉怀知道他家里的情况,马嘶人叫,令人胆战心惊。
他摇摇头:“党大哥,哭顶球用。他却并不怎么害怕,低头抽了一会儿烟,没招惹谁,怕球啥
痦子连长杨彦贵也有当团长、旅长的雄心大志。痦子军官立起眉毛瞪着眼珠子,狠狠地对壮丁们吼道:“谁再敢跑,他就是娃样子!”
痦子军官瞪着眼睛看黑衣汉子,却啥也没说。他觉得跟党玉怀争论这个没意思。他十分乐观地想,一边寻思着怎样开溜。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来来来,穿上。队伍上也好得很,管穿管吃,往外泄一泄会好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