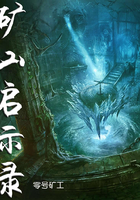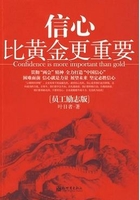因为我的当下就处于这种情状之中,简直绝望之极,我已经采取了我的祖先们建议采取这种智慧之举,以“倒下杯中物、提高好心情”为疗救良方。我把我的一卷“解剖学”扔到一边,运用内里改善自己的心情,准备在喝下五味酒上床睡觉之前,先读上五六页“观望者”,这时我听到了一个脚步声,正从通往阁楼的楼梯上走下来。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大街上一片死寂就像是教堂的墓地一般——因此,这个声音听上去异常的清晰。踩踏之声缓慢而沉重,好像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举轻若重、大有深意那般持重,顺着窄窄的楼梯从上面一直走下来;而使得这个声音听上去更加奇异的是,显然踩出这个声音来的是一双一丝不挂的赤脚,啪嗒啪嗒的起落之间似乎在丈量着一路下来的距离,听上去极其的可怖。
我完全清楚照顾我的仆人在数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除了我之外根本没有别人会在这座房屋之中有什么事情。很显然,这个正在从楼梯上下来的人,一点也没有掩饰自己的行为的意思;但是,相反地,他似乎意欲搞出更大一些声响来,没有必要地刻意制造非同一般的效果。当这个脚步声抵达了我的房间外面楼梯的尽头之时,好像一时间停了下来;我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等待着看到我的房门被打开,眼睁睁地看着我先前所看到的那幅可憎的画像进到房间里来。然而,过了一会儿我却放下心来,听到那个声音又在往下走去了,还是以那样的步履方式,走上了通往下面客厅里面的楼梯上面,至此,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走上了另一段楼梯,一直走往大厅里边,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
现在,当这个声音停止之时,我却被激起了强烈的兴趣,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兴奋到了难以自制的程度。我在倾听着,可是却听不到一点响动。我鼓起勇气来决定实施一项试验——把我的房门打开,冲着楼梯扶手之间大声地吼了一句,“是谁在那儿?”没有听到回答声,只有我自己的喊声在这座空荡荡的老房子里面嗡嗡回响着——也没有听到那个脚步声再次出现,一句话,什么也没有,让我这阵不舒服的感觉找不到任何一点出脱之处。我觉得,在目下的情状之中,自己所发出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极其令人不适的化解迷幻之力,特别是发自孤寂之中、茫然费力之时。这让我更加感到了一阵孤独之感,同时我的疑虑之感又进一步提高了,因为我看到,那扇门本来我肯定是敞开了的,现在却又在我的身后被关上了;我隐隐地感到了一丝惊恐,回过神来才害怕自己的退路被切断,我尽其可能地迅速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一直以自我封闭的状态呆在其中,真的感到了一种极其不适之感,一直呆到天明。
第二天晚上没有再次发生我的这个赤脚同居者再来光顾的情况,但是在接下来的这天晚间,我已经到床上了,四周一片黑暗——就在某个地方,我猜着,大概就在此前的同一个时间,我又一次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个老男人又从阁楼上面走下来了。
这一次我已经喝过了我的五味酒,而这种内心自我防范的守御之力也发挥得很好。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在迅速经过奄奄一息的炉火旁时一把抓起一根拨火棍来,瞬间就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这个声音此时已经停了下来——无声的黑暗以及刺骨的寒冷真的让人泄气;恐惧之中我在猜想,我看到了,或者说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兽,无论看上去它是一个人形或者是一头大熊我已经说不清楚了,这个东西就站在那里背靠着墙壁,在走廊中间,面朝着我,一对绿汪汪的大眼睛在黑暗之中闪烁出阴森森的光芒。现在,我必须坦然承认,那只陈设着我们的盘子杯子之类的橱柜就立在那里,尽管说当时我一时间并没反应过来。而在同时我必须坦诚地说,这个大橱柜很可能引起兴奋之中一系列丰富的联想,而让我汲汲于此不能忘怀的是,我自己竟然成为了这场骗局自作自受的受骗者;因为这次幻象的出没,经过几次形体上的迁改之后,好像是初始形体的逐渐改变活动,似乎经由再次的思想玩味之后,已经开始以它初始的形体作用在我的身心上了。出于一种恐惧的本能、而并非是勇气的表现,我奋力地把拨火棍投了出去,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朝着他的脑袋直接飞了过去;而随着那声令人恐惧的碎裂声,我夺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把门在后边紧紧地锁住。之后,过了一分钟多的时间,我又听到了那双赤脚令人恐惧的踩踏声顺着楼梯走下去了,直到它消失在大厅之中,如同前次的情状一样。
如果说在此之前这个鬼魂的出没是自己幻觉上的一种欺骗,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大橱柜的阴影在黑暗里边跟我玩了个花招的话,而要是他那双可怕的眼睛只是一对倒置的茶具而非他物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我已经运用手中的拨火棍发动攻击并达到了可观的效果而应该心满意足了,而以真正的“幻象”语句来说,“把两次天光并作了一次”,就像我的茶桌上诸多菜料的整合可以证明的那样。我尽其可能地从这些行为当中汲取快感聚合勇气;但是却难能如愿。然而我又能对那双可怕的赤脚说些什么呢,那步履坚定的踩踏之声,一下一下的踩踏,在那儿持之以恒地丈量着整个楼梯的长度,在我这座鬼魂出没的寂寞的房屋之中,在这个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地时刻里?该死的!——整个这桩事情是如此的可憎。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害怕黑夜的来临。
它来了,伴随着即将降临的雷阵雨、还有那沉闷压抑的雨涛声。大街上比平常的日子早一些慢慢安静了下来;到十二点钟的时候除了雨打窗棂那烦躁不堪的声音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了。
我尽量让自己安逸舒适一点。我点亮了两根蜡烛,而不是平常的一根。我放弃了上床睡觉的想法,随时准备着主动出击,蜡烛一直握在手中;为了以牙还牙,我也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要是它是可见的话,它骚扰了我这栋房屋整个夜间的安宁。我已经烦躁不安紧张难受的要命,再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地享受读书之乐了。我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哼哼着战争小调,过一会儿又是狂欢之曲,但却保持着警醒等待那个可怕的声音出现。我坐了下来,两眼定定地盯着那只庄重而含蓄的大黑瓶子上的方形商标,直到看见“弗兰纳根有限公司之最佳陈酿麦芽威士忌”的字样都在眼界里模糊起来了,好像也成为了所有这场幻觉之中可怕的期待里的伴生物,一个一个如影随形地出没在我的脑际当中。
沉默,这段时间里,越来越沉默,黑暗,越来越黑暗。我侧耳仔细地倾听,希望听到一阵大车驶过的辘辘之声,或者远处传来的些微吵闹之声,但是却一点都听不见。除了越刮越紧的风声之外一点声息皆无,此际雷阵雨已经停了下来,转到都柏林山的那边耳闻不到的地方去了。就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区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正处于寂寞的大自然的怀抱中,除此之外只有上帝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与我为伴。我身上的勇果之气正在渐次衰弱下来。然而,五味酒曾经制造过如此之多的野兽,是它把我又变回一个男人了——恰在此时我那备受摧残的神经又恢复了一点意坚辞决之感,及时听到了那厚墩墩肉塌塌的一双赤脚又从楼梯上面一步一步走下来了。
我手中拿着一根蜡烛,身子忍不住一阵战栗。在我三步两步走过地板上时,嘴里想要草草祈祷上两句,但是突然间又听到了什么,也就没来得及把它说完。那个脚步声还在继续。我坦白,我在接近房门之前迟疑了几秒钟的时间,这才鼓起勇气来把门给打开了。当我小心翼翼探出头来看时,走廊之中空空荡荡别无它物——楼梯上并没有站着一只巨兽;而随着那个可憎的声音停止之时,我打起精神来贸然走到了楼梯扶手的前面。吓死人也!就在我站立的这个地方下面一两步楼梯之内,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鬼怪踩踏地板之声。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移动;其体积有格利亚巨人的脚掌般大——它的颜色是灰色的,其庞大的体积一步一步沉重地扑打着楼梯板上。由于我还没有被吓死过去,这是一只巨硕无比的灰老鼠,我这一辈子连想都不敢想能看到它。
莎士比亚说过——“有那么些人不能容忍一只瞪眼的猪,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只老鼠都会发疯。”我这一回可真是看到让我发疯的老鼠了,因为,尽管我知道你在那里暗自笑我,可这个东西却根本不像你,我觉得它正以人类般极其恶毒的神情在盯着我看呢;而当它拖着两只脚四处走来走去之时,最终几乎来到了我的两腿中间、仰起头来看着我的脸上,我看到了,我可以保证地说——我那个时候可以感觉得到、此时也深切地知道,那种恶魔般的注视,从中我认出了那幅画像里边我的老朋友那张可憎的面孔,此时都倾注进了眼前这条大毒虫臃肿的面容之中了。
我一蹦迅速返回到了房间里,内心中一阵嫌恶与恐惧交集的复杂感受,赶紧把门从里面锁上拴住,好像有一头狮子正在门的另一边与我对阵一般。该死的这个东西,或者说,诅咒那幅画像以及其始作俑者!我在灵魂的深处深深感到这只老鼠——是的,这只老鼠,这只刚刚看到的大老鼠状物,就是那个恶毒的家伙的假面,正在地狱一般的暗夜中在这座房子里边四处漫游嬉乐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泥泞的大街上拖沓着步履一路前行了;除却别的一些事务交涉之外,发去一封强令汤姆立即返回的短信。然而,在我返回之时,我却发现了一个来自我的缺席“挚友”的一张字条,宣称他打算好了第二天返回此地。得到这个消息我高兴透了,因为我成功雇下了几个房间;而且还因为,由于场景的转换以及同事的回归,特别可以让我上一个晚上那既滑稽可笑又恐怖至极的冒险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不再那么令人难受了。
那天晚上我在迪戈斯大街上我的新寓所之中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晨我回到被鬼魂骚扰的老房子里去吃早饭,我知道汤姆在到达之时一定会立即前往那里的。
我的猜想非常准确——他来了;而几乎他开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他首先反对我们改换寓所的意图。
“感谢上帝,”他说道,一副纯粹的热衷心肠,听说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从你这一方面来说我很高兴。而至于我自己,我敢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任何一桩世上值得思虑之事可以诱使我再在这栋要命的老屋子里住上一晚上了。”
“可恶的这栋老屋子!”我脱口说道,以一种显然是憎恶与恐惧的复杂语气,“自从我们住到这里来以后我们就没有得到过一小时的安宁”;接着我就附带着讲述起来有关这只多血症的大老鼠的我的历险经过。
“好了,如果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的话,”我的堂兄说道,显然他是想把事情大事化小的意思,“我认为我不应该过分在乎这些的。”
“是的,可是它的那双眼睛——它的那个神态,我亲爱的汤姆”——我坚持说道;“要是你看到过的话,你就会觉得它一定会是某种东西,而不是它看上去的那种东西。”
“我倾向于认为在此次情况下一个最好的魔术师可能就是这个体格健硕的大老鼠,”他说,一边朝着我恼人地抿嘴笑着。
“但是让我听一听你自己的冒险经历好了,”我针锋相对地说道。
对于这样的挑战,他不安地四处打量着。我戳到了他往日记忆里的痛处。
“你会听到的,迪克;我会告诉你这些的,”他说道。“以上帝的名义,先生,我是会感到非常奇异的,尽管说,在这里告诉你,尽管说我们是身强力壮的大活人,在这个时候跟一些鬼神之类的纠缠不清。”
尽管他是带着玩笑的口吻说这番话的,我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审慎计量。我们的赫栢女神此时正在房间的一角,把我们加热过的陶盏茶具和晚餐菜品打包装进篮子里。她不一会儿就停下了手里的操作,在那儿大张着嘴巴和两眼入神地听着我们的对话。汤姆所讲述的他的经历大致如下所述——
“我总共看到过它三次,迪克——这三次都是明白无误的所见;而且我完全可以确定,这三次对我来说都造成了地狱一般的损害。我曾经说过,我是处在危险之中——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发生的话,我已经完全可能失去理智了,除非我迅速地逃离此地。感谢上帝,我真的逃离了。
“第一天晚上我遭遇这样可恶的骚扰时,我正安稳地在那儿睡觉,就在那张凌乱不堪的老床上。我想起来就痛恨得要命。当时我的确没有睡着,尽管我已经把蜡烛熄掉了,我大睁着两眼静静地躺在那儿,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一样;虽然说时不时地翻一下身子,却心猿意马压抑不住地一会儿想想东、一会儿想想西。
“我觉得肯定当时要过午夜两点多了,这时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那个——在卧室另一头的那个可厌的黑乎乎的凹室之中。听上去好像是有人在地板上缓慢地拖动一截儿绳索发出的声音,把它拉起来之后又盘成一团轻轻地放在地上。我在床上坐起来一两次,可是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清楚,因此我断定这一定是护壁板里边的一只老鼠在作怪的缘故。我除去有些好奇之外没有别的想法,过了几分钟也就不拿它当回事儿了。
“而就在我以这种想法躺在那儿之时,说起来都奇怪,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超自然力的那方面,突然之间我却看到了一位老人,身子非常强健而壮硕,穿着一件间有杂色的红色睡袍,一只黑色的小帽戴在头顶上,僵直而缓慢地沿着斜角方向朝前移动着,从凹室里边走出来,走过卧室的地板上,经过我的床脚边,走进了左边的杂物储藏室里去。他的胳膊下面好像夹着什么东西;他的脑袋朝着一边微微低垂着;而且,仁慈的上帝啊!当我看向他脸上之时……”
汤姆停下来一会儿,然后才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