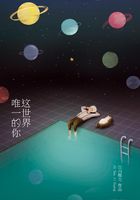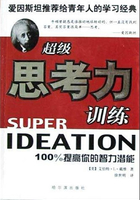岁序依旧不息地轮转。太阳还是天天从沧海升起在桑田沉没。
抚今追昔,彭德怀越发感到时候的珍贵。他本想在下面多跑些地方,然后写一份综合调查材料,经建委审议后呈报毛泽东和党中央,可是时间对于他已经变得异常吝啬,时间将宣告他重新工作的机会并不多了。
这天一大早,景希珍突然接到建委的电话,要彭德怀马上返回成熟开紧急会议,什么内容没有透露。
“什么事这么紧急,又这样秘密?”彭德怀感到奇怪。
“彭总,要不要我回电话问一下?”一直陪同视察的副秘书长杨焙也感到莫名其妙。
“既然来电话不肯告诉会议的内容,那就算了,反正到那里就晓得了。”
回到成都后,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贯彻中同《五·一六通知》。参加人员是建委局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进入后期时开始联系实际,理所当然地把予头指向了彭德怀。
大会要彭德怀做检讨,要他承认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要他交待到西南后所进行的新的“反党”活动。
会议开了1个多月。收获呢,便是拟定了彭德怀到西南后的10余条“罪状”,编印出简报,上报中央,下发各局。
彭德怀对这种以突然袭击的手法造谣生事、胡编乱造、栽赃陷害的行为,极端气愤。他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舌战群儒,没有做任何检讨。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毛主席对我彭德怀总还有一些情分呢,可这些人却毫不留情!我刚出来工作,就又拉开架势批判我来了!娘的,批吧!叫我认罪、叫我低头,无论如何做不到!休想!”他向杨焙等人滔滔不绝地发泄满腔的愤懑与苦衷,“噢,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建委的一名成员吧?为什么中央文件不发给我?我要向毛主席告状!我要给李井泉写信,不让我看党的文件是谁的决定?”
杨焙劝慰他说:“彭总,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建委为何对您这样,这是有来头的。中央文革几次打电话询问情况,让建委也很为难。上边的态度那么坚定,建委只得照办哪……所以,您思想上还是得有个准备才是啊。经请示井泉同志,现在把中央文件给您送来了,您好好看看吧!”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我早就是个败名朝野的人了,思想准备不准备都无所谓,无非是打倒了再掀起来再打倒!”
暮色四合。
他的心里就像四合的暮色一样,越发感到沉重。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双目凝滞,面色铁青,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景希珍悄悄把屋里的电灯拉亮了,他也没有察觉。他的心里依然是黑漆漆的。他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与茫然之中。
他想念自己的侄儿、侄女,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他在给彭梅魁的信中写道:
西南局在《五·一六通知》下来后,很快召开了会议,这个会的目的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揪住我不放,又在逼我,又说起了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翻起了旧帐,围攻我,让我写检讨,揭发自己,批判自己,和1959年一样,在逼我,让我承认我要翻案,我是反党分子……
梅魁你若能抽出时间的话,来成都一次,我有事给你说……
没想到就在他发信的第3天,彭梅魁已经到了成都--说来多巧啊,也许是心灵的感应吧?伯伯思念侄女,侄女也思念伯伯。伯伯给侄女写信的同时,侄女正在去看望伯伯的路上。
彭梅魁的到来给彭德怀带来莫大的宽慰!
是政治气候的骤变触动着她敏感的神经,她感到有种不祥之兆向她伯伯袭来。她实在为伯伯担心。她清楚地记得在伯伯来西南之前,她请求伯伯无论有多忙,也要半个月给她来封信,她让他们姐弟们放心。彭德怀当即不假思索地应诺下来。到西南的前几个月里,尽管视察工作很忙,他都坚持每到一地都给侄女写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亲人。可是最近一个来月,彭梅魁一直没有接到来信,她着急了,每天总要三番五次到传达室的信箱里查看,每次都失望而归。这天夜里她做了个恶梦,梦见她伯伯在视察途中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山体滑坡,崩溃的山岩遮天盖地地压了下来,她的伯伯在一片可怕的黑暗中挣扎、挣扎……她惊醒了,汗水和泪水浇了个秀湿。于是,她急匆匆买了车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现在,她端坐在伯伯面前,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但她不愿将那该死的恶梦讲给伯伯听,那太不吉利了。
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从《海瑞罢官》谈到“彭、罗、陆、杨”的倒台,从《二月提纲》谈到《五·一六通知》,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谈到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越谈越困惑不解,越变越疑窦丛生。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这场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非要发动这场革命不可呢?
父女俩谁也说不清楚。
彭德怀说:“《五·一六通知》我看了多遍。怕是觉内又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噢,新名词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凭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在中央开个会就可以解决了嘛,为什么这么上上下下大动干戈!如何解决党内矛盾,我党是有着优良传统的,毛主席不是不知道,可为什么硬要成立个高于党和国家权力机构所谓‘文革小组’,还要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当初毛主席和她结合,曾告示于她,不许她参与政治局的活动嘛!现在让她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吧,干吗捧那么高?”
彭梅魁讲了北京的形势。
彭德怀听后长长叹了口气:“唉!中国,乱套了!我是注定躲不过去了。我感觉到了,有些人总想打我的主意。俗话说,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
接着,他把话头转开了,问起他交给她的那包材料怎么样了。
那是1962年的春天,彭梅魁去吴家花园看望伯伯。彭德怀向侄女倾诉了自己“犯错误”的详细经过之后,就把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底稿,和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底稿交给了彭梅魁保管。后来,他又把“八万言书”的底稿也交给了她。他对她说:“梅魁,你是最了解伯伯的人了,你将这些材料保存好,千万别丢了,它十分重要,关系着伯伯的政治生命。问题迟早要搞清楚,没有了材料可说不清了。”
彭梅魁将材料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锁在柜子里。她没有对张春一说此事,因为她不愿意牵连丈夫和孩子。
突然有一天,彭德怀对前来看望他的侄女说:“梅魁,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的事你们没必要扯进去,你把那包材料拿回来吧!”
彭梅魁只好把材料交给了伯伯。
在彭德怀将要开赴大西南之前,他又重新把材料交给了彭梅魁。
这次,彭德怀给彭梅魁写信和彭梅魁来成都,父女俩都惦记着这包材料。
“梅魁,那包材料还在吧?”
“在。伯伯您放心。”
“好,早晚有一天能用上它。”
“我一定会保存好的。”
“这样吧,梅魁,”彭德怀又将考虑好的新方案讲了出来,“你不是来信说你妈妈老想让你们回湖南老家一趟吗?你就把那包材料带回老家去吧,这样更保险,你看怎么样?”
“伯伯,我和你想到一块去了!”
“好,梅魁,这样我就一百个放心了!”
他突然被一种浩大的激情所鼓动!
他在得到某种抚慰的同时,更坚信自己依然年轻,依然血气方刚!
--这便是他一口气读完了报纸上公布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所产生的一亢奋情绪,这种情绪犹如灿烂的朝霞在胸中鼎沸。
他突然觉得对眼前中国的这场运动理出了头绪,感到充分理解了。他眼含热泪说:“还是毛主席伟大呀!不再搞庐山那种形式,而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进行一场大运动,分清是非好坏。我赞成,我赞成!叫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他立即打电话给建委办公室,问有没有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给他的文件。
对方在回答了他没有发给他什么文件之后,建议他最好到远离都市的工厂或者农村去躲一躲,形势驿他和当权派们很是不利:大街上已经出现了“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的标语口号,一些“战斗队”、“赤卫队”正在冲击西南局机关……
谁知,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他就冲着听筒吼了起来:“岂有此理!哪有共产党干部害怕革命群众呢?只有那些做了亏心事,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人才害怕哩!我要和群众在一起,决不躲避!”
在院内忙活的景希珍听到他的声音,赶忙奔进来,一把夺下了他的电话,劝他不要发火:“看你激动的样子,好像人家欠你八百大洋似的……”
彭德怀瞪起眼珠子说:“欠了我大洋我倒不至于这样。你,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现在风声紧,叫我躲。”
“彭总,人家这是好意。现在是运动的风头,社会秩序乱了,要注意安全嘛!”
彭德怀一听,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你呀,也是‘怕’字当头!你看报纸没有?有什么好怕的?街上乱,我知道。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只有大家都说话,才有办法分清楚。你有嘴巴我也有嘴巴,最后会辩出个真理来的。让大家讲话,我们国家好多问题都能解决了……”
正当他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见”的当儿,建委办公室副秘书长杨焙悄悄进了屋。
彭德怀转眼看见他,便毫不客气地说:“噢,你来了。你是不是来通知我,叫我走开躲一躲呀?”
杨焙一脸阴云,说:“彭总,西南局情况不好啊!已经陷入半瘫痪状态。造反派勒令我们把办公楼让出来,作为他们的指挥部,一三二厂也被他们占领了。所有领导躲的躲,逃的逃。你是不是也尽快离开成熟,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地方,去川南……”
“我没说错吧,你一来准是下逐客令的。也不知道是我不明白还是你们糊涂,群众起来了有什么可怕呢?你越怕不越说明你没鬼也没有鬼吗?”
“彭总,造反派可不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呀!”
“他们是革命小将,很好嘛!我们党有缺点应当让揭!你们走吧,我不走!”
“你不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建委,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呢?走吧,彭总!”
“杨焙同志,我问你,中央派我到西南来干什么的?是叫我和大家一道建设强大的后方基地的。现在基地还没建好,就惊慌失措地溜之大吉,我该怎么向中央,向毛主席交代呢?这跟为了逃命丢下阵地有什么两样?你们都走好了,我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景希珍见秘书长说不动这个“倔老头”,就气呼呼地吐出一句:“我看你呀,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蛮干错误!”
彭德怀一听,愣了愣,没有发火,反而嘿嘿一笑说:“好家伙,你小子给我扣大帽子!哈哈,我告诉你吧,我这是革命英雄主义!”说罢,转身翻出报纸,指着上面某些被他用铜笔划了红线的条文念道:“这上面讲‘放手发动群众’,‘不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倡充分的辩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你们听听,这有什么不好?嗯?”
杨焙摇摇头说:“彭总,文件是文件,行动是行动,造反派的行动跟冠冕堂皇的文件根本就对不上号!你把事情看得太理想化了!现在可是横扫一切呦!”
彭德怀说:“可话说回来,他们真的把一切都横扫掉,躲是躲不脱的,960万平方公里,你能躲到哪儿去?”
“好好,我说不过你。”杨焙无奈地摊开双臂,转身就走。
“稍候,我还有事相求呢。”彭德怀拦住他,然后打开抽屈取出两封信,“这两封信请秘书长负责呈送一下,一封信写给建委领导的信,请批准我去看大字报,参加辩论会;一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主要是汇报我来西南后工作的情况和提出的几点建议,另外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表示赞成和支持的态度。”
杨焙接过信,沉思了半天,然后说:“好吧,我尽最大努力想办法呈上去。但有一点,在没有接到我的通知之前,你无论如何哪儿也不能!”
彭德怀随声应道:“好好,我听你的,不过你不能拖我,要尽快明确答复我。”
杨焙长长叹了一口气,重重点了点头,还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的彭德怀只不过是暂且歇个脚、喘口气的“反面角色”,导演们会随时根据剧情的需要令他立即出场。就在他津津有味地暂且坐下来观赏前台演出的时间里,幕内已经闹得纷纷扬扬、乱乱哄哄了。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在4月中旬就由康生、陈伯达着手起草了,后经毛泽东审阅并做了若干次修改之后,准备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康生就利用这个“时间差”,同江青密谋制定“从北大点火,尔后往上搞”的计划,抢先一步秘密派遣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绕过北大党委,鼓动聂元梓等人起来造反。康生在听了聂元梓政治、作风各方面都有问题的反映后说:“她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一张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北京市委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孤大字报。仅半天时间,就有上千张大字报对此进行反击或支持。当晚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在运动中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注意保密等有关规定,并且批评了聂元梓等人。然而,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们却带着几分傲慢的神采四处宣扬着“过几天你就会知道了”,使得一些敏感的人领悟到这张带有神秘色彩的大字报可能有着神秘的大背景!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仅几天时间,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进北大校园。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聂元梓成了显要的新闻人物,被无数的敬慕者簇拥着走上飞转的政治舞台。而学校的当权派、学者、专家们被毫不留情地踢了下来,推到了“斗鬼台”、“斩妖台”上,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剃“阴阳头”……
6月上旬,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面对着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提出暂时不准备返京,“请二位相机处理运动问题”。二人立即赶回北京,急忙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原校党委垮了,谁来代替领导。会议决定派工作组进校,越快越好,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将此决定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然而,***哪里知道,此决定是在蔓延的狂热情绪中点火烧油,同时也是促成他下台的第一级台阶。
7月8日,毛泽东分析了中央文革频频传递给他的情况后,在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当人们看到他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这位73位高龄的领袖更加崇拜,更加信赖。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展现出的强有力的轮廓,那挥扬万钧的手臂的线条,那明察秋毫、从容镇定的神情,那叱咤风云、善于驾驭局势的风度,使得全中国为之鼎沸。“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口号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