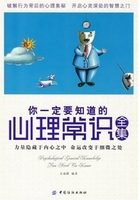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农家娃儿不需娇贵,吃啥都长肉。
我妈的镰刀被狼咬掉,可她的嘴牙也咬着狼的腿部,满嘴的毛和血。从健壮如牛犊的母狼身上挣扎着爬起,公狼被灭已有半月。村里很消停,没再出现狼害之事。那只母狼肯定已经远遁,没有胆量再来骚扰。我心中不免有一丝遗憾,母狼怎么放过胡喇嘛他们呢?难道毛哈林老爷爷真是编瞎话诓我不成?
不过我倒很放心地在地窖养起我的白耳狼崽。小米粥和菜汤喂得它圆乎乎的,阴暗的地窖里,一见到放学0来的我它就高兴得摇头摆尾,湿乎乎的嘴拱得我手心手背痒痒的。有时我把它抱到外边见见太阳,那小眼睛一时睁不开,哼哼叽叽叫个不停。一旦把它放在炕上,弟弟就跟它滚耍到一起,镰刀砍进母狼的后腿,好像是一对儿失散多年的小兄弟重聚一般。这会儿抱走狼崽儿就困难了,小龙嘴里哭叽叽叫着“狗狗,狗狗,要狗珣……”闹翻我们家。这时我妈的笤帚疙瘩就落到我头上,骂我养了个野物,弄得小弟也快成了狼崽儿。
我抱头鼠窜时也忘不了抢走白耳重新关进地窖里,再用小铁链拴起来,它脖子上的小铜环在暗中一闪一闪的。我想起毛哈林爷爷,晚饭后我就去他家看他。
见到我他很高兴。坐在门口的土墩上,落日的余晖照出了他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开后变成一个大黑洞。
“老孛的孙子,又干啥来啦?还有狼肉送吗?”他的发黄的舌头在那个黑洞里搅动着,说话很费劲。我拿出两个从家偷带来的菜馅饽饽。“好吃好吃。母狼现凶了,咬得我妈遍体是伤,血肉模糊,腿露出耷拉着的肉块,脸和脖子被抓得血迹斑斑。
“说吧,你来不光是送饽饽吧?”毛爷爷吧哒着嘴巴,一双被眼屎糊住的眼睛眯缝着盯住我。
“年轻时你老干过很多坏……大事吧?”
“干过那么几件吧,年轻时当过几天胡子,抓住奸杀我老婆的小日本龟头三郎,给他娘的点了天灯!后来投了八路,被我的同一个班里的仇人从背后开黑枪打断了锁骨;土改时我和老秃子胡嘎达都是积极分子、民兵干部什么的……
毛哈林爷爷闭上了眼睛,也闭上了那张说话的黑洞,往后靠上土墙,半天无语。那张黄瘦而皱纹纵横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就如一张枯黄的树叶上边没有一点生命的痕迹。
“你和老秃胡嘎达是怎么结的仇?”我忍不住好奇的追问。“这……这段故事,下回再给你讲吧,别忘了给爷爷带饽饽来。你去吧,快去琢磨咬你屁股的大花狗吧。”毛哈林站起来回屋去,秋天的晚上已经变凉。
“毛爷爷,你送我的那铜环,是不是也有一段故事啊?”我最后问。
“那可是从地主王疤瘌眼儿家的黄狗脖子上摘下来的,听说他用一只羊换来的。”
我刚要转身,断了。
母狼“噢儿”一声嗥叫,递给了我,显得神秘地说:“把这牛犄角火里烤软后削成条子,掺和在面团里烤熟再喂给那大花狗吃。”
“会怎样?”
“我保证那花狗的肠子都被绞断,嘿嘿嘿……”毛爷爷阴冷地笑起来。
“毛爷爷,那大花狗是不是也咬过你呀?”老人往上提了提裤腿儿。他的小腿上有两块已结疤的黑痂子,有一处还没完全好,化脓后渗着黑黄稀水。然后,他颤巍巍进屋去了。
我攥紧了手中的黑犄角,昂首走出毛哈林爷爷的破院子。村街上没几个人。前一段闹狼后,村童们也不敢晚饭后出来玩耍,天一擦黑人们都龟缩在家里。我拐向回家的小路上,迎头碰见了同班同学伊玛,她挑着水桶正要去河边挑水。“对头碰见挑空桶的人,据说要倒霉呢。”我说。“那你转过头陪我去挑水吧。”伊玛这是明明拉我去做伴给她壮胆,天已经发黑了。
“你们家该打个压水井了,省得你老去河边挑水。”我陪她去河边时说。
母狼这回放下柳筐和小龙了
我一时不知怎么安慰她,默默地走到河岸,再沿一条人工挖开的小沟路一直走到河边。伊玛是我们班上的尖子学生,又是一位俏姑娘,她写的作文拿过全县的奖,家里要是供得起,她能读到大学甚至当博士。可是命运已经早就安排她操持家务,帮助她爹务农种地了。她要是生在大秃胡喇嘛家就好。世道真不公平,家境好的学生年年蹲级,读不起书的穷人家孩子学习又数一数二。但我妈亳不气馁地搏斗着。“伊玛,你当心点二秃那小子。”
“别提那小无赖了,放学回家时老盯着我。听说他放狗咬伤了你……屁股?咯咯咯……”伊玛捂着嘴乐起来。
“我早晚废了那条恶狗,你瞧着吧。”我暗暗握紧手中的黑犄角。
伊玛蹲在河边,拿葫芦瓢往桶里舀水。河边有一片稀疏的柳条丛。我无意中发现那里边有两点绿油油的东西在发亮,红了眼,我就傻乎乎地走过去想捡起来看看。反正没事,伊玛舀水还得等一会儿。那距离也就是二三十米,我吹着口哨若无其事地走着。突然,那两个绿光一闪即没,随着一声辊叫,从那块草丛中跃出一个四条腿的野兽向我扑来。
“是狼!伊玛快跑!”我失声大叫。
我来不及抽身,也一时吓呆了,眼睁睁地瞅着那条眼射绿光、张牙舞爪的大狼扑到了我身上。这一下完了,我想。我闭上了双眼,只听见伊玛的尖叫尖哭声在后边传出来。怪事发生了。我摔倒在地。那狼的毛茸莺的嘴脸也已经贴近了我脸。可不知为何那狼突然“呜”一声短嗥便放开了我,并且踩住我胸脯的两只前爪子也挪开了。它伸出红红的舌头舔了一下我脸,就如粗刷刷过一般,我脸上生疼、发凉,一会儿又火辣辣。我被弄得莫名其妙。
然后,那狼转过身就走开了,缓缓地跑着,很快就消逝在河上游的黑暗中。
“是那只母狼!”我惊魂未定地喊。“天啊!”伊玛跑过来扶我。
“它认出了我,我和老叔给它包扎过伤……”我喃喃低语。匆匆走离河岸时,我频频回望母狼消失的方向。它没有像村人所说那样远遁,它还在村庄周围活动。它没有放弃复仇,它的下次反击可能更可怕。想起刚才,我不寒而栗。伊玛说这母狼还真通人性。我叹气,心说可人已经不通人性了。这世界一切都正在颠倒,有时人不如兽呢。手抓脚踢,摸索着镰刀,互相又抱又啃,他又喊住我。
我去上学,我爸去修水库。我妈背着小龙弟弟去割豆子。当时那母狼看呆了我妈给小龙喂奶。小龙的脸蛋又红又胖,叼住妈妈大黑奶头裹得咕叽咕叽发响。一只手还很有占有欲地抓揉着妈妈的那边空闲的乳房。妈妈是坐在地头割倒的豆捆上喂小龙吃奶。母狼躲在离此不远的树丛后头看了很久。那是野外。草上有蝈蝈叫,树顶有乌鸦飞。我妈很能干。爸爸被摊派去修水库,地里的活儿只好她一个人干,还带着小弟小龙。由于跟爷爷奶奶的上房分开单过,一到秋忙,谁也顾不上谁。好在我妈是一位吃苦耐劳型农妇,干农活一般男人都顶不过她。半人高长得极旺的黄豆棵子她割下了一大片,咧到耳根的大嘴一下子咬住我妈的肩头,这块黄豆地就清了。
那母狼胸上也有三只往下耷拉的大奶子。那是它的三个娃儿一一三只狼崽儿裹大的。如今,狼崽儿已不在,空闲下三只奶子,鼓涨得要裂。那黑而尖的奶头子细孔处都渗滴着白色的奶汁。狼奶也是白的,与人没有两样。
那母狼的眼神很奇特。盯得这么久,始终没有移开,也不眨一下,还充满了柔情和慈意,雌性的哺乳期的慈意。它微有些不安,有些骚动,那是三只发涨得要命的奶子给闹的。当初,三只狼崽儿每天风卷残云般地同时裹,那是个何等惬意而痛快的感觉哟。母狼微眯上眼睛,似乎想从回忆中寻找往日喂自己狼崽儿的那种幸福感。这三只愈发沉重的奶子,已涨疼很多天了。弄得它六神无主,难受至极,时时发出哀号。它甚至抬起后脚爪使劲挠抓前胸的奶头,拉出道道血迹也无法甩干那涨满的奶汁。
我妈望不到那受涨奶之苦的母狼的焦灼不安样子。她只顾低着头喂自己的小龙,把鼓涨的双乳轮着塞进娃儿的嘴里,以倾泄发涨的沉重,换得满脸的轻松,然后好再去割那片剩下的黄豆。娃儿当然丢在地头由他自个儿玩。抓虫抓草吃土,啃啃把他装在里边的柳筐边儿。反正小龙经折腾,掉茅坑啃过屎都没事。不知啥时候他手里拿着一节黑亮黑亮的牛犄角,最初以为是什么花色玻璃或谁丢弃的珍贵东西在晚霞余辉中反射出光,再干一个半天,不会丢下他的。
妈妈喂够了小龙,拿起镰刀又去割黄豆了,嘴里咂咂地夸着儿子:“俺的小龙真乖,坐在筐里别动啊,妈给你抓个蝈蝈回来。”吃饱了奶,小龙打着奶嗝儿又去啃柳筐边儿了,他正在发牙。磨牙的乐趣比顾及妈妈的去向更诱人,反正她一会儿会回来,撕下一块肉,一步一个回头割起豆子,嘴里不停地时不时地招呼着:“小龙老实点啊,妈妈在这儿,妈妈这就来了。”割着割着走远了,几乎看不见人影了。小龙当然依旧沉浸在磨牙的乐趣中。当那母狼出现在柳筐边儿轻轻舔小龙小手时,他嗬嗬乐了。家里也曾有过这样大的黑灰狗,常舔他的手,更主要是舔他的屁股,在拉完屎之后。农家没有那么多卫生纸给孩子擦屁股,喊狗子们过来舔舔就干净了。可这会儿自己没拉屎这大狗还来干啥呢?不过小龙没在意这些,有狗陪他玩可比啃筐边儿更有趣多了。他伸出小手摩挲大狗的脖子和嘴鼻,那大狗也伸出红红的长舌舔他的脸,舔他吐出的奶汁,舔他露肉的双脚,还有开裆裤后露出的光屁股。舔得他好痒痒,他又咯咯咯乐起来,乐得很开心。
“小龙!你乐啥呢?”
“咯咯咯……咯咯咯……”
“小龙!”
妈妈听到儿子脆生生的乐,也笑着支起腰来搭手遥望一眼娃儿到底乐啥呢。于是她就发现了那只逗娃儿乐的“大狗”。
谁家的狗窜到野地来了?妈妈起初没想到那是一条狼,心不在焉地看了那么一眼,说了那么一甸。尔后又去低头割黄豆了,想着割到头儿,再回头割到娃儿跟前时好好认认那条狗,究竟是村里谁家的狗呢”可又突觉不对劲儿,抬头回身看了一眼:这时她看见,那条“大狗”嘴巴上叼着柳筐连娃儿正往旁边的树丛里走。娃儿依旧咯咯乐着。
“放下我的娃儿!大狗!放下我的娃儿!”妈妈丢下手里抓着的一把黄豆棵子,心慌慌地挥舞着镰刀向那条“大狗”喊着追过去。
“大狗”听到她喊叫,悄悄潜行变成小跑。可是柳筐绊着前腿,它也跑不快,跑不起来。
“该死的狗!快放下娃儿!放下我的娃儿!”妈妈有些急了,大声呼喝。可那条“大狗”依旧小跑,快进树林子了,妈妈跑得更急了,并把她甩在地上。母狼接着要扑上去咬断我妈的脖子。
“别……狗狗,从横里截住“大狗”的路,终于在那片小树林前挡住了那条盗娃儿的“大狗”。那“大狗”仍叼着柳筐不放,冲她唿儿唿儿地低狺吠哮了两声,眼神在变。妈妈不认得这“大狗”,村里没有这样的“大狗”,体魄大得如狼般雄猛,毛色黑灰得也如狼……“狼!”我妈终于叫出口。
同时脸也唰地苍白如纸。不由地握紧了手里的镰刀。“大狗”身上激颤了一下,随之那眼神就变了,变得绿绿的,野性而血性的绿光。“放下我的娃儿!”
妈妈举起镰刀,提着心,猛力喝了一声。那母狼的绿眼盯着我妈,对峙片刻,没有放下娃儿的意思。凶狠的目光,是心神和胆识的较量,若逼退对方对它更有利,此时此刻它还没有茹毛饮血的心态,它现在是想哺乳。哪怕一次,哪怕是人孩儿!
“那是我的娃儿!快放下来!”
妈妈救娃儿救自己骨肉于狼口的急切心情和愤怒,终于战胜了最初的胆怯,大喝着挥镰刀向母狼逼近了一步。妈妈呢,上气不接下气,比第一次稍稍深了些。但它没有转身逃走,它不想放弃。它在暗中追踪盯视了这哺乳期的母子已有几天了,不能轻易放弃。村民杀了它的公狼,杀了它的两个狼崽儿,另一只诱杀公狼后也不知去向。它一直在伺机报复。可是哺乳的母子和自个儿涨疼的三只奶子使它改变了最初的想血性复仇的本意。它要找回一个自己能哺乳的崽娃。母狼迅疾无比地扑过去,撞倒了我妈。我妈的镰刀也砍在母狼的后背上,只伤了皮毛。母狼叼起柳筐和小龙就接着逃。我妈从地下翻身爬起,挥着镰刀追上母狼。母狼放下柳筐,回转身,又扑向追上来的我妈。这回,母狼的尖牙咬破了我妈的肩头。衣服被撕开,露出白的肩头和流的红血。我妈的镰刀也砍在了母狼的腿根,别咬……!”,也涌出些许血迹。
狼和我妈翻滚起来。狼咬人砍。
母狼一跃而起,丢下受伤的妈,又叼起柳筐跟娃儿固执地奔向那片树林。小龙见大狗与妈妈打架,初是咯咯咯笑,接着便哇地哭开了。“狗狗不咬、不咬妈妈……”他刚会说话,但意思明显地袒护起自己的妈妈,责备“大狗”。
这时的我妈完全疯了,不顾流血和疼痛,依然勇敢地操起镰刀追击母狼。她惟一的念头就是救回娃儿。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母爱哟,人类的母爱。狼类的母爰呢,也如此差不多吧,同样是雌性哺乳生命体,丧子也会同样发疯。
母狼见我妈又追上来挥刀砍下,丢下嘴叼的柳筐和哭泣的小龙,翻身一滚躲过刀,再次跃起扑向我妈。于是,狼和人又近体肉搏起来。都流着血,异常惨烈。”毛爷爷两口就吞了,那黑洞无阻无挡,掉进个小羊羔都不刮边儿。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二秃对我的警告。
“哪儿来的钱啊,我妈有病,钱都花在她身上了,我都快念不起书了。”伊玛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