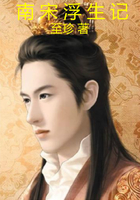有个周末,我从县城回村探家。刚进院,就听见从下屋传出咿咿呀呀的叫声。推开下屋门,见铁笼是空的,而狼孩儿弟弟则站在笼旁一个硕大的塑料盆里,爸爸妈妈正忙着给他法澡。当然脚镣和铁链还没松开。
“阿木,你回来得正好,快帮我抓着点,这小子调皮,不让洗小鸡鸡。”爸爸招呼我。他脸上身上溅满水,妈妈抓不住弟弟的两手。也许见水高兴,小龙在水盆里又蹦又跳,又叫又闹,弄得爹妈狼狈不堪。
“我来啦!我来给他洗鸡鸡!”
我从带回的兜里拿出两个大红苹果,洗了洗,过去塞进小龙弟弟乱抓的手里一手一个,又做出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嚼的样子,说:“小龙,吃吧,吃吧,好吃着哪。”
或许大漠里一块儿生死相处有印象,或许小时背他上学掉厕所有烙印,小龙见我不怎么认生和反感,嘎嘎嘎乐着,把手里苹果放进嘴里咬起来。左咬一口,右咬一口,果汁横流,可也老实多了。
于是,我就给他洗起小鸡鸡和两个腿根。其实狼孩儿弟弟身体器官都过于结实而显得麻木和迟钝,包括他的小鸡鸡。我怎么揉扯抻拉,洗洗涮涮,他似乎浑然不觉,随我玩弄。那时他的兴趣全在两个苹果上。“嘿嘿,他这小鸡鸡还变硬了嘿!”
我刚叫出口,“哧”的一下,那变硬的小鸡鸡撒出一股尿水来,正好灌进我张开的嘴里。
“哇哇!”我大叫着丢下他的鸡鸡逃走。爸爸妈妈笑得前仰后合。可撒尿的小子似乎全然不觉他的小鸡鸡在喷射,依旧吞嚼着苹果。
“真是个大尿仙!”我咔儿咔儿地漱着口,清洗满嘴的腥臊味儿。
洗完澡,爸妈又给他身上涂起一层层黄油来。“嗨嗨,家里都舍不得吃黄油,涂他身上干啥呀?”我问。村里吉亚太老喇嘛说了,涂黄油能软化他这一身铠甲似的硬皮。”爸爸说。
我一想,有道理。老喇嘛行医半辈,就这次可能说对了。小龙身上处处结着厚厚一层硬茧,有些地方蹭了一层松油桐油更是刀枪不入,可这些厚甲全封闭了它身上的汗毛孔,影响新陈代谢,影响发育,影响血液循环,容易患病,这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说的。可这些年,弟弟不照样活得挺好的?
小龙现在浑身油光闪烁,赤裸亮丽,挺着鸡鸡,毫不逊色于老在电视上露脸的黑人健美健将。我拿出向同学借来的相机,“咔嚓”一下拍下了它的这一绝世尊容,后来真成了绝版珍品。相机的闪光刺激了小龙,“嗷”一声叫,向我扑来抢相机,我赶紧逃,又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朝他扔过去,他猴子般灵巧地接住,这才平息了他对相机的追缴。他真爱吃苹果。
狼孩儿弟弟显然正在适应新生活。
也许,他感到这里不比原来的大漠古穴差,更具有丰富的食物,不再遭受饥肠辘辘之苦。他按照爸爸安排的规律生活,尽管很被动,却也很惬意。只是被牵出来放风时,他总是跑到墙角或树根下,抬起一条腿斜里撒出一汪臊尿,使得爸爸不得不当他面掏出玩艺,示范一番人类中的男性的文明撒尿方式手端尿枪,叉开双腿,向正前方射出一条弧形水线。狼孩儿弟弟果真模仿,可把那玩艺攥得紧紧的,疼得自己嗷嗷叫。爸爸妈妈让他模仿的项目不止这些,如端碗拿筷子吃喝,穿衣戴帽穿鞋穿袜;如两条腿走路,恢复上肢、手的功能等等。另外就是,教他咿呀学语。他也能简单掌握一些单词,见圆的说“蛋蛋”,见鸡便喊“鸡鸡”。有一次喊完“鸡鸡”便拔腿追过去,凶狠狠,眼红红,爸爸抓得迟了点,他早已逮住那只倒霉的鸡,咬断其脖子,血赤呼啦地生吞活剥茹毛饮血。跟家人的关系,狼孩儿弟弟总的来讲还是跟妈妈比较亲近,让她挠痒,让她梳头洗脸,喂饭喂水,较喜欢由妈妈领他出去玩。有时他的性情也变得很温和,不乏调皮,往往把裤子套在脖子上急叫,或者揪着妈妈的头发比划自己已剃成秃瓢的光头,大有惊惑之色。有一次,趁爸爸不注意,拿过他的酒壶灌了一大口,辣得他连连挠嘴打滚,逗得爸爸妈妈笑出了眼泪。他的活动范围一般限制在两间下屋和院里,只要到外边玩,都由大人牵着他的链子。
有一次正在院里散步时,从院角的地窖里传出白耳长长的狼般嗥叫。
狼孩儿弟弟的头“哧愣”一下昂起来,侧耳倾听。熟悉的嗥叫,亲切的呼唤,顿时令狼孩儿弟弟热血沸腾。他猛地一蹿,拖着后边的妈妈直奔地窖而去,同时他的嘴里也“呜呜”地发出长长狼嗥。
顷刻间,狼孩儿弟弟冲进了地窖。
拴着铁链的白耳也许饿极,也许无法忍受这寂寞难耐的牢笼生活,高扬起尖嘴狼般嗥哮着。
狼孩儿“欧、呜”亲热地呼应着,又蹦又跳地靠近过去。大有他乡遇故知,或老乡见老乡两腺泪汪汪的感觉。
可白耳不领情。它双耳直立,眼睛变红,似见了异类或怪物般,“唿儿”地一声断,扑上来就咬起狼孩儿弟弟。狼孩儿弟弟“嗷儿嗷儿”惨叫,在地上打滚。一是没有防备,二是他还不是白耳的对手,顿时肩头后背抓咬得鲜血直流。
“白耳!不许咬!快松口厂失魂落魄的妈妈惊叫着扑上去,又踢又打白耳,好不容易把狼孩儿从白耳爪下拽出去,抱着儿子痛哭起来。
闻声而至的爸爸,拿鞭子狠狠收拾了一下白耳。可怜的白耳从此更是每况愈下,在家里受尽冷落。听完这些,我扭头就跑向地窖。
茕茕孑立,皮包骨头,毛色脏秽。我已认不出白耳了。我那雄健秀美、毛色亮丽、修长身材的狼子白耳不见了,换成了一只脚脖被铁链磨破渗血,瘦弱不堪的癞皮狗。我抱起白耳热泪盈眶,嘴里喃喃自语:“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你……”
“孩子,白耳快成大狼了,它越来越野性了……”爸爸不知何时出现在我的身后。
“不,你们待它不公!你们心中只有小龙弟弟,欺负我的白耳!”
“孩子,它毕竟是狼崽儿,其实就是一条狼了,看不住就会出事的……”
“不,你说过,它是你的干儿!对我也有救命之恩!它不是狼,它是在我们家长大的好伙伴儿!”爸爸摇头,走出地窖。
我抱着白耳哭够了,起来给它拌食。白耳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看来这么多天来,它头一次吃到这么丰美的肉骨头和面汤。它不停地“呜呜”着拱我的腿和胸口,舔我的脸。
我这回真正的犯愁了。拿白耳可咋办哦。我还要去上学,不可能老守在家里保护它。家里人又不愿管它,还随时提防着它去咬伤狼孩儿弟弟。他们几次劝我把白耳送到县城公园,要不放回荒野。
可我知道,这两条路对白耳都不合适。
不过我对家人宣布,不解决好白耳问题,我再也不去上学。
爸妈的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看狼般看着我。
“阿木娃,我们没办法啊。”伊玛的爸伊尔根说。“家里穷啊,我们两口又没本事。”伊玛的娘萨仁花说。伊玛的爸瘦削猥琐,像个大烟鬼,四十多岁的人像个小老头儿;伊玛的妈“欧嘿欧嘿”咳嗽着,双颊有两块粉红晕,双眼深陷,眼珠似从脑顶冒出来,肺和气管儿的毛病害得她不像个活人,只有一口气的坟坑边的痨病鬼。我一向不大喜欢伊玛的双亲,过去很少到她家串门儿,有事都是隔墙喊伊玛出来。这次无奈,到她家来看望一下变魔怔的伊玛。可伊玛不在家。
“阿木娃,你可好好劝劝她呀……”伊玛的爸继续唠叨。
“她听你的话,你给她个痛快话,让她死心……”伊玛娘的话,刺激得我差点跳起来。他们当是我在勾着他们女儿的“魂”,甚至因为我而不嫁胡家,以至发疯。
“大叔大妈,你们胡说啥,我跟伊玛只是个好同学好邻居,没有别的……”我尽量压着内心的厌恶解释。“那更好哇,你就劝劝她……”伊尔根说。“劝她啥呀?”
“嫁胡家呀!”
“伊玛不是魔怔了吗?还嫁啥呀?”我奇怪地问。“嗨,那是一时的尖心疯,时好时坏,嫁人没问题,人家胡家也不嫌弃,反正他们的儿子也不是什么正常人,正好配对。”伊尔根说时歪歪嘴乐了,我真想一巴掌扇那张猥琐的脸。这哪儿是一个为人之父的脸。
“你还说只是个好同学,我女儿可不一定这么看。”伊玛的娘瞥我一眼,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她得病前,天天跑到河边哭,就是魔怔了以后也天天坐在那河边土坎上发呆,一坐就几个钟头,你说怪不怪?”伊玛的娘嘿嘿乐了,笑声像猫头鹰叫。敢情这痨病鬼啥都知道。我心中也不禁一颤。
“她现在人在哪儿,我去劝劝她。”我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了,站起来告辞。
“还能在哪儿?河边土坎呗。”两口子同声说出。我逃跑般走离伊玛家,到外边大口大口喘气。我先回家,从地窖牵出白耳,正好带它去河边放放风,又可给我做做伴儿。伊玛这疯丫头,别见我又犯病。
我远远看见,她呆呆地坐在那土坎上,望着秋水出神。“伊玛……”
她不看我,依旧呆望凉寒的河水。
“我是他们捡来的养女,养女……”伊玛兀自叨咕。“什么?你是他们养女?”我不知道此时的伊玛正常不正常,观察她的脸和神态,除了憔悴变瘦外,现在她还算正常,只是眼睛阴冷阴冷。
“是啊,他们去通辽看病,从医院板凳上捡回来的,我是人家丢弃的私生子。我娘压根儿就不能生育。他们瞒了我这么多年……”
“难怪他们对你这样狠!你是咋知道的?”
“我不答应他们,他们就又打又骂,说捡回来你这野种养了十七八年,该报答他们了……”
“原来真是这样。唉,伊玛,你真命苦……”我不知说啥好,也望着那秋水满肚酸楚。面对这种命运,她不魔怔也难。白耳围着伊玛转,嗅嗅闻闻,又拱拱她的膝头。过去我常带白耳,约伊玛一起去野外挖菜打柴,它跟伊玛很熟,一点儿不认生。
伊玛突然抱住白耳的头,“呜呜”痛哭起来。白耳摇着尾巴,任她搂抱亲热和发泄,显得很大度和理解。我暗自纳闷。不过,白耳在家里的待遇也跟伊玛差不多,真是一对苦命人兽。白耳伸出舌头舔起伊玛流泪的脸颊,更令她感动不已,哀泣不止。
“把白耳送给我吧!”伊玛突然对我说。“这……”我一时惊愕。
“我想有个伴儿……白耳又理解我。反正你不在家,也不需要它,你们家人也老打它,我跟它同病相怜,在一起还有个照应。连这一点你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吗?”伊玛站起来,瞪大眼珠面对着我。
“好好,先别急,咱们好商量……”我怕她又犯病,安抚着,“你这主意,倒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也正为白耳的事头疼呢。可你那宝贝爹妈同意吗?”
“会同意的。我就带着白耳嫁胡家,白耳是我的嫁妆。这是条件。”
“你还是同意嫁胡家?”
“不同意你让我嫁谁?守着这对狼心狗肺的爹娘,还真不如嫁。出去,找个汉子过自个儿的日子,嫁谁不嫁呢?咯咯咯……我一个疯子,还能嫁谁?咯咯咯……”听得我倒吸一口冷气。
我拗不过伊玛铁了心的请求。最终咬咬牙决定,暂时把白耳交给伊玛照料。我担心不答应她,又让她伤心。我再也不想伤害她那破碎的心了。而且,白耳还真有了个好着落,我不必再牵肠挂肚。一想,这还真不赖。
“好,白耳就送给你照料。你好自为之。”我由衷地说,此时此刻说什么也多余,我一个少年也无法改变伊玛的命运,惟一送给她的就是祝福了,还有白耳。
伊玛高兴之极,抱着白耳滚倒在地上,发出“咯咯咯”的爽朗笑声。白耳这么多天头一次在河滩地上如此自由地跳跃撒欢,似乎听懂了我们的决定,跟未来的女主人无拘无束亲亲热热地玩闹着,钯欢乐和快意撒满河边沙滩。
“伊玛,将来要是你真去了胡家,他们谁欺负你就叫白耳咬他们!”我说。
“我会的!”伊玛说得咬牙切齿,两眼又变得阴冷。我不寒而栗。
我此时真拿不准我的决定对还是错。第二天返校之前,我好好喂了一顿白耳,再跟家里人打了招呼,然后就把白耳牵到了伊玛家,亲手交给了伊玛。奇怪的是两边都没什么反应。我们家好像早就等待着我把白耳牵走,管它是公园、荒野或是别人家;而伊玛家,也好像早已达成协议,默默地看着伊玛把白耳牵进一个新搭的狗棚居住。
从此,人们常常看见河边沙滩上有个孤女牵着独狗溜达,或坐或躺或笑或哭,或瞅着那流逝的河水哼一曲哀伤的歌。人和狗日趋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相互照应,有时人犯病变得疯疯癫癫时,狗忠诚地守护着她,不让顽童或不轨者靠近半步,甚至把他们追得“嗷嗷”乱叫。
又过了一段时日,这孤女和独狼的身影从河滩上消失了。惟有那河水日夜奏着哀婉的曲调,哗哗唏唏地唱,如泣如诉。
伊玛果真嫁到胡家,带着白耳。
不久,她和羊痫风罗锅丈夫胡大一起承包了村里塔民查干沙坨中的野外窝棚,远离了村庄,当然也带着白耳。住进离村二三十里外的窝棚,看管村里闲散牲口,淡出村中烦人的环境,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出路。但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下边是伊玛和白耳后来遭遇的故事。有一天,他们的爹爹胡喇嘛突然跑到窝棚,躲进了狗窝。可那白耳狼狗盯得他发毛。
屁股下的干草尚软,胡喇嘛往后蹭了蹭。那白耳狼子依旧盯着他,冷冷地。他真有些发毛。莫非这东西还记得我,记得几年前的事?那一双眼白占多又绿光闪闪的圆眼,阴冷阴冷,似是两条寒极射线,把他钉在冰凉的墙角,不敢动一动。
一条铁链噼哩啪啦拴在白耳脖颈套环上,他壮着胆挥了挥手里抓到的树枝。咝一一白耳毫不含糊地冲他翻起上嘴唇,白牙利齿连红红的牙床一并露出来,发出吠哮。他身上一抖。他不再惹它,知趣地远远躲到白耳够不到的墙角。“胡大!胡大!”他开始喊叫。
长子胡大闻声出现在低矮的狼狗窝前边,嘴边还残留着白沫。显然刚犯完病,后背上鼓出的小山包,挤压着他上身几乎成九十度地面朝大地,手里的拐棍是惟一的支撑以防跌落。“爹又咋了?”
“牵走这狗东西!”胡喇嘛说。“它是个好狼狗!”
“牵走!我看着烦!老冲我龇牙,它肯定还记着以前的事!”
“不会吧,好几年了,伊玛现在训练得它像个家狗,老实又听话。”
胡大跨迸土坎,摩挲了一下白耳的脖颈。那白耳伸出红红的舌头舔起他的手。“你看没事吧,白耳老实点啊。”胡大说着紧了紧白耳的皮脖套,还有那链子。白耳现在愈发矫健,黑灰杂毛长而硬,尾巴毛茸茸地拖在地上,被伊玛调理得更具狼风。
“爹,你们到底犯啥事了?”
“你不要管,我肚子饿了,一会儿叫你媳妇送饭来!”
“出去上屋吃吧!”
“不成,那帮雷子万一找到你们这儿咋办?”胡大拄着拐棍走了。
随着一阵大咧咧的脚步声,胡大的媳妇伊玛来到狗窝前边。手里捧着一钵饭菜。人胖了许多,可魔魔怔怔得更厉害,人总处在精神恍惚状态,似醒非醒,似明不明。她有些胆怯地低着头,往低矮的狗窝里瞅。
“爹……吃、吃饭了。”伊玛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送进来。”胡喇嘛盯着白耳不敢动窝。伊玛不大情愿地猫着腰走进狗窝。这是个由原来的小羊圈改建的,上有篱笆顶,四面是土坯墙,后墙有透风的方口子,下边还铺着干草,有股刺鼻子的腥臊气。那白耳用头蹭一蹭伊玛的大腿,蹭得她好痒痒,咧开嘴露出已经黄锈斑斑的大牙,扑哧乐开了。一双吊吊的大奶,自由地颤动着,隔着单花褂子明显感觉出那波峰浪谷。老公公胡喇麻的双眼随之如狼眼般变绿了几许,死死盯起那双丰乳肥胸,燃起希望的星火。他就欣赏儿媳的这堆坠肉,一开始在她小姑娘刚发育时起就喜欢。伊玛放下饭钵子,慌乱地转身离去。“等一等”
“爹”
“过来。”
“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