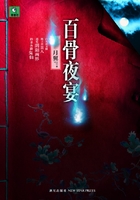狼孩儿受惊了。鼻冀扇动,嗓子眼里发出阵阵“唿儿唿儿”的声响。那一双愚鲁而阴冷的眼睛,射出两道绿幽幽的寒光,只见它猛地“唿儿”一声,张口就咬住了妈妈的手腕。妈妈没叫也没抽回手,任狼孩儿子咬着。尽管那尖利的牙齿深深咬进肉里,殷红的血顺着他牙齿渗出来,她仍然没有动,反而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狼孩儿的头和脖子,嘴里无限温存地低语:“孩子,你咬吧,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当初没能保护你,是妈妈害了你……你咬吧,这样妈的心里才好受点呵,呜呜……”她伤心地哽咽起来。
妈妈的发烫烧红的脸,紧紧贴在狼孩儿子的头上,亲切温柔地蹭动,两行滚烫的热泪“叭哒叭哒”往下掉。
一道温柔的清泉水,一丝和缓的春风吹。崇高的母亲充满挚爱的召唤:迷途的孩儿,回来吧!
两排如刀的尖齿渐渐松动,最后从那柔嫩的手腕上移开。也许,那母性的脸的亲切蹭动,使他想起了母狼那尖嘴的拱动;也许,亲生母亲的慈性的召唤,唤起了他遥远的沉睡已久的幼儿时的忆念。奇迹就这样出现了。他居然抬起半人半兽的头脸,兽性的目光变得迷惘,两个鼻孔一张一翕,伸出舌尖舔舔滴落在他嘴唇上的泪水,那张昂起的痴呆愚鲁的尖长脸,就像一个大问号:我是谁?来自何方?你是谁?你的泪水为何跟那大狼爸爸的泪水一样是咸的,我的眼泪也是咸的,为什么?你为何用脸蹭我?也是一只用脸的蹭动来表示亲热的母狼吗?自从自己的眼里第一次流出咸水起,他每每用舌尖去吸吮,获得一种乐趣。这会儿,他又伸出长长舌尖舔起这个蹭自己脸的人的泪水,一时间他那焦躁不安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安抚,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情绪驱使,他接着伸舌尖舔舐起那手腕上渗出的血迹。妈妈泪如涌泉,抱住那粗糙的头脖亲吻个不停,嘴里不停地低语:“孩子,我是你妈妈……我的儿,认出我是你妈、妈妈……”
“妈、妈……”狼孩儿艰难地吐出这字,当初大狼爸爸教的记忆突然又恢复。
一直在笼外目睹这一幕的爸爸,一时愣住了。当妈妈一扑进笼子里,他失声叫着不好,心就提到嗓子眼上,尤其妈妈的手腕一挨咬,以为狼孩儿就要上去咬断她的脖子,爸爸做好了冲进笼子抢救妈妈的准备。可眼前的事态发展,使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龙今天不同往常,开始认人了。苍天在上,这真是个好兆头。也许,小龙娃真的会很快就恢复人性,回到我们人的中间了。他的心顿时热烘烘的,自己几年来的千辛万苦的寻觅和遭受的罪过,终于将获报偿,爸爸喜上眉梢。
爸爸拿一块熟肉,递给妈妈说:“你喂喂他,接着教他说话,跟他交流。”
妈妈默默接过熟肉,送到狼孩儿儿子嘴边,亲热地说:“妈妈来喂你吃肉,好香的鸡肉哦,小龙来吃哩,你的名字叫小龙,我是妈妈,你是妈妈的小龙……”
狼孩儿或许真的饿了,咀嚼妈妈塞进他嘴里的肉,迷迷茫茫地听着妈妈的唠叨,似懂非懂,直哼哼。过了几天,他又完全不认妈妈了。
妈妈三天后再次钻进笼子里,想给他喂东西,谁料,狼孩儿小龙“唿儿”一声一下子撞开妈妈,猛地向前一蹿,张牙舞爪地跳出了笼门。幸亏,拴他脚腕上的铁链子没有松开,他“叭”地扑倒在笼门外边。
当时,正好爷爷守在下屋。家里的男人们都轮流守下屋,爷爷爸爸叔叔们互相替换,也不能耽误了地里的农活儿。一见这状况,爷爷一惊怕小龙挣脱铁链逃出去,扑过去从后边抱住他。狼孩儿弟弟机敏地一翻身,随即一只长臂伸过来,狠狠往爷爷脸上抓去。爷爷一偏头,“哧啦”一声,肩头被抓,衣服扯破,尖指甲划破了皮肉,留下几道血痕。爷爷急忙跳开去,气喘吁吁。狼孩儿弟弟在地上暴怒地蹿跳,“唿儿、唿儿”地发出吼哮,龇牙咧嘴,一张粗野丑陋的脸变得更加狰狞恐怖。那架势,谁要胆敢接近他,就咬断谁的喉咙。
妈妈的脸变得苍白。
“娘的儿,别胡闹……听话,妈妈来了,这成啥样子……”妈妈钻出铁笼子,仍想以母性的温柔来感召他,一步步靠近过去。
“唿儿!”狼孩儿小龙一声低吼,红着眼向妈妈扑来。我一把拽回了妈妈,就差一瞬间。不然,那张开的大嘴、两排利齿,定是咬住了她的咽喉。妈妈惊骇了,望着又完全像野兽的儿子,痛苦得咬破了嘴唇,“呜呜”哭将起来。
爷爷从铁笼挂钩上拿下那根常挂那儿的皮鞭,在空中挥动,咻咻作响。
“啪!”一声脆响,皮鞭抽在狼孩儿弟弟身上,疼得他“嗷嗷”嗥叫。
“回去!回笼里去!”爷爷威严地指着笼门吆喝,那根黑皮鞭像条蛇在空中舞动,发出“咻咻”的声响。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哀叫着扑上来,想夺下爷爷手中的皮鞭子。
爷爷一把推开了她。
“不用皮鞭,不拿住他,他永远是一条狼!”爷爷怒吼,把皮鞭飞舞在狼孩儿头上,咻咻发响。那狼孩儿小龙弟弟恐惧地盯着那根可怕的鞭子,两眼贼溜溜转动着,一步步后退。当鞭子再次要落下来的一刹那,他一个蹿跃,仓皇逃进笼子里去了。爷爷跟上两步,关住了笼门,滑上门闩,上了锁。
狼孩儿弟弟关进了笼子里,真成了困兽,吠哮着东撞西碰,尖利的牙齿咬着那脚上的铁链,嘎嘣嘎嘣直响。他狼般蹲坐在后腿上,愤怒地撕扯起裹在身上的衣服。那是妈妈费了半天给他穿上去的,眨眼间,一条条一片片布料扔满了笼子里。
他已经扯坏了好几身衣服了。
爷爷看一眼妈妈无血色的脸,向我示意扶她出去。我搀扶妈妈时,她那瘦弱的身子瑟瑟发抖。善良的母性的感化遭到失败,对她打击不小,一时绝望的情绪攫住了她,摇摇欲倒。我安慰她说:“妈妈,这事不能性急,弟弟现在还是半人半兽,兽性多人性少,千万急不得。他在荒野上跟母狼呆了这几年,又正好是他开始懂事的年龄,天天又吃狼奶长大,哪能一下子变成乖儿子呢,得慢慢来。”
妈妈稍稍心绪好点,说:“还是阿木懂事,幸亏妈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在身边,唉。”妈妈叹口气,垂着头,伤感地回房休息。
爷爷默默观察片刻,也退出了下屋。没有了人,狼孩儿弟弟吠哮了一阵,渐渐安静下来,卧伏在笼角。
我也一直关切着狼孩儿弟弟。这些日子从县城图书馆、新华书店,找来许多有关动物学、人类学方面的书和资料来读。资料表明,解放前我们这一带出现过两次狼人踪迹。五十年代印度原始森林捕获过一位狼婆婆,四五十岁,几十年与狼群一起生活,抓回人间后很快就死了。美国和加拿大也发生过多起与狼共度的狼人事件。
可狼人的结局一般都不妙。
我真有些暗暗为弟弟的命运担心。咱们真能够完全恢复他人性,让他完整地回到人间来吗?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人性和兽性的搏斗问题,在小龙弟弟身上体现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我还暂时不理解,不懂得那意义和道理,但那肯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人性和兽性、哲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原因导致母狼完成了小龙弟弟的人世道理以牙咬人,咬这世界,咬这人的世界。
其实,弟弟已经是人类的叛逆者。他现在拒绝文明。
爷爷端着他的烟袋,几次过来催促爸爸,赶紧送我去县城继续学业。家族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还算健全又够聪明的后辈身上,盼着我将来光宗耀祖。我去上学的日子愈来愈临近。
可有三件事,使我放不下。一是狼孩儿弟弟,二是白耳,三嘛,就是那丫头一一伊玛。不知怎么,近来不知不觉老惦记她的事,她会不会嫁那胡家羊痫风呢?大秃胡喇嘛盯上她了,她真像她所说“嫁他个头啊”就能完事吗?
这一天中午,她在门口拦住我说:“我有话跟你说,晚饭后河边见。”
还没等我吱声,她又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这丫头又遇上啥麻烦了呢?黄昏的河边静悄悄。
我如期来到我们两家一起挑水吃的河口,找个土坎坐下,秋天的艾蒿散发出一股浸肺的清香。夜鸟啁啁啼着,归人河边树,小河偶尔翻出一两声哗哗水花,不知是河鱼嬉戏还是夜燕掠水。远处突闻狼嗥,似曾相识,我不禁一抖,不会是那只老母狼吧?它应该放弃了。当时它身受重伤,或许压根儿就没能活过来。我兀自笑了。多疑。
这丫头咋还不来,整个一个敖包相会。别是涮我吧,我这哥哥可没那么大的耐心,我正想拍屁股走人,只见她沿着小路急急匆匆地赶来了。
我拿根草放进嘴里咬着,跟电影上的无聊男人们一样,歪着头看她,说:“小姐,你怎么跟那些电视上的嗲女一样考验起我的耐心哎?”
她看也不看我,坐在土坎上,嘴里说:“烦死人了,他又来了,还在我家呢。“
“谁烦死你了?谁来了?”
“你这死脑瓜,一到这时就犯傻。还能是谁,大秃子呗!”
“来了又怎样,你一说嫁你个头哦,就行了呗。”
“可我爹同意!”
“那管啥,让他嫁去。”
她扑哧一乐:“可他给我下跪,又打我……你看!”伊玛撸起衣袖,胳膊上青一道紫一道。“这一下麻烦了,你爹还是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分子有权有势,无孔不人。唉,一个小小的农民百姓哪能承担起这反腐败的历史重任呢?”
“你胡勒个头啊。人家急死了,你还寻开心!真是白当一回好同学了,狼心狗肺。”伊玛白我一眼,眼泪汪汪。我这才感到事态严重,连声道歉,听她详细诉说。考虑到一家的生活,伊玛的爸爸还有妈妈铁了心拿女儿的青舂和一生。换取家里的生活奔小康,投靠胡喇嘛这棵大树。
我跟伊玛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出逃,她舍不得病娘,先嫁个理想中的男人,可除了我她似乎还没有考虑过其他小伙儿。我当然不能为了她,把自个儿撂在这沙坨子里,那爷爷和爸爸不打断我的腿才怪。其实她都知道我的处境和状况。
“算啦,不去想它了,我死也不嫁就是了。到时候,真逼我,我就拿刀抹脖子。”伊玛的手掌往我脖子上划了一下。
“别、别,这不是你的脖子。就是你的脖子也别轻易抹掉,你这么如花似玉,多可惜。”
“你这油嘴滑舌的小子,是不是你也觉得我漂亮了吧?”说着,大胆的伊玛一下子抱住我脖子,狠狠地亲了我一下脸。顿时,我脸上烫了一下烙铁一样,火烧火燎,顿感奇妙。“你约我来,就是为了亲我一口啊?”我的心评评跳着说。“不只这些,反正我早晚是人家的人,不是嫁大秃家,就是二秃三秃家,还不如先让我自己喜欢的人摸我碰我呢……”这个大胆的村姑伊玛整个地疯了,愣在我不知所措中拽过我的手,塞进了她那半敞的内衣里头。
于是我的手抓到了两只乱跳的小兔,软软的,绵绵的。我的手一开始哆嗦着,几次想抽回来,没有成功,后来就如被磁铁吸住的矿石一样,沾在那两只小兔上不动了。
天啊,女人的胸原来这么软,这么烫,这么……还没来得及往下想,我的嘴唇上又贴上了两片嘴唇,滚烫滚烫,又湿漉漉,这疯丫头啥都会,电影电视真没有白看。我这十六岁的少年就这样一生头一次触摸了女人,吓得我心扑腾扑腾乱跳,有一种犯错误的恐惧感袭上心头。可我的血液却是沸腾着。身上有一股奇妙的感觉,简直万箭穿身。伊玛更是如醉如痴,喃喃低语,不停地催促着:“我的一切都给你,拿去吧,都给你,快点啊……”
我不知道她催促我干什么,但我的手被她的手牵着,从她胸上移向小腹,再往下。
正这时,河的上空飞过一只猫头鹰。“咕一咿一”两声瘆人的怪叫,吓得我一哆嗦,发热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的手也被蛇咬了一样,猛地抽回来。
“对不起,伊玛,咱们不能这样……对不起……我永远记住你对我的这份情……”我慌乱地说着站起来,如一罪犯逃离现场一般,拔腿就逃向家里。
我身后传出伊玛扑在地上抽泣的声音。我已经没有勇气回头再看她一眼,头也不回地跑着,如被狼追着屁股一样。回到家时,妈妈看见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说:“撞见鬼了,孩子?吓成这样,刚天黑啊!”
“撞见了活鬼,女鬼,舌头又红又长,差点活吞了我。”我定了定神,走向屋里。
“那女鬼不是西院的伊玛那丫头吧?”妈妈神秘兮兮地说。“你咋知道?”我一哆嗦。
“知子莫若母嘛。你刚去河边,她也过去了嘛。你可当心点啊,人家可是胡大村长看上的儿媳妇哟,你别蹚这浑水。你的媳妇啊,在大城市楼里住着呢……”妈妈冲我刮刮脸,兀自进下屋看狼孩儿弟弟去了。
几天后,我就离开村庄去了县城。
一个月后,家里人来县城看我时说伊玛疯了。
我的心猛地一抖。唉,伊玛这丫头,没能扛过去,真命苦。
我心中几多怅然,一丝酸涩,还有股说不出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