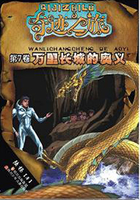5月15目,毛泽东就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事实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全党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分子遥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总批判修正主义。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此后,即在个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由于运动中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作为军事医学科研领域的最高学府,军事医学科学院也就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灾区”。一批资深的医学科研人员因发表不同意见、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在学术研究上持有不同观点,皆被当做“右派言论”、“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学术权威向党进攻”等罪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
盛志勇感到惊异,感到困惑,感到优虑,无论怎么想,一时间也弄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尽管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但他还是弄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也曾带着这个“疑惑”去询问过副院长沈克非,而沈克作的“疑惑”比他还重。沈克非说,也许天晓得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搞运动,我们的外科学研究和外科队伍就功亏-篑,就拖垮了,就完了!
但这话只有他两人一块说说,若被传出去或被人窃听到打了“小报告”,两个人无疑都会打成“双料右派”。
盛志勇说,既然弄不明白,那就保持沉默,叫开会就开会,叫学就学习。即使有时间也不敢看书,尤其是一些外文资料和业务书刊,惟恐被划到“那边”去。
沈克非说,这个问题就留给政治家们去解决吧,等运动一过,我们还要惨淡经营我们的“生意”。眼下就沉默,井水不犯河水。忍着点,等着吧。
二人相视无言。
反右整风整了一年多,令人惊诧的坏消息不断传来:许多地方部门和高等院校都挖出了“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
紧接着,是北京大学批判该校校长马寅初。先是《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竹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继而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批判。随后在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而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在北京大学宣称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史加激烈、升温,并撤销了马寅初的北大校长职务。
对马寅初的批判成为全国反右斗争的一个“样板”,各地的反右斗争也骤然升级,各地也都在揪大大小小的马寅初式的人物……
笔者最早听到“马寅初”的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一篇批判《反动人口论》的文章中。那时刚念初中,稍谙世事,虽然对马寅初的人口论不甚了了,但对领袖的教导“此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一脍炙人口的语录耳熟能详,只是对人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干活等问题想得太少,甚至没想。到了80年代,人们又提起马寅初的人口论,并且流行这样一种假设:当初要是听了马寅初先生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这么多亿人,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等问题就不会面临今天这样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七八亿人来享用现在的国民经济总收入要比今天的12多亿人来花销要松快得多,这就好比三个人的饭五个人来吃……对这种假设,我似乎是在人们的附和中表示认同,无疑,这是一种长期教化与陶冶的结果:人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有意无意地发现,“大脑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于是,人们从不敢思考变得不再思考或懒得思考,人脑的功能似乎只限于接收与记忆,不再用于思考与输出。久而久之,便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主见,这些大脑要么成了一张白纸,写上什么就是什么;要么是一种复印件,人家说个什么,你就出个什么。这一切似已过去,其负面影响却是久远的。
而这一次听盛老提及“马寅初”的名字,不由使我想起在最近的一本《书摘》杂志上看到的马寅初先生写于50年代末的《附带声明》,这是对那场针对他的政治讨伐的勇敢回答,文章仅有1500来字,却是字字铁骨,句句热肠。如文章中小标题所说: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接受挑战,当是丝毫不让,据理力争,铁骨自在;马寅初言表感谢,更是晓情明意,有分有寸,热肠袭人。他的慷慨陈词,读之无不令人佩服其不屈权势,为真理而战的豪气与胆魄;他的肺腑衷言,更叫人见出先生“友情重,真理尤重”的执着精神。他在文中写道:“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会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伹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承担一切后果……”文章的最后一段更让人过目难忘,感慨万端:“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总的劝告,心中万万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两段文字“情、理、义”倶在,读后,任何一个稍有良心或良知的人都会通过先生简朴而真诚的文字把握到一个高贵的灵魂,并会于不知不觉中抬起眼眉,肃然仰视,有如面对一种精神,面对一座高山。他的思想是一座山,他的人格也是一座山,两座山重叠出的冯寅初先生,孤傲而又孤独地标示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的精神高度,岌岌然,巍巍然,让活着的与将要出世的人们高山仰止。
……
就此打住。我们再追随着盛老的思绪,把镜头转向“那个时期”的上海。
在上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揪出的马寅初式的代表人物是吴之理。
吴之理先是受到批判,随之被撤销其第二军医大学校长职务及兼任急症外科医院院长职务,后被发落到空军某单位去广。
又换了一个校长,据说是位老红军。这位老红军校长目台后,首先挥起的权力之刀,就是把急症外科医院给砍了。他认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医务太忙了,而军事医学科学院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嘛,为啥子非要两家掺和在一块,搞啥子急症外科呢!有这个必要吗?
于是,经这位领导这么一句话,就把刚刚创办三年的上海急症外科医院取消了,从此再也不复存在了。
“很可惜,很可惜啊!”年过八旬的盛志勇教授大脑中蝉翼般闪现着当年急症外科医院创建时的繁忙之景和被取消的冷落之景。
当初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医院?
因为打仗。
从朝鲜战争来看,我们的军事医学没有治伤的经验,在参加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中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战伤。以后再发生战争你怎么办?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那些受伤的战士因得不到很好的救治而死去吗?
盛老的情绪有些激动。但他努力克制着:摆摆手、摇摇头,继而哈哈一笑了之。这时你会发现,他的克制力特别强,而克制力来自于一个人的忍耐能力。
忍耐,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久经历练的品质。
5.历史的选择
1959年国庆前夕,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前来参加中华人医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一天上午,盛志勇突然接到通知,参与一位意外受伤患者的会沴治疗。
患者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同事们猜测着。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重要人物究竟是谁。
盛志勇在没有与患者见面之前也不知道接受治疗的患者究竟是谁。
他甚至跟家人没来得及打声招呼,就匆匆赶到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会诊室为患者医治伤情。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患者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在一次意外交通事故中黎清毅不慎腿部受伤骨折,盛志勇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及时赶来为他治疗。
已是9月下旬,离国庆庆典的日子越来越近。
周恩来前来医院看望黎清毅副总理时,对盛志勇和治疗小组的医生们寄予厚望:要尽一切所能,保证黎清毅副总理能够不失外交礼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
时间紧迫。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显然遇到严峻挑战。
这位越南的副总理说,机会难得,就是拄着拐杖或者坐轮椅,也要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中国盛大的节了庆典,以表达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祝愿。
根据他的骨折伤情,即使经过十分有效的治疗,恢复得很快,也不可能在几天之内痊愈。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拄着拐杖或者坐着轮椅上天安门城楼;盛志勇和治疗小组的同志们立下诺言:10月1日,人们将会看到这位越南的副总理和其他友好使者一起,迈动着双脚一步一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先进行消肿、消炎、化瘀治疗,时后对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加固护理。
盛志勇说,时间不允许他和同事们对这位富有特殊使命患者的这条腿束手无策。
三天后,瘀肿已消退。
黎清毅急着下床在地板上踱步。显然,被加同护理的腿脚迈起步来不那么灵便,一拐一拐的……
为此,盛志勇想了各种办法,为他赶做了一双具有保护性的特制鞋。黎清毅穿上感到非常舒适,也非常满意。
10月1目,黎清毅穿着这双特制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后,黎清毅回医院继续治疗,他十分感激地对盛志勇说,这双鞋完成了它的使命,我想把它留作纪念。
半个月后,黎清毅的腿伤已基本治愈。盛志勇遵照周恩来的嘱托,亲自护送他回越南。黎清毅给周恩来发报对中国医生表示感谢,并祝愿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笔者在采访盛志勇教授时,出于对他职业的“情感流向”的探寻,特别留意他为越南副总理治伤的这个鲜为人知的经历。因为关键人物总是关键时刻的历史见证人。
这在盛志勇教授的档案里并无记载。
我想是否与后来发生的某种“历史原因”有关而被“忽略”了呢?
然而,在盛老十分清晰的记忆里,历史事件和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生动地呈现在你眼前,尽管他叙说得很简练,甚至“一言以蔽之”。直到后来他踏着硝烟到“自卫还击”的南国边陲抢救伤员,他对“友谊”的理解更多了几分珍视和体恤。
历史的选择,总是有着偶然和必然的联系:
1961年4月,盛志勇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任创伤外科、烧伤科主任。
啊,敬爱的盛老,您当时是否理解,这个历史的选择,对您的人生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