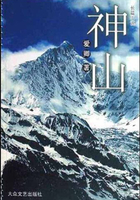韩春旭的《人类的童年》,是文学家以最生动的笔触所写的“人类学生命学”论文;是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文学伟大而光荣的一个例证。文学的生命无处不在,关键是文学家是否自觉地担负了责任与使命。
《人类的童年》如果作家读不出它的意义,人类学家(生命学家)肯定会读出它的价值;如果后者亦疑惑不解,那么,不甘堕落的生命会读懂它。
“甲虫”会读得懂,因为它经受了变异的痛苦。
12.猪与佛性
去山西的路上,周晓枫问我,“你知道猪的‘三大理想’么?”我自然不知道,便向她请教。她笑而不答,在她随身带的小本子上飞快地写了几笔,递给我。上写:
圈栏全拆掉,天上掉饲料,屠夫死翘翘……我莞尔一笑,“这是人性,而不是猪性。”
她也莞尔一笑,说:“你一点也不懂幽默。”
我并不反驳,因为我知道,不懂幽默就是幽默;在别人超常思维的时候,你固执地坚持你的惯性思维,便产生了差异,幽默便小请自来了。
“三大理想”全是人的视角,是人的自由观、幸福观和生活观;它一切均以自我为中心,不含“责任感”、“使命感”的词根。体现着人的贪婪、任性、专制及人的好逸恶劳、一相情愿。
于是我说:“对于猪来说,所谓自由,真不如一泡新鲜的人粪。”
晓枫听之,笑得细眼更细,像新生儿,难以面对突如萁来的人世间的那第一缕阳光。嘴上却说:“你这个人很鄙俗。”
在我的家乡十渡,我曾对祝勇、彭程和晓枫讲过猪的事情--在京西,猪栏与人厕是建在一起的。当人人厕之时,猪会闻讯赶来,仰视着厕卜那或尖或圆、或黑或白的两瓣臀尖,一旦有物质产下来,猪便接而食之,是不做片刻思量的。猪幸福地享用着,像人的盛宴。这与猪性无关:是由饲养者的物质基础决定的。苦涩的树叶,干涩的谷糠,总比不得人粪来得鲜润和腴厚。
这合理的存在,却使晓枫做了一个颇不合情理的决定:“我以后再也不吃猪肉了。”
当时我想,猪一生随遇而安,庸福自享,无命运感,有一种与生即来的佛性,乃佛性天成;而人的佛性,是源于禁忌,比如得知猪食人粪之后而不吃猪肉。
晓枫是个独特的作家,她的一本《鸟群》,让我耽读不已,曾对友人说:“怀抱‘周晓枫’,夜不能寐。”
她的独特,就在于由绵密的比喻所凸显的修辞性。正如她自己在《锦鲤》一文中所说:“我一意孤行,已是积习难改。热爱修辞,嗜好优美的形容词和新奇的比喻……通过比喻,我洞窥造物主省力的设计原则,与万事万物之间奇妙而秘密的勾连。而今,我发现自己对应着一个喻体,那便是锦鲤。装点着一身斑驳的词语鳞片,使我区别于其他朴素的鱼……”于是,她出奇地计较文字的最小的计量单位:词。以致于在日常的对话中也是“词”话连珠,美不胜收。比如她介绍自己:“我是看上去很不正经,其实是假不正经;有人表现得很正经,其实是真不正经。”这就为她过于别致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听者便只能倾听,而不好反驳。所以,跟她谈话,往往是她已“汪洋恣肆”了,你还在“目瞪口呆”--在她面前,聪明人也变得很弱智了。
在太原,我和祝勇、周晓枫除了游览了晋祠、平遥古城等著名名胜以外,还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文物点--太山寺。这就给了我一次意外的发现--太山寺位于晋源镇西的风峪沟北向的山腰间,始建于唐景云元年(710年),原为道教庙宇,后改为佛寺。这出景观尚在开发之中,游人甚希。我等到后,见寺门紧锁,仅几个民工在开凿道路。周晓枫是一个很会跟生人打交道的人,她居然说动了一个老者,给我们开启了一处庙门的锁。庙门一开,使我们震惊不已:那里保存着未被“修缮”的唐代悬雕,是从未见到过的文物真迹。我们有福了!老人可能正患着重病,因为他在我们身边呻吟不止。
我被深深打动了,轻轻对晓枫说:“是不是给他一点钱?”“不可以,那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她制止了我。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了了,沉迷于对占物的欣赏。不经意间,见晓枫在主佛前轻轻跪下,虔减地拜了几拜,然后往古旧的“功德箱”里放了两张钞票。老者轻声问“您是居士?”晓枫一笑,不置可否。老者被感动了,给我们打开了所有庙门的锁。我也被深深打动了,但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她的做法是与佛的境地相和谐的,无声最好。但我毕竟发现了她的另一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现代女性,竞有这么丰沛的佛性--如果佛足善的话,那么她的祭善,实为善际,即:善对所遇到的一切。
这一发现,使我顿然理解了她的写作--她虽然很重修辞,但不能就据此而说她是形式主义的作家。她是参透了现代人的“时尚化”本质,即:易于感受外化的东西,对于无法外化的事物很难予以接受。而事物的本质性因素往往是很难被外化的,这成了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障碍。
周晓枫用文字,挑战了这种障碍--她用绵密的比喻将事物无法言说的部分层层“外化”,变成能被常人把握的形象。所以,她的文字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放大”功能。即:隐而显,微而著;从无形,到有形。这类似菩提树下的佛禅之道。
她太体贴她的读者了,她进行的是一种佛性的写作--由己心到人心,由己悟到他悟,由惠己到惠人。她是一个精神的“引渡者”。
所以,猪的佛性虽然天成,去过于“无心”,无心便无为,无为便无用。虽然不贪婪、任性、专制,但猪还是猪。
13.山村踩响的犬吠
刘利华是我的一位友人。他将诗集《黑月亮,白月亮》赠我,感到五内热络。读了他的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不禁吃了一惊:我是一个山里人,他也是一个山里人,而且他比我还“山”,口音总是在“山音”与“京音”间打摆,却写出了那么“洋气”的诗,感到人主观的神游是束缚不住的,可以超越地域、时间和已有的生存状态。
他的爱情诗,写的不是在爱情中沉迷时的那种甜蜜的小感觉,而是对爱情的审视、剔滤,在人生况味这一层面上,冷静地“浸入”爱情。
夜晚,我走在没有灯光的路上;假如有一个女人;能同我一起走这段路;那我肯定会爱上她;这段路;就会像一支烟;越吸越短;很香甜;也提神儿。
(《走在没有灯光的路上》)
这是一种深厚的人生体验,只要你上了三十岁,就会体会到。那个女人,在男女小温情中是个女人,在人生的漫漫大途上,就是一个符号:任每一个旅人填进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内容。还有他的“冬天里想一个人/如同/赤裸裸地立在雪地上/想一件棉衣”(《冬天里想一个人》)更是如此。以往的体验,思念是一种黄昏情绪,无奈、忧伤而美丽,作者却把它叠印在棉衣的意象上,如稻草一般,招摇在雪中的裸人的面前。棉衣之于裸人,是残酷的生存层面上的关系;那么,思念还是一种小忧伤么?
很少有人这么些爱情啊!
之于诗,我是个极主观的人,认为:读太斑斓太飘忽的诗没意思,读太直白太媚俗的诗又不如躺在床上想心思。这里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诗的意象不能飘忽不定,或过于纷繁。飘忽不定是过度的朦胧,是障眼法,它遮掩诗的苍白和空洞。它不让你体会明白,你拿它没办法,那么还是早一点走开为好。其二,诗不能缺少含蓄。
直白的诗句,正如过清的河流,无鱼摇尾,无意蕴涵泳,莫不如自己想人非非,自己制造出一点心跳的境界来。殊不知,不扰人的自娱,也是一种高品位啊。
断言之,前者是作者缺乏自信,没话找话;后者则是作者瞧不起别人。均是缺憾,让人叹息。
利华的诗,正是在这二者之间,作了恰切的把握,在写法上,既意象清明,又用语含蓄;既可读懂,又回味不尽。
“你的身影/碎成了离别时的笑声/播进我的心/落地生根/生成一株含笑的树/每片叶子都静默/等待着”(《树》)。这是写分离,但分手却并末一了百了,走了人的身影,在留住者心中长成了一棵树,生无法铲除的根。
人就是这样,简单又深刻。“树”的意象单纯清明,与人的心对应得准,使读的人认可。但这又是怎样的一棵树啊,谁也一下子说不清楚,诗便活了。还有一处,我久久注目,甚至想把那诗句后的余音用散文写出来。便是《少女》一诗的结句:“你踩响的犬吠/渐渐静下来。”这是极具张力的诗句。回溯:以前的十六行诗,无一处描绘少女出逃的氛围,而“踩晌的犬吠”却让人想到少女的出逃之于山村,是一件多么不可以承受的大事件啊。前瞻:犬吠虽“渐渐静下来”,但天边的夜色又把少女重重包裹起来,少女的命运便多么令人牵肠挂肚!我们希望,少女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好丈夫,这个丈夫是个被人遗弃过的大她十岁的一个市政工人。他每天只要下了班,便匆匆地回到家,狼吞虎咽地吃她作的饭,然后用满脸的胡子茬扎她,听她咯咯的欢笑。千万不要找一个比她小的小白脸,“乱”了她的青春之后,再将她抛弃,那么,她便只有走回头路。这是题外话,因为诗的作用,使我忍不住地说了出来。
利华的诗会唤起人们良知上的自觉。
他的爱情诗,又一个不能不淡的特点,便是自身的冷静。用诗评家张同吾的话说,便是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没有直接地表现出“我”的爱情感受。这未必是缺点,表现出他的成熟与自持。但作为朋友,这是不町容忍的:对爱情的体味,对女人的感受,是朋友走近朋友的通幽捷径啊。
是山人的根性,使你摘不下人格的面具还是怕老婆?怕老婆的诗人,活得累啊!
14.纯粹精神的呼唤--读《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
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之后,韩春旭以她特有的灵魂拷问的方式,向我们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栽《当代》2000年第二期)韩春旭的这声呼唤显得异常残酷--在人们耽于世俗的美好和享乐的迷幻,自我感觉良好地迈向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却听到了这惟一的一声理性而真实的诘问:这一声诘问,让聪慧者先醒--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并不曾给我们带来内心所需的真止的幸福。我们生活在虚妄和自欺之中。
于是,韩春旭发出的,便是一种世纪诰问,旨在让人们匆忙地向21世纪迈进的时候,在门槛前稍稍停顿一下,作一番理性的自审之后,找准落脚的方位。韩春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深情的人文关怀,是一种冲破女性固有的褊狭的自爱自怜之后的人间大爱。
韩春旭的人文关怀,是建立在她多年来一贯的理性思考之上的,这有她发表的一系列与精神大师对话的长篇思想随笔为证。她洞悉了人类思想进化与演变的生命流程,她从人类思想大师那里探寻并构筑了自己观照人类生活的理性坐标。
韩春旭对20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论述,是准确而深刻的--准确得让人无法辩驳,深刻得令人悚然自惭。
人要活得自尊、自知,必须要有这种自惭;正如一个有羞耻心的人,做了错事会脸红一样。这种自惭,是一种反思的姿态,是健康人性的标志。而韩春旭关于“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的诘问,就在于要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就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来讲,通过反思,我们不难看出,在前半个世纪,压迫与专制,剥夺了人们实现“自我”的权利;“自我”的获得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理想,为之追求和奋斗了漫长的岁月,并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所以,权力话语对“自我”的剥夺,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正由于剥夺的强制性,引起了人们本能的反抗,演绎出了人类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一曲曲慷慨悲歌。因此,人们痛苦着,却也悲壮着,崇高着,幸福着。到了20世纪末,权力话语给予“自我”以相对宽松的机制保障,而物质话语却乘隙而入。物质主义迎合了人们的肉体欲望,在消费享乐中,人们的个性自觉慢慢被腐蚀了;人们不战而降,于不自觉之中,惭惭被“物化”了。所以,抵抗物质话语对“自我”的侵蚀较反抗权力话语对“自我”的压迫更难,这需要人们有高度的自制与自警。
那么,到了世纪的交替之处,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便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话题--人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21世纪,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世纪!
如何拯救?
韩春旭说--人类的肉体与人类的精神重新整合,将是新世纪的新人道主义的内容;人类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灵与肉高度统一的原则,在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到一种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在物质相对发达,亦即肉体的需要得以较为充足的满足之后,21世纪的人类,必须向精神化的生存方式倾斜。
她说,人活得什么都有,但却没有幸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人只给了肉体的安享之所,却没有构建灵魂的栖息之地,灵魂无所附依,怎能不焦灼不安。而且,“人”的确立,人与人高贵与卑贱的划分,乃至富有和贫穷的实质意义,就在于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精神(灵魂)生活决定着并支配着人类高低贵贱的肉体。“自我”的实现,关键的不在于肉体的宴饮,而在于精神的自足。
解读韩春旭的文本,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偏执的空洞的泛精神主义者,她主张建立一个不割裂灵与肉和谐关系的“精神生命体”。
在20世纪末,读到韩春旭的《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焦躁滞浊的内心,不禁生出一份满足,一份清明,一份宁静,一份和谐,一份庄严,一份崇高和一份希望。我感到,韩春旭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人类精神的呵护者,一个精神使者和圣子。从她的文字里,我生出一种压抑不住的感动,汨汨地在周身的血管中欢快地流淌,不由得喊出了一个响脆的声音:
精神万岁!
15.南迁嘉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文坛的喧哗还是那么的嘹唳,但实际支撑着京城文坛,并给京城文坛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足“新文人”群体的随笔创作。这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新文人”的写作,具有“符号价值”,或者说,具有“符号作用”。
符号作用,便是代表性作用。
而在这个“新文人”写作群体中,伍立杨是面旗帜,是个灵魂人物;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以文字,一以为人。
伍立杨具有极强烈的“读书情结”,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可以毫不做作地品藻出钱钟书、余光中、董桥与李敖的学问与文字的可圈点处,可见他学问的广博与深厚。
他在对中外文化传统的长久迷恋中,培养了自己勃郁的“文人情怀”。竹林七贤的放诞,谢灵运的山水情怀,太白的高标,东坡的旷达,李笠翁的情调,袁子才的性灵,济慈的夜莺般的快乐,契河犬的从容与洞彻……均在他心中激起了梦幻般的向往。文章之中的“诗酒精神”被他看成是“浮世的迷醉”,对文字的深情成为“骸骨的迷恋”;他把思想的专断视为“精神的阉割”……他“活在文字中”。
是文字给了他人性的滋润,是文字给了他灵性的自由,也是文字给了他人生的坐标--所以,文学是他的生命所在,他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世界。
因而,他创造了一种只属于他的,优异卓越的文体--新艺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