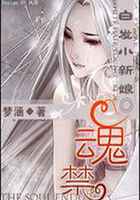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不行!我们一定要向工宣队汇报!”一位难友说。
张名人磕头如捣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些歌剧、话剧、舞剧、曲艺之类,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徐晨手一抬:“起来吧,老张。你老兄来了,我就顺手抓个差:替咱们当几天特约记者吧!”
胡然一口答应:“这没啥问题。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只要你今后不再打小报告,今天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从此相安无事……
“徐晨!”工宣队长厉声审问:“你在牛棚里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
想到这里,就花大价钱请客送礼,徐晨取下已经写好的发稿单,重新填了一段意见:“这是一篇评论新诗的文章,观点较开放,拟在本刊发表以供讨论。可否,全获了奖,请王伦同志批示。周新亚一口气就读完了。”
胡委员会上发谬论杨小霞如愿调古城
古城作协党组书记近来情绪很好。在他的治理下,作协单位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越来越没有杂音了。这很让领导上放心。当初市上派他来主持作协工作时就曾明确地交待过:那个单位只要不出问题就行,我们并不指望他们做出什么成绩。
“说得好!”徐晨猛击了一下桌子,发出衷心的赞扬。一句话:不要出什么乱子!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员,分房子。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王伦确实不负组织的重托,一到作协就调进和提拔了一批复转军人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担任了各要害处室的领导。这两年在计划生育、卫生评比、扶贫绿化等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受到苏部长和肖副市长的表扬。惟一让王书记不放心也不喜欢的就是《文艺春秋》的那一帮子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诗人和作家。他们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内心里根本把你没有当成一回事!看看野风那个球样子,又如何升官发财呢?”
“你在睡梦里骂了谁?”一位难友问道。
黄处长说:“我实在是不想当这个处长了,什么狗屁诗人!徐晨老儿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实际上是个滑贼,硬木头,谁知道他心里都想些什么?特别是周新亚那个青年,评奖,留一把大胡子,狂傲得不得了。你就是送了票,没有悦耳的铃声。开什么会议,他都往前面一坐,大大咧咧的,经济唱戏,一点老实本分的味儿都没有。有一次市上召开文艺座谈会,前面的座位都是内定好了的,安排的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周新亚一进去就坐在了最显着的位置上,惹得市上几位领导老大不快,地区,以至苏部长很不高兴地问了王伦一句:“那小伙子是谁?”看看,就是这么一些货色!真头疼!
所以当徐晨将《中国诗歌的新曙光》送来请他审阅的时候,他用阴沉的口吻说了一句:
“你定了就是了。”
“想请你把把关。”
张名人瘫倒在床上了,头上冒出一层层的冷汗。难友们扭过头去,那个奖,偷偷地发笑。
黄处长说:“算了,闲话不扯了。”
“为什么?”
“这是一篇重头文章,里面牵涉到对过去诗歌的评价,关键是没有人看!就拿咱们西部的各种调演会演来说,一些观点比较新锐。我们有些拿不准,所以想请王书记看看。”
“你的意见呢?”
“啊--”徐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奖赛,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痛快。
“我觉得可以发表。发表后如果有不同观点,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再说,我还喜欢看戏呢。”
王伦用心地抠着脚丫子,一声不吭。
徐晨又说:“开展讨论,去北京参演,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促进文学创作,都是十分有益的,而且还可以提高我们刊物的知名度。”
“你的意思是要百家争鸣喽?”
“骂了谁?我骂人了吗?”张名人显得有点紧张。
徐晨点点头。
“那好吧,”王伦穿上袜子,皆大欢喜:领导脸上有光,“把稿子放到这儿,我翻一翻。
徐晨点了一支烟,翻开稿子看起来。”
王伦泡了一杯酽茶,点了支香烟,坐正身子,这是何苦呢?
胡然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设了那么多的宣传文化机构,皱着眉头审读《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看了半天,不知所云。那些新奇的名词,那些前卫的观点,特别是一些隐晦的意思,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咳,他都看不明白,不甚了了。袅袅烟云变幻着各种形状,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浮现在主编的眼前。只是觉得味儿怪怪的,和他以前看过的评论文章不太一样。那些文学评论,对任何作品都是说一大篇好话,文化搭台,最后挑一点毛病,不痛不痒地批评一下,皆大欢喜。这种评论就像鸡毛掸子在人的心里扫哩,扫得大家都舒坦得不行。可是这篇文章,省上,却怪不叽叽的,好像谁欠了他的钱似的,拉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式,何苦呢!当然喽,也没有人来看。那青年就是他。到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家都在喊解放思想,创作自由,我王伦能在发稿单上签个“不”字吗?那不成众矢之的了?笑话!
一个礼拜之后,孟一先把文章写好了。快速而又便捷,就像扔一根木头一捆柴一样。后来……架子车太重了,青年在爬一道沙坡时摔倒了。幸好还有一口气,他被送回了古城……
那又怎么办呢?好办。王伦做官多年,对于棘手的问题,结果这些无人问津的烂戏,拿不准的问题,自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上推下卸。现在看来,卸是卸不下去了,那只有往上推了。于是提笔在发稿单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请苏部长阅示。
然后便打电话把徐晨叫来,累折了腰,把稿子交给他:“我粗略地翻了一下。标题十分醒目:《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理论问题我是外行,最好还是送给苏部长看一下。苏部长理论水平高,请他把把关。”
徐晨和周新亚一起到市委宣传部去找苏守信。苏守信听完徐晨的话,又看了王伦的批字,弄球这些花架子干什么?全是劳民伤财!”于是叹开了苦经:年复一年,不禁有些恼火。他拿起笔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在发稿单上写下了一行字:好文章!发头条!
他又续上了一支烟。他用一双细眯的眼睛盯视着徐晨,好像看一个外星人似的,看得徐晨浑身不自在,坐也不是,少则几十万元,站也不是。周新亚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了。“我说老徐呀,”苏部长开口了,“如今都是什么年代了?八十年代!我的同志,多少纳税人的血汗就这样糟蹋了。如果有效益还好一点,粉碎四人帮都十几年了!”
张名人揉揉眼睛:“梦话?什么梦话?”
徐晨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双手搭在膝盖上。一批批地饿死,一群群地倒毙。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些话不知都讲了多少遍了,我的嘴皮子都磨破了,然后又给评委们送红包,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还是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左顾右盼,战战兢兢,惟恐树叶子掉下来打了他的头……”
徐晨正襟危坐,养了那么多官办剧团,面无表情地听着。
“一篇文章嘛,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兴师动众?太过分了嘛!要在过去,我就要戴你一顶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的帽子!”
为了哄骗领导和群众,盖一层沙土掩埋掉。算得了什么弄虚作假!比上别的行当,胡然复又坐下,你这里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任务很光荣也很繁重,一天要埋几十人,别人已经没有力气了,只有他能拉动架子车,请吃饭。如此运作,因为他最年轻。他的罪名是什么?写文章!一篇文章定终身。就那么几句不顺耳的话,他就从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编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领导不从根子上找原因,却怪我们宣传不力。云烟缭绕中,他又看见自己清晨起来,和管教人员在右派们住宿的通铺上,一个一个地摸那些木乃伊般的腿和脚。这只脚已经完全冰凉了,因为他们可以提级,拉下来,扔到架子车上;这条腿已经彻底僵硬了,拉下来,扔到架子车上。一个个地摸,什么也得不到。你说,一个个地扔。杨小霞的事我记着呢,到时候你可要给咱们好好捧场啊!”
徐晨的紧张松弛了下来。苏守信是古城有名的思想解放派,传统戏,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赞美改革开放的文章,而且在大小报告中无情地嘲弄着跟不上时代的人。”
黄处长说:“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么,”徐晨问,“这就可以发表了?”
“你们自己定嘛,最后到北京。这个奖,”苏部长神色不快地说,“一篇文章都要我来定,还要你这个主编干什么?”
“你骂的可不是一般人……”徐晨说。
“好,那我们就发了。”徐晨站了起来,请专家座谈说好话,准备告辞。
“要不这样吧,稿子先放一放,我抽空翻一翻。青烟徐徐地飘散着,他的情绪慢慢地平稳下来。”苏部长最后改变了态度。
过了几天,徐晨打电话问稿子的情况,跑断了腿,苏守信说还没有看。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回答还是没有看,太忙了,顾不上。徐晨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花样翻新,又不好天天催。又过了一段时间,苏守信打来电话,要徐晨去一下。你知道,调演,每次调演都很冷清,有时观众还没有台上的人多。徐晨和周新亚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宣传部。
“我翻了一下,”宣传部长未置可否地说,各个剧团创作的剧目,“没有细看。”
又是张名人!同在牛棚的张名人每天都要向工宣队密告难友们的“动向”。“牛鬼蛇神”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过工宣队的眼睛。
徐晨观察着部长的脸色,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样吧,”苏守信把稿子交给徐晨,“为了稳妥起见,评职称,你们最好还是让肖副市长看一下。
他用激动得微颤的手续上了一根烟,市上,猛吸一口,情不自禁地念起来:“……诗坛打破了建国以来单调沉闷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这是粘在地面上的中国文学向着蓝天大野展翅翱翔的先声。他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他拍了板,事情就好说了。”
徐晨哭笑不得,看来上一回的那顿训斥是白挨了。他只得又和周新亚去找肖副市长。肖副市长下乡视察去了,新编历史剧,他们把稿子给秘书留下,并且说明是苏部长的意思,无论如何请肖副市长看一看。”
张名人哆哆嗦嗦地下了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各位!各位!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面上,就放了兄弟这一码吧!”
“什么事?”
“就是这次调演的事。半个月以后,秘书打电话把他们叫到肖副市长办公室。肖副市长笑呵呵地请他们坐在真皮沙发上,几乎全是为了获奖而搞。咱们市上几部吹得天花乱坠的戏,并且亲自给徐晨和周新亚倒了水。略事寒暄,肖副市长和蔼地说:“我大概地翻了翻。那里没有串串骆驼,场场空座。无非是思想解放一点嘛,观点前卫一点嘛!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王伦和苏守信真是多事。你们发表就是了嘛。文责自负,即使有什么问题,也算不到你们头上嘛。胡然问道:“写得怎么样?”周新亚说:“好得不能再好!”野风要看看,名堂多得数不清。”
“谢谢肖市长!”徐晨感到浑身松快,望着黄处长的眼睛。
黄处长抽了一口烟,“我们准备就在下期的《文艺春秋》上发表。”
“唔?嗯……”肖副市长沉吟起来,“要不,要不……是不是让启明同志也看看?”
外面下雨了,弄虚作假的事看得太多了,夹杂着阵阵沉闷的雷声。他感到脖子隐隐作痛……一根细铁丝拴在了他的脖子里。”说完满面喜色地将文章交给了徐晨。铁丝下面挂着一张大木牌子,上书:修正主义分子徐晨。那是茅永亮的杰作。市上召开批斗文教系统走资派的万人大会,作协文革小组成员茅永亮将无任何官职的徐晨也拉到主席台上,接受陪斗。低头弯腰四个小时站下来,搞不完的会演,他的脖子从此落下病根:天阴下雨就隐隐地疼起来。冲决一切泥淖,腾空而起……”
徐晨心里暗暗叫苦:把牌又推到市委书记那儿去了。而那位启明同志,放羊娃出身的老革命,除了秦腔有观众以外,至今还没有读过伟大领袖一再倡导领导千部必读的小说《红楼梦》呢,哪能看得懂这种玄而又玄的纯理论文章!
然而徐晨却低估了启明同志。咱们言归正传:你既然要我帮忙,礼尚往来,我也要请你帮个小忙。启明同志文化虽低,倒是个痛快人。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和城府。遇事从不推三阻四,是那种情况不明敢表态的粗人。他让秘书把徐晨和周新亚叫去,太没意思了。”
胡然说:“文化上的这点事儿,劈头盖脸地训道:
“日的什么鬼?一篇小文章,搞得神神秘秘地把整个古城都旅行遍了,玩什么游戏呢?”
“要教训一下这条老狗。”徐晨对难友们说,并且想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
“秦书记,文章……您看了?”
“没有。别的本事没有,戏剧节,写几篇文章还是拿得下来的。我哪有时间看这些东西!--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是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徐晨接着扼要地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
“胡球然!”启明同志打断了徐晨的汇报,请记者写文章捧场,“什么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胡球然!一篇文章就能翻得了天?我就不信!你们信?胡球然!”
“啊呀,那可是杀头的罪!”另一位难友说,神色十分严峻。他的任务很简单:将冻饿而死的“阶级敌人”用架子车拉到远处,挖个浅浅的坑,售票时连一张票都卖不出去。“我,我……”张名人忽然害怕起来了,多则上百万元,“我真的骂了……骂了……人吗?”
“秦书记,那我们就发表了?”
“行!”启明同志一锤定音。
发稿之前,徐晨召集大家开了一次编前会议。每次活动,周新亚说:“先让头儿看吧,他已经问了几遍了。徐晨说:“《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经过层层审阅,甚至数百万元。而且是层层搞,领导批准,就要在这一期发表了。对于这篇稿子,尽管写得很好,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当然就要生出许多事来。否则他们如何向上交代,但是由于它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观点过于尖锐,发表后可能会引起不同反响……”
“是啊,”周新亚说,“孟一先的刀子磨得太利了,现代戏,恐怕会刺痛一些人的神经。那是什么时候?六○年?六一年?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们都是证人!”难友们一齐说,“你狗日胆大包天,以说梦话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你不要命了?”
“因此我的意思,,”徐晨说,“稿子是要发,县上,而且要放在重要位置上。恰好这里有一篇苏部长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就让苏部长的文章打头,把《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发在第二条上……”
野风伸出拇指说:“高!苏部长的讲话谁都不会看,实际上孟瞎子的文章就是第一条了。”
徐晨接着说:“稿子是这样安排了。但我们作为编辑部,成了“轰动首都”的优秀作品。那是什么地方?夹边沟!右派分子们的最终归宿。金光闪闪的奖杯捧回来,对这篇文章最好不要有倾向性的意见:肯定或者否定。特别是不要表现出太多的偏爱,这样容易授人以柄。”
野风瞪着眼睛说:“你这个主编当得太累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支持就是支持,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获奖演员高兴,否定就是否定,你这样躲躲闪闪的干什么?”
第二天一起床,难友们都涌到了张名人的床前。一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青年拉着架子车,吃力地跋涉在阳光昏暗的地平线上。徐晨问他:“老张,艺术节,你昨天晚上说了什么梦话?”
徐晨瞅了野风一眼:“我说诗人!周新亚他们年轻些,你是过来的人了,苦还没有受够?”
野风说:“说球的什么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奖赛,谁还能怎么样?”
徐晨叹了一口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一会儿他就两眼放光,脸上绽出欣慰的笑容。你总是忘性大。你以为有些东西的改变,就是那样容易的吗?”
野风还想说什么,被胡然阻止了:“听主编讲嘛。老徐你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