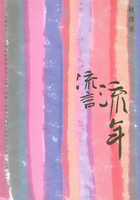如今,随着商品时代的到来,黄河茶园的性质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某些旧的东西不见了,一些新的内容产生了。茶客的成分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多了一些颐指气使的大款,他们是来“渔色”的;也多了一些浓妆艳抹的女郎,她们是来“钓鱼”的。而那些口袋发瘪的市民阶层,原先茶园的常客,反而很少光顾了。除了听戏之外,这里还成了赌博、谈生意、拉皮条、结伙成群的好地方。当然,来这里的大款,都是些西部的土大款,这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就可以看出来:一律光头,黑面,肥硕粗笨。胖手上戴着特大号的金戒指,光头上架着铜腿子水晶石眼镜。这都是些活跃在古城各个角落的包工头。真正做大生意大买卖的人是不到这地方来的。而那秦腔,也已不再是自拉自唱的“自乐班”。似乎是一夜之间,从各地涌来了许多专业的演员和乐师,以其业余爱好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黄河茶园。这些人里面,有本省各县的演员,甚至还有从陕西一些县剧团来的演员。县剧团早已发不出工资了,为了活命,女娇娃们不远千里,结伴来到古城地方,在黄河茶园里生根开花,很快便打开了局面。以至后来,凡有点姿色的女角儿,几乎每人都傍了一个大款,过着吃香喝辣的生活。增添了如此新鲜的内容之后,黄河茶园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茶园了。单纯的休憩变成了金钱的角逐,自娱的戏曲变成了商业性很强的演出。注入茶园的那些“新鲜血液”需要大把的人民币来维持。起先是演员唱了一段之后,由“剧团”的人端了塑料盘子到各个茶座上收钱,茶客们可以随意施舍,有钱人则直接往台上扔钱,伴随着粗野的口哨。这很不雅观,也很不规范。实践出真知。到了后来,也便有了经验,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各个茶园通用的规则:搭红。所谓“搭红”,就是往台上扔被面。先是自己买了色彩鲜艳的被面,扔给心中喜爱的演员。后来发现这很不方便,便由茶园购置好一批缎子被面,任由茶客们搭在自己崇拜的偶像身上。慢慢的也还就有了统一的价码:每条被面十元。你如果“搭”十条“红”,就付给茶园100元。而那些扔过的被面,依然被茶园收回,轮番使用。最后按搭红的多少,由茶园方面和演员分成。一般是茶园和文武场面一半,演员一半。特别出色的演员还可以多拿一点。于是这里便成了大款们争风吃醋、逞强斗富的地方。
演出的形式也介乎清唱和化妆演出之间。女演员们的化妆都很调皮,只化头脸而不穿戏装。一张打了粉底涂了胭脂和口红的脸蛋远比本人要漂亮的多,而贴了鬓包了头的发型更能使女性的特征突现出来。至于服装,那还是如今的时装来得性感一些。古代的戏装太保守了,像一只口袋似的将女人的身体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一点外露的地方都没有。而时髦的服装,比如超短裙、透明纱什么的,使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那些地方都可以明白无误地或者若隐若现地展示给男人们看。这多痛快!于是黄河茶园便出现了这样的景观:一群穿着性感的“古代美女”,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些光头墨镜满嘴脏话的暴发户跟前,和他们一起说笑逗趣,一起嗑瓜籽刮碗子。当大款们的手捏她们的脸蛋时,她们便发出娇嗲的惊叫,随之又是一阵浪笑。
胡然走进黄河茶园时,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作家先生来得有点晚了,偌大的场子里已经坐满了茶客。只有一张茶桌的旁边只坐着一个人,还有两三只空着的马扎子。于是便走了过去,拣一把干净些的马扎子坐了。
“咦,胡老师!”邻座操着浓重的土话和他打招呼。
胡然认出了对方。此人名叫尤大头,曾经带一个包工队维修过作协的房子,互相是认识的。
“怎么,你也到这地方来?”尤大头问道。不等胡然回答,他已经叫过伙计,给作家先生沏了一个三炮台碗子。“冰糖放多些!”高声地吩咐着。
胡然要了一瓶黄河大曲和一盘油炸花生,邀尤大头共饮。尤大头拿起瓶子看了看,说道:“我已经戒酒了。”又指指油光光的脑袋:“高血压。”
胡然知道他嫌酒不好,也便不再硬让。斟满杯子,独自个儿呷饮起来。一边抬头向四处张望,看看还有什么熟人。当看到远处的一堆红男绿女时,他的目光凝住了:杨小霞!那个位子很好,垂柳之下,紧贴黄河,既有浓荫覆盖,又可以沐浴到清凉的河风,里面是喧闹的人声,外面是潺潺的流水,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如此绝妙的位置,肯定是茶园老板特意给她留的了。和小霞一起的,还有几位市秦的女演员,那是她的小姐妹,平常关系很铁的,肯定是一起来“淘金”了。另有一位黑大胖子,极为惬意地躺在马扎子上,一幅大坨子墨镜遮住了他三分之二的脸面。他似乎是睡着了,带听不听地听着几位女郎叽叽喳喳地说笑,偶尔咧开肥厚的嘴巴,表示一点笑意。胡然没有认出他来。小霞也看见了胡然,她走了过来。胡然拉过一把马扎子,她吹了吹上面的微尘,撩起大红的风衣,款款地坐了下去。
胡然问她:“上次我老家过事,说的好好的,你怎么没有去?--把一庄子的人都等死了!”
“哎呀!”小霞拍拍额头,“忘死了,忘的死死的了。--你怎么不打传呼?”
“打了,”胡然说,“没人接呀。”
“噢,那可能是忘带了。”小霞说过这句话,便扭过头去,和尤大头寒暄起来。
胡然呷了一口酒,略带讥讽地问小霞:“你们市秦的人不是坚决不到这种地方来吗?今天怎么有兴致了?”
小霞的脸微微一红。这两年黄河茶园兴起“搭红”的风光,外地的三流演员纷纷涌来,市秦剧团的艺术家们岿然不动。他们嫌到这种地方唱戏掉身份。当有人劝他们去茶园凑凑兴时,艺术家们总是从鼻子里哼出这样一句:“那地方太脏了!”现如今,谁也没有动员,他们却自己来了。
略一沉吟,小霞便说:“哼,我也看开了。时代在前进,观念要更新,这也是下海呀!原来坚守着那一份清高,那一份神圣,给谁坚守呀?谁又给了咱什么好处?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有!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喝西北风呀?”
胡然问:“你今天唱什么?”
小霞说:“也就是几段清唱。”
尤大头凑过一张油碌碌的嘴巴:“杨小姐,今天可要吼亮豁些!”
小霞粲然一笑:“还要尤师傅抬举哩。”
尤大头说:“那是自然。今天听说你要亮相,我才撵来的。要是那些老鼠子乱唱,拿大红帖子请,我都不来哩。”
台上的锣鼓家什已经响了,小霞向尤大头和胡然微微一欠身,步态轻盈地向台上走去。当夜莺奖得主站在台口,向全场鞠躬致意时,茶园里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尖厉的口哨。
就是亮豁!只一嗓子,就吼得满台生辉。胡然忽然来了一股邪劲,高声喊道:
“十条红!”
叫声刚落,伙计已从账房里取出一摞缎子被面,熟练地朝台上扔去。茶园老板同时便出现在台口,将被子拾起,又拿回账房。小霞朝胡然微微一笑,又接着唱起来。
“一百!”伙计轻手轻脚地来到胡然面前,伸出一只手来,胡然掏出一张“老人头”,递给伙计。伙计把钱交给账房,账房记下数字。
胡然感觉很好。他又喝了一口酒。这些天连续收到几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口袋胀得鼓鼓的,他准备潇洒一回。
“二十条!”他又喊了。
一大摞各种花色的被面像飞天似的舞向台口。
“感觉好极了!”作家先生在心里说道,又喝了一大口酒。
“五十条!”尤大头发话了,瞅了胡然一眼。
“一百条!”胡然眼睛红红地望着尤大头飞向舞台的五十条被面,嘶声吼道。
更多的被面扔上去了。醉眼蒙中,作家先生看到伙计伸出的手:“一千,先生!”
他把钱全掏了出来,数了十张老人头,交给伙计。尤大头望着作家先生瘪下去的钱包,嘴角微微地动了动,做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
“一千条!”尤大头高声宣布。
场子里响起了一片叫好声。杨小霞向包工头鞠了一躬,更加卖力地唱了起来。
“不玩了?”尤大头问胡然。
胡然眼睛看着别处,没有回答。
“捧把式,”包工头说,“那点钱不行。”
说着解下别在腰里的蛇皮钱袋,抽出一沓子钞票,往茶桌上一:“作家!手头要是不方便,这钱你先用着。咱俩再玩它一个回合,咋样?”
胡然把钱推了过去,冷冷地说:“你玩吧,我已经玩够了!”杨小霞已经唱完了一段。尤大头朝台上招招手,高声叫道:“杨小姐,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咱给你泡一个甜甜的碗子!”
夜莺奖得主笑嘻嘻地望着包工头,却并不挪动身子。
这时,垂柳下面的茶桌上,那个一直躺着养神的黑大胖子微微地欠起身来,摘去了大坨子墨镜,露出庐山真容:马福录,马百万!马福录用食指轻轻一勾,茶园老板快步来到他面前,躬身笑问:“马哥,有啥吩咐?”
马百万附耳低语了几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纸本本,交给茶园老板。茶园老板用茶盘托了那小本儿,兴冲冲走上台去,大声宣布道:
“特大喜讯:黄河大酒店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福录先生为扶持和振兴秦腔艺术,特赠予杨小霞女士人民币贰拾万元。这是活期存折。”
说着拿起存折,向台下展示了一番,郑重地交给夜莺奖得主。
黄河茶园立时开了锅。喝彩声、赞叹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
杨小霞兴奋得两眼放光。她朝着马百万的方向,连着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走下台去,坐到垂柳下的茶桌旁,深情地依偎在马老板的身旁。
马福录拉起小霞的手,拍着她的手背,轻声说道:“拍电视的事,就包到我身上了。”
小霞娇声问:“真的?”
马福录说:“这你就放一百个心。《游西湖》你想拍几集就拍几集。”
小霞把头靠在马百万的肩上。
胡然猛地站了起来,提起酒瓶,将剩下的半瓶酒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使劲把瓶子摔向远处,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接着便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他醉倒在茶园门口。
杨小霞急忙跑了过来,把他扶起来。她扬手叫了一辆的士,搀胡然上车。胡然一把将她推开,吼道:“走开!我能上去!”望着的士远去的车影,小霞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当天晚上,她就和马百万住在一起了。
本篇讲述的是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如何变成大象的故事
杨小霞和马百万的销魂之夜是在黄河大酒店的一个高级套房里度过的。
当那个黑大胖子压在她的身上时,这位风情女子一点激动、一点感觉都没有。她只是觉得窒息,有点儿透不过气来。肥大的身躯在上面起伏晃动,臭烘烘的嘴巴咬着她的脸蛋,她紧紧地闭了眼睛,心里在默默地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遍又一遍地数。终于,一股爆裂的感觉传遍了她的全身。她的下身全是湿的了。
她光着腿子走进浴室,彻里彻外地冲了个澡。当她回到床上时,马百万已经打起了很响的呼噜。她静静地躺在一边,用毛巾被盖住了身子,却怎么也不能入睡。眼前又浮出了一张白里透黄的脸,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在幽暗的光线中晃来晃去……她开始怜悯起这个穷书生了。
哎,胡然呀,你要明白些。你能养活我吗?我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个唱红了高原大地的演员,你能养得起吗?你能配得住吗?我要穿高档衣服,吃生猛海鲜,我要买房子,住豪宅,你能办得到吗?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稿费更是少得可怜。我做一次美容就是几百元,买一套进口皮装就是上万元,你能供得起吗?说句不客气的话:你的那点工资,连买一瓶好些的香水都不够呢。
当然,当然,我得承认,你给我帮了不少忙。你在穷山恶水的茫茫人海中发现了我,鼓励了我,使我认识了“我”,读懂了“我”。不仅如此,你还帮我调到了古城,帮我获了奖,成了这块地面上的一个人物。这我都记着哩。可是,可是我也对得起你呀!我和你好了两年,实心实意地好了两年,把什么都献给你了,一点代价都不要,整个身子都给了你。你打听打听,世上还有比我善的女人吗?
再说,再说,你的那位夫人,我能招架得住吗?我一个搞艺术的弱女子,能是杀猪婆的对手吗?和一个疯婆子纠缠不休,又是何苦呢?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哎,胡然呀,胡然……
她蜷曲着身子,像一只小鸟一样,依偎在马百万的身旁,渐渐地睡着了。
此时的胡然却无法入睡。他整日借酒浇愁,心情极为沮丧。他不怨小霞薄情,惟恨自己无钱。着名的西部小说家,堂哉皇哉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却拴不住一个女人的心!太没有本事了,太窝囊了,太丢男人们的脸了!作家先生甚至以为,小霞的离去,不单单是失去了一个女人,而是他整个人生路途上的一大失败。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就连周新亚那些精彩纷呈的段子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就在此时,他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一件来自乡下的包裹。包裹单上注明的寄件人是田珍。他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到了那个遥远而又迷蒙的夜晚。打开包裹,里面装着一件精心编织的驼绒背心。背心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上什么都没有写,只是抄了两首花儿--
走哩走哩者走远了,
眼泪花儿飘满了,
眼泪花儿把心淹了。
大雨倒给了整三天,
毛毛雨毛给了两天;
哭下的眼泪担子担,
尕驴子驮给了九天。
这时他的耳畔忽然响起了几年前田珍和他走过那段空旷的田野时,嘹起嗓子所唱的花儿--
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阿哥的憨肉肉哟,
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看去是容易摘去是难,
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阿哥的憨肉肉,
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随着这幻觉中声音的渐渐消失,他的眼睛被一层湿气罩住了。
他准备给田珍写信。但犹豫了半天,却下不了笔。他不知这信怎么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分手这么些年之后,那个年轻的村妇依然想念着他。而他,却早已将她忘记了。他又和别的女人生生死死热火了一场。这话该怎么说,又如何向她解释?难啊!而且,写了信又该咋办?恢复联系,再续旧情?他还真下不了决心和一个农村妇女结合。作家先生处在两难之间。他把驼绒背心悄悄地压在了箱底。又找了几本刊有自己新作的杂志,给田珍寄去。信嘛,准备过一段时间,想明白了再写。
“嘀铃铃……”电话响了。
胡然拿起了听筒。
“胡老师吗?”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是沈萍!
“胡老师您好!”声音甜得不能再甜。
胡然一下子来了精神。
“小沈,你在哪儿?”
“我在古城。”
“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
“是出差吗?”
“不。”
“那……”
“我调到古城了!”难以抑止的激动。
“调到古城了?”胡然也兴奋起来。
“对,调到市妇联了。”
“太好了!”作家先生对着话筒叫起来。
“你高兴吗?”
“高兴!高兴!”
“胡老师,我想来看你。”
“欢迎。--你是怎么调来的?”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咱们见面再谈吧。”
“好的。我等你。--你可要来啊!”
“一定来。拜拜!”沈萍挂上了电话。
胡然依然握着听筒。下意识地嗅了嗅,那话筒似乎还有沈萍的热气和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