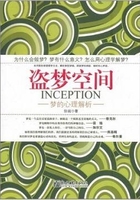“这个没问题。”杨安接了过来。
安茜款款离去。
御盈走上前去推门,里面突然扔出来一个小酒坛子,伴随着男人狂躁的声音,“滚开!不是说了不见吗?还忸怩个什么劲!”
“小心!”杨安眼疾手快,迅速将御盈拉过去,好心劝道:“御姨娘小心些,庄主恐怕谁都不愿见,您这样硬闯,会伤了自己。”
御盈嗤嗤地笑,绝美的脸上光彩照人,“我偏不信,偏要去闯,我倒要看看他能如何伤我。”
她说罢不顾杨安的阻拦,大踏步走了进去。
书房内充斥着一股刺鼻的酒味,御盈忍不住皱了眉。
程连萧听到房中有脚步声,放下手中的酒坛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含糊道:“杨安,酒呢?我让你抬过来的酒呢?我要喝酒,要喝好酒!”
御盈诧异地看着程连萧,她简直不能想象,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带领过千军万马吗?真的曾是威风赫赫的虎贲军的大将军吗?真的是让叛军伏诛,让蛮夷归降的大功臣吗?
眼前的男人,只是个失去了右臂的残缺的人,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淋淋,披头散发,藏污纳垢。
御盈忽然就觉得眼眶酸胀,有一种液体流了出来,她便尝到了咸味。
可是程连萧眼神恍惚,根本看不清。
“没有酒,妾身擅自做主,打发抬酒的小厮回去了,庄主今晚喝不到顶好的女儿红了。”御盈盯着程连萧,语气是出奇的平淡。
程连萧指着眼前的模糊人影,口齿不清道:“大胆!你是谁,敢这样和本庄主说话!”
御盈看着他颓废的面貌,直直地走了过去,她拿起他仅剩的左手,抚摸自己的太阳穴,幽幽道:“庄主,您摸摸这个字,这个程字,是您亲手用剑刻上去的,你把我做了标记,怎么能想不起我来呢?”
程连萧像个孩童一般呵呵傻笑,他用粗粝的拇指一遍遍摩挲她的脸,“胡说,我怎么会在人脸上刻字?”
“因为御盈做错了事,所以庄主要惩罚御盈。”御盈平静地看着他。
程连萧浑身一震,突然用左手摸着空荡荡的袖筒,喃喃道:“难道我也做错了事?所以老天爷这样惩罚我?”
御盈眼中精光流露,“难道庄主没有做错吗?”
她像对待一个孩童般温柔,轻轻地按着他坐了下来,慢慢脱去他血淋淋的外衣,他右肩的纱布早已被血浸透,却因为无人能靠近,迟迟未换。
御盈将纱布拆下,细心地用药酒擦拭伤口,“庄主,会有些疼,您忍一下。”
程连萧呵呵苦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痛吗?”
药酒一接触伤口,便发挥它强大的威力,程连萧感觉伤口火辣辣的疼。
这样一疼,脑子反倒清明了。
他看着御盈忙碌的小手,想起她刚才未说完的话。“你刚才说我做错了什么?”
御盈擦药酒的手一顿,抬头看着程连萧冷峻坚毅的脸,“庄主真心爱护安茜妹妹,为了救她而失去一臂,应该觉得值得。男人有义务保护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庄主实在不必如此颓丧。”
这话成功的惹怒了程连萧,他猛地揪住御盈的头发,御盈被扯得头皮发痛,心中却觉得安慰,她就是要他看清楚事实。
“谁告诉你,安茜是我最心爱的女人?哼,心爱的女人,我竟不知,她有那么重要。”
御盈勉强笑了笑,“我明白了,庄主只是出于男人的职责,保护自己的女人,与对方重要与否,无甚联系。”
程连萧放开了她的头发,冷声说:“你倒是不笨。”
他现在情绪低落,御盈不与他计较,继续帮他包扎伤口。
“庄主难道没想过报仇吗?向安茜妹妹射出毒针的人,可谓卑鄙至极,庄主不想手刃仇人吗?”
程连萧眉头紧皱,“是些不入流的江湖小门派,不用我说,杨安定会追查。”
御盈低低叹了一声,故意道:“安茜妹妹平时心肠不错,也不与庄外的人来往,怎么就被江湖门派惹上了,还痛下杀手。”
程连萧头痛地扶额,有些不耐道:“她早先与我讲过,以前学了些玄门法术,与江湖上的人有些未了的恩怨。”
御盈心中有了思量,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程连萧见御盈若有所思,冷笑不已,讥讽道:“怎么,忍不住要告状了?你也喜欢争风吃醋吧?你走吧,快些走,我没有精气神应付你。”
御盈正要思辨,却听他冲外嚷道:“杨安,给我拿酒!”
很快杨安便将酒送了来。御盈站起身来,看了看杨安,却见他无奈地叹气。
程连萧身体软绵无力,却不让杨安帮忙倒酒,硬要自己举着坛子,对着酒坛大口喝。
一坛酒的重量不轻,他的左手又不好使,手一软便听见“啪”一声,酒坛碎裂,陈酿的女儿红流淌了一地。
御盈心道不好,忙若无其事道:“庄主快闪开些,这些陶片很锋利,仔细割伤了您的脚。”
她说着便要扶着他走,程连萧却狠狠地推开了他,他冰蓝色的双眸闪着猩红的光,额上青筋隐隐跳动。他暴躁地踢翻了桌子,怒吼道:“我成废人了,什么也做不了!写不了字,舞不了剑,现在连酒坛子也端不起来,啊……”
他像一只突然发了疯的雄狮,浑身的血液都流淌着狂躁的因子,推开房门冲了出去。
外面天气原本闷热至极,令人窒息,此刻,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沉闷的雷声如同大炮轰鸣,使人悸恐,接着便下起瓢泼大雨,房檐上水流如注。
御盈拽住程连萧,“庄主,你冷静些,你这样出去淋雨,伤口一定会恶化的。您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程家庄啊,您是主心骨,忍心弃全家人不顾吗?”
程连萧负气道:“那就散了吧,杨安……把全庄的人都遣散!”
他忽的钳制住御盈下巴,阴阳怪气道:“要不要我给你写一封休书?你还可以奔更好的前程。”
“什么?”御盈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却见程连萧脸色隐痛,毫不留情地推开了她,疯狂地冲入厚厚的雨幕中。
御盈看着程连萧像孩童般赌气,左手握成拳,下了死力气,狠狠地砸向院子里那颗碗口粗的大树,硬要砸得树上的叶子簌簌落下,方显得自己手臂依然有力气。
树叶漫天乱飞,其中有几片湿漉漉的贴在御盈的脸上,脖子上。
她看着那雨中发狂的男人,苦涩地笑了起来。
杨安愁容满面,好心劝御盈:“御姨娘还是回去吧,今个儿庄主是没法好好说话了,这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辰呢。”
御盈却不听,直直走入雨幕,决然道:“他要闹到几时,我便陪他到几时。”
程连萧的酒劲上来,他疲劳至极,心力交瘁,突然呕出一口血来,便直直地栽了下去。
御盈大惊,忙跑过去将他扶起,可程连萧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杨安扑通一声,跪在了程连萧面前,四十岁的大汉却泪流满面,他重重地叹气:“我跟了庄主这么多年,从未见他一蹶不振,这以后,可怎么好?”
御盈也颇为动容。此刻狂风咆哮,天神仿佛收到信号,撕开天幕,将天河之水倾注到人间。
她怀中抱着昏睡的程连萧,直直地抬起脸,任雨点砸在自己娇美的脸颊上。
似是想通了什么,御盈笑颜如花,她对杨安道:“杨总管,你信吗?庄主会好起来的。”
杨安老泪纵横,重重地点了点头。
御盈抬起头看天,雨水落入了她的眼眶,她闭上美眸,幽幽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咱们庄主,将来必能成就一番伟业。你瞧,连老天爷都看不得他如此落魄,这不是发出了警示吗?”
杨安大震,有些惊骇地望着御盈,觉得不可思议。
杨安将程连萧扛回房间,御盈为他脱下湿漉漉的外衣,看见才包扎好的伤口又渗出血丝,里面想必已溃烂不堪,御盈眼中掠过不忍。
杨安看在心里,苦口婆心地劝:“御姨娘您回去歇着吧,这一夜恐怕都不得安生,别把您累垮了,我找丫环来伺候庄主。”
御盈摇摇头,“那样不妥,丫环们伺候,我不放心,我对医术略知一二,还是我来吧。”
御盈将程连萧的衣服换下,用热水将他的身子擦洗一遍,又清理了伤口,给他左手上的创面也细细地涂了药粉。
做完了这一切,她坐在床边,一双晶亮的美眸盯着程连萧,没来由地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她伸出玉手,抚摸他冷硬的脸颊,低低问道:“程连萧,你能让我依靠吗?”
在这寂寥的雨夜里,回答她的,只有男人沉沉的呼吸声。
在青峰山兰若寺的一间禅房内,广慈一身裟衣,席地而坐,面容如玉温泽。
他左手竖直立在胸前,右手轻轻敲打木鱼,嘴上喃喃念着《金刚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广慈的身边坐着一位老者,满头花发,慈眉善目,身着厚重的袈裟。他睁眼看了看身边年轻的广慈,忽而皱了眉头。
“广慈。”他平静地打断他,声音十分温厚。
广慈骤然停下手中的动作,恭敬的对那老者施了一礼,“师父,请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