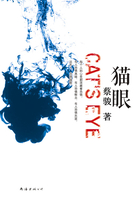吕明阳走进正厅,见迎门挂着一副山水中堂,两边写有对联:得闭口时且闭口,应饶人处可饶人。地面上摆放的都是上好红木做的桌椅,茶几上放有杯盘碗盏,也是不俗之物,四面的雕花窗子精工细致,一看便知是有钱人家。吕明阳看过那副山水,随口问道:“怎么这中堂下边不放些兰花或者盆景?如此才像样子。”李小姐皱眉道:“以前也有人这样说过,不过父亲素来不喜欢花草,屋子里外都不准种的。他说他闻到花香便头晕,故此我家从不养花。也因我小时爱摆弄花草,所以他就很生气,将我送到三里外的一处房产中居住,平时也不见我。”
听了这话,吕明阳心中仿佛打了一个结,又道:“哦,原来如此。我听说塞外有些人,生活习性怪异,闻不得花草气息,难不成令尊就是塞外人氏?”李小姐摇头道:“这个我也不知,因为我家搬来之时,我才不过四五岁,记不得事,家中的仆人也都是此地雇来,故此他们也不知道。”吕明阳道:“那你没问过你父亲么?”
李小姐面露苦楚:“我曾问过他,可他却不说,而且看他的样子很是恼怒,所以我以后也就不敢再问,只当自己是本地人罢了。”吕明阳见问不出什么,便道:“可否带下官到你父亲房中看一看?”李小姐道:“大人可是为给我父申冤报仇?”吕明阳不置可否,道:“此是下官职责所在,但有一分疑惑,便要问个究竟。”李小姐似乎面有难色,吕全喝道:“小姐,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家老爷?”李小姐连连摇手,吕全不耐烦的道:“那就快快带路。”
李小姐没办法,只好在前边领路,两人跟在后面,转过前厅,走入后堂,来到一处屋门前,李小姐停下了,红着脸用手指了指房门,说道:“这就是家父卧房。”吕全跑过去开门,不防正与一个人撞个满怀。
那人刚从房中出来,急急的要走,不想被人当头撞见,举头一看,见是吕明阳,立时吓得面无人色,低了头要走,被吕全一手扯住。吕明阳抬眼看时,见那人竟是吴玉年吴举人。
吕明阳喝道:“原来是吴举人,你因何躲在这里?”吴玉年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看样子是吓得语无伦次了。倒是李小姐为他解围:“这位吴举人与家父平素交好,现在家门不幸,特意来帮忙的。”这话虽是中听,但却不无破绽,可见李小姐虽是胆大,却也没有什么经验。吕全道:“便是帮忙,也不必帮到死人屋里吧。”
吴玉年看着李兰兰,涨红了脸,突然来了勇气,一挺胸膛,道:“既是被你们发现,我也不必隐瞒了,我与李小姐情投意合,琴瑟和谐,这个也犯法么?”吕明阳笑道:“倒也不是,但是你可否说清为何要躲在这屋子里。:吴玉年大声道:“说便说了,兰兰家中出了这种事,我来帮忙,只因大人来得匆忙,小人不愿出头,故此找地方躲一下,李小姐说这里最是安静,没人会来,所以才将我藏到这里。如今被你们撞破,也没什么好说的。“
吕明阳一笑,只觉得这吴举人倒是个痴情种子,没什么心机,便和颜悦色的道:“这个本官管不着你们,你二人也不必有什么理亏之处,本官权力再大,也不能禁止别人幽会。吴举人本就在屋子里,而我也想观瞻一下,可不可以相烦阁下代为介绍?“
吴玉年万没想到吕明阳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怔了一下,道:“这屋子我也是头一次进,说什么代为介绍,大人想进便进罢了。”吕明阳也不客气,抬脚进屋。但见这屋子与前厅又是不同,这里除了一床一桌以外,竟是什么也没有,窗子离地很高,也很小,而且好像从来都没有开过,桌子上只有一只杯子,除此之外便空无一物。这地方简直是达摩老师的面壁之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吕明阳怔住了,他万没想到一个富绅的卧室竟会是这般寒酸。
他问道:“你父亲就住在这屋子里?”李小姐道:“是的,他已住了多年,从没想过要搬。”吕明阳点头叹息道:“现在我知道他是如何成功的了。”他当然知道,一个把钱不当钱的人,通常都会很有钱,因为他们不把有钱当做很享受,他们只把钱当做一种工具,地位的工具。
吕明阳不由得说出一句:“单看这屋子里,只怕神仙也看不出他是哪里人了。”这句话一出口,吕明阳就感觉自己说走了嘴,不由得面色一红,幸好他面对里面,没有人看到。
可虽然没人看到他的脸,但每个人都听到了他的说话。吴玉年接口道:“大人想知道他是哪里人么?”吕明阳一惊,回头问道:“难道吴先生知道?”吴玉年摇晃着脑袋:“我当然知道,君子虽不窥人阴私,但无意中听入耳朵的话,倒也没法子忘记。”吕明阳一听,急问:“你听到什么?”吴玉年看了他两眼,转转眼珠道:“如果我对大人说了,大人是否会把今天的事忘却了呢?”
吕明阳微微一笑,道:“忘却什么?本官从没到过李府,不知有什么可忘却的。”吴玉年怔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竖起大拇指,道:“那样最好,最好。”接下来他又偷眼看了一下李小姐,见她没什么反应,便将吕明阳拉到一边,轻声在他耳边说:“那日我厚着脸皮来李府提亲,被李掌柜迎头骂了出去,但他说的话中却无意间露出了他的底细。我听出他曾说了一句话,口音是……江州口音。”
吕明阳霍然看着他,道:“你如何听出的?”吴玉年笑道:“小人前些年曾在江州求学数载,如何会听不出那里人说话?”吕明阳道:“你可说准了,如果乱讲,关系非小。”吴玉年沉下了脸,一字字道:“如果小人有半句假话,大人尽可以下小人大狱。”吕明阳看着他,吴玉年也睁大双眼,与他对视。有片刻之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突然吕明阳大笑道:“今日下官有些醉了,沉醉不知归路,误闯误撞,还望主人不要怪罪。吕全,赶紧扶本官回去。”
吕全何等人,自是聪明,一个字也没说,搀着吕明阳离了李府,回转县衙。刚刚进门,吕明阳脸色一正,道:“你不要休息了,带一个衙役,速去江州走一趟,看看那里有什么关于墨菊的消息。”吕全应了,点头叫过一个衙役,上马而去。
吕明阳见他走了,微微冷笑,草草吃过晚饭,也不带从人,一个人向张凤如的宅子走去。
此时天色已晚,县城内大街小巷都亮起了灯光,买卖大多都关了门,只有几个酒铺饭堂还是高朋满座,呼叫喧哗,好不热闹。吕明阳穿街过巷,直入张宅。此时张凤如刚吃过饭,正泡好茶要喝,忽听县令大人来到,忙出门迎接。
吕明阳喝了一口茶,微微笑道:“不想张大官人也是好茶之人,以后有机会,定要在一起论茶品茗才是。”张凤如谦逊道:“哪里,小人哪懂得什么茶艺之道,只不过随口乱喝,便是好茶也遭踏了。”吕明阳微微一笑。张凤如道:“大人夜间光临,可是为了那件案子?”吕明阳点点头,道:“我只是想知道那天夜里,你们几人聚会的情形。”
张凤如想了片刻,道:“那几人常来我家聚饮,前天的情形嘛,与往常相同,谈古先生弹了几支曲子,明尘大师画了几幅画,并没什么与往常不同之处。”吕明阳道:“那在李应龙睡下的前后时间,可有人离席?”张凤如道:“自然有的。几个人都曾离过席,李掌柜睡前,吴举人和明尘法师曾去方便,谈古曾去沐浴更衣,我也离席去过一次内室,唯有李掌柜没离过席。但李掌柜睡下后,便再无人离席了。”
吕明阳听了,沉思一会儿,道:“你可知道那几人的住处?”张凤如道:“自然知道。”吕明阳道:“那相烦你告诉我,本官想去登门拜访。”张凤如一一说了,吕明阳也不多留,起身告辞。
等到了张宅门外,吕明阳抬眼看了一下天色,但见夜色正深,街头巷尾人来人往,倒不算冷清。吕明阳信步走进一个茶馆,要了一壶滟茶,慢慢的坐喝,耳朵却听着茶客们的闲谈。
忽听一人讲道:“最近也怪,听城外人说,现在的盗墓贼好像离开此地了,再埋下的尸体没有丢失的了。”另一人道:“你们还不知道?这两天城中出了一桩奇案,我看八成是这盗墓贼惹出来的。”
又有人道:“你说的是那桩老鼠吃人的案子么?那跟盗墓贼有什么干系?”前一人道:“你怎么不想想?老鼠可有敢吃人的?定是那些盗墓贼惹得天怒人怨,老天派下神鼠来了。”最前一人道:“那为什么老鼠不去咬盗墓贼,却去吃李大掌柜?”那人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没脑子,那李掌柜平日神头鬼脸,让人捉摸不清,来路又不正,而且还有那么多钱,不是盗墓贼还能是什么?”几个人都不住点头。
吕明阳听了,心中一动,正在此时,门外突然又闪进一个人来,因走得急,正撞上一个茶客,那茶客正听得入神,不防此人,被撞得差点倒在地上。他气急一推那人,骂道:“你这人奔丧么!走路不带眼睛。”那人点头哈腰的陪笑脸,说了一些好话,茶客才放过他。这人四下扫视了一遍,好像是来找人,似乎这里没有他要找的,便要离开。吕明阳何等样人,一眼看出这人是个偷儿,而且早已得了手。他走上前去拉住偷儿,笑道:“王老弟,怎么来了也不招呼一声,敢问是找李大哥的么?”
偷儿一惊,想要甩脱他的手,但吕明阳平素好武,五根手指如同钢钩一般,掐得那人脸上变色,嘴巴一直要歪到后脑。偷儿知道遇上了眼亮的主子,陪笑道:“哦,原来是张兄,失礼失礼。既是如此,小弟做东,去喝几杯吧。肥鸡肥羊,一人一份。”
这是行话,意思是与他分赃。吕明阳摇头,从他袖子里取出一个钱袋子,扔在那茶客桌上,茶客一见,正是自己的,方知被人摸了。不由大怒,连同几个朋友一起要打那偷儿。吕明阳说明身份,那些人方才住手,再看那偷儿,早吓得面无人色。
吕明阳擒着偷儿回转衙门,等到一个僻静的小巷,那偷儿吓得跪地叩头,死赖着不肯走。吕明阳一问这才得知,原来他是早上刚刚从衙里放出来的。再被关进去就要重判。吕明阳沉着脸,喝叱道:“既知朝庭法令,为何一犯再犯,像你这样的人,不重判何以服人?”偷儿苦求道:“小人不是故意犯法,只是身体单薄,做不得工,家中有老母幼儿,不得已才上了贼船。”吕明阳听得也是心酸,但他执法多年,断不肯徇私。
那偷儿急得泪水直流,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道:“吕大人,如果小人知道一些事情,可不可以戴罪立功?”吕明阳一怔,道:“你知道什么事情?”偷儿道:“只要大人许可,小人就会说。”吕明阳脸一变:“你是在与本官讲条件?这样的话更是罪上加罪。”偷儿拍着胸膛:“小人绝不敢与大人讲条件,也罢,无论大人放不放小人,我说了便是。”
原来凡是这种街头行窃者,必是两人或三人一组,以便偷了东西后好转手,这样你便捉住他,却搜不出赃物。俗语说捉贼捉赃,没有赃物,他还要反咬你一口,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可今天这偷儿只有一人,没有帮手,是因为那帮手已死了,就是那个被毒蛇所伤的赵驴儿。而他说的,就是这个赵驴儿的事。吕明阳开始没怎么留意,但听他说到重阳节那天,突然心中一动。
原来偷儿说道:那日吃过中饭,他找到赵驴儿,想与他联手做案,谁知赵驴儿却拒绝了,只推有事,一个人勿勿的去了城西,他不太放心,也到了城西,没想到此时却发现赵驴儿不知从哪里回来了,手中提着一根似是短棒样的东西,转进了一个茶楼,他刚也要进去,却迎面撞上了一个人,他认得这人,竟是张凤如张大官人。张凤如吃了一惊,却也没怪他,便急急走了。他再到里面找赵驴儿,发现却也不知去了哪里。结果没过下午,就传出了赵驴儿身死的消息,偷儿说这一定是张凤如下的手。
吕明阳见偷儿怀疑是张凤如杀了赵驴儿,不禁失笑,只觉得其中漏洞百出,没有任何根据,但他却对赵驴儿手中的那样东西产生了兴趣。看来赵驴儿重阳那天做案并不是一起,而那样形如短棒样的物件到底是什么呢?
他突然猛的想起,明尘法师说过,他失窃的东西里面少了一幅画,难道那样东西就是这幅画?赵驴儿既是已偷走了画,为什么又要去偷窃一次?况且他大字不识,绝不是懂画之人。
吕明阳脑袋里满是问号,却没有放过偷儿,将他带回衙中,却没有立时判他,只是关了起来,等到一切案情大白之后,再看他当初的举报有没有作用,如果有用,便减轻判罚。那偷儿叫苦不迭,但也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又住进班房。
第二天一大清早,吕明阳便起了身,吃过早饭,带了周虎,出城向清神谷来。他已向张凤如打听过谈古住的地方,所以转过一个小山包,就看到了一所竹篱围绕的清静小院。
他们未到门前,就听屋子里传来一阵琴声,这琴声如怨如诉,如泣如慕,忽而欢快,忽而忧郁,仿佛人世间一切悲欢离合尽在七根弦上流淌出来,使人沉浸在其中,不觉沉醉。
突然“铮”的一声,好像琴弦断了,将吕明阳从沉醉中惊醒,就听屋子里有人道:“门外可有俗客?”吕明阳朗声一笑,道:“下官自然是俗客,打扰谈先生清兴了。”房门开处,谈古一袭白衣,头发披散着走出来,看样子刚洗过澡不久。他看到吕明阳,也没有什么表情,淡淡的道:“原来是吕大人光临,失礼了。”
他开了大门,请二人进屋。吕明阳一脚踏进屋子,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香气,原来屋子里四面都燃着香,如同寺院的佛堂一般,香烟缭绕。而屋中的摆设竟是极为简单,四壁空空如也,用白粉刷得一尘不染,四角放着八个香炉,中间地上有一张小几,一个蒲团,几上一张琴古意盎然。
吕明阳笑道:“谈先生每次弹琴之时都要焚香的么?”谈古点头,道:“琴乃神物,不焚香是为不敬,也就奏不出妙音。”吕明阳道:“不错,谈先生大有古代圣贤之风,单看这屋子就知道阁下清心寡欲,无怪乎能弹得这一手仙曲。可称当世妙手。”
谈古淡淡一笑:“大人过誉,小人绝不敢当。”他又取来两个蒲团,请二人坐下,自己也坐了一个,道:“小人家中很少来客,只有明尘法师和张凤如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也不常来。所以有慢待之处,请大人莫怪。”吕明阳道:“不怪不怪,能听到阁下的仙乐,已是不虚此行了。”他突然干咳了几声,道:“下官来得急了,有些口渴,不知可否讨杯茶喝。”谈古道:“这有何难,我这里备有上等茶叶,大人少等,我去烧水。”
原来这宅子只是他一个人住,没有人服待,谈古自觉得年轻,也用不着人来帮忙。
吕明阳看着他出门去烧水,便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屋子里到处都是浓烈的香气,几乎有点熏得人头晕。他想找个清新点的地方,便一推门进了一边的卧室。
他刚一抬头,目光便一下子定住了。这屋子与外间的琴室不同,有桌有椅有床有柜,却并没有什么与平常卧室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有一点,在正对着床的窗台上放着一盆花,黑色的菊花。
墨菊!
吕明阳脑子里如飞一般在转,无数个画面闪电一般掠过,又是墨菊,此地本不产墨菊,这盆花是他从哪里带来的,会不会是江州?这个谈古难道也是江州人么?那朵插在庙门上的花是不是出自这里?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谈古的脚步声,忙退到原地,见谈古已提着水进屋,方要泡茶,吕明阳摇摇头,苦笑道:“谈先生不要见怪,下官是不能在你这屋子呆下去了,这股子香味冲得我头脑发晕,心头恶心烦呕,下官要告辞了。”
谈古见他要走,也不强留,送出门外。等到不见了吕明阳背影,谈古回头看了一眼那屋子,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吕明阳丝毫没停留,马不停蹄赶回衙门,这一路上他的眼睛越来越亮,仿佛有什么难题解开了一般。可刚一进门,就见仵作慌慌张张跑过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吕明阳眉头一紧,道:“真有这回事,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