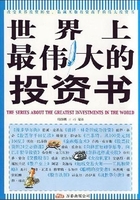几年前,省拫的总编辑退休。大家觉得惋惜,他自己也惆怅。说是六十岁,看上去不到五十。老年人可能有的病,他一种也没有。精力则比许多青年人还旺盛,实在是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于是订了一个消耗余热的旅行计划。因了这计划,董源在沉寂了至少几百年之后又一度出名。
董源所在的这个县,处在这个省的边远地区。全省的公路干道几乎都与邻省联网,独到这个县的几十公里是一段窗肠,往前是一派连绵的大山。翻过山,坐一天汽车,便是当代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的特区。而董源则失察在这派大山里,无声无息。
在几十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间,总编辑差不多走遍了这个省的山山水水。像这样他从没有涉足过的县是极少数。不光是因为此地太边远,也不光是因为报社顾及不周,实在是因为这里太没有新闻传出。纵然是曾有过点什么事情,也太没有新闻价值。隔绝在那山窝里的一群人,朝暮作息,生老病死,别有洞天。先前县里开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郎会,常常忘记给素源发通知。
总编辑以前在大学里是学历史的闵为革命的需要才搞了新闻。现在革命又不再馆要他搞新闻,他的兴趣侦又回到了历史。这次旅行,没有新闻采访任务。每到一地,他都问的是历史典籍,名胜古迹。到了这个县,他遇见的几位县领导都很年轻,又都上任不久,有的是从外县交流来的,有的是从地区专员公署机关下到基层来锻炼的。平时大约没有怎么在这方面留心。他一问,他们就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所云:
总编辑很含蓄地笑笑,说,你们这个县,我以前倒是有些耳闻的,有这么儿句民谚,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一门四进士,十里九布玫I还有,三状元,四宰相,六尚书,九布政,芝麻官,三斗三。说的都是这个县出的人,历史上很辉煌的呀,很了不起呀。
主管宣传文化的县委副书记一下被提醒:您老说的怕是董源。我听说那村盘子有座状元楼,还是宋朝留下来的呢。
是么
总编辑眼睛一亮:
你还没有见过?
没有
县委副书记的脸很惭愧地一红。
那好,我们看看去。
您老要去?很不方便的。
县领导们很为难。
我这回就是想走不方便的地方7总编辑不虚此行。他在茎源一住三天,临走还恋恋不舍地说,我还要回头的,苒来,至少住个一年半载。蹲下来,认真做点研究。董源是可以搲出一部巨着来的。回到省城,他立刻着手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向省委书记和省长汇报董源的人文古迹,历史文化及旅游的价值。把他们说得心向往之,当即表态说一定要去这个董沪看看;另一件是给省报写了一篇介绍董源的文章,称董源为再现于世的桃花源。文章的篇幅比一般报纸发的同类性质的文章要大得多,文字也极古雅隽秀。仅以文章论,至少总编辑自己私下觉得是一篇并不下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美文。文章的题目就是《新桃花源记》萤源自然随即就在省内有关各界引起了注意。
首先是董源所在的县和专区,听说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临董源视察,很快拨了专敕,给董源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以达乡政府所在的槊镇。先前县里的公路只到乡镇。从乡镇到董源连一条能走手扶拖拉机的路也没有。这个县和这个专匠都是吃补贴的财政,拨款修这条不足十公里的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公路,纯粹是挖肉补疮。
路修出来好久,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却一直没有抽出空来。乎生难得半日闲,比不得退休的总编辑有雅兴。省文化界和旅游部门倒是派过几回人来,由县里或是乡里的吉普车载到董源,总算没有太委屈这条辛苦并且忍痛修出的公路。遗憾的是,这些人并非《桃花源记》里记的南阳刘子骐那样的高尚士。他们之来,都是领导派来的,负有考察任务,原本就没有多少欣然规往的意思。来了之后,在村盘子上草草转一圈,便旋即登车驱返,满面是逃窜之色,全没有总编辑的那份热情洋溢。回到省城,自然是再没有下文。日久,总编辑发现的新桃花源,也便如同陶渊明当年记载的由一个渔人发现的桃花源一样,后遂无问津者。
省里没有人来,县里和乡里也就没有人可陪,也就没有去董源的必要。偶有人去,或是董源偶有人出来,也都是步行,走的是董源最早的先人走出的那条路,习惯使然。这样,专区和县两级联合拨款专门为茇源修的那条路,便重又为各类深深浅浅但一律霸蛮的草所掩埋。
在山里或乡下走陌路,记住两条,一是认日头判断方向二是如果同一方向有两条类似路的路,拣苹少的那条走。草少,正因为走的人多。
程志下乡以后,把这一类的乡村生活要决记了一大本子。去董源他自然选的就是草少的那条路。那正是人们进出董源惯走的路。严格的说,那不是路,是河床I更严格的说,连河床也不是,是山洪冲出的乱石沟。沟时宽时窄,没有明显的沟沿。若有,便是树,树是该省最常见的香樟4不过如此密集而蔚为壮观的香樟林子,全省也许不会太多。这里的香樟怕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层层叠叠,郁郁苍苍,一去十几甩。枝柯繁茂,隔沟相拥,将整条十几里长的山沟掩成拱形长廊。头上的曰脚难得穿透下来。偶然落下几朿,便在沟中间的浅水上面燃起一个一个光点,将那原本清净暗黑的水,映出一片一片请亮,使水所掩覆的卵石,如玉般晶莹。石间游鱼群聚,如逢盛会,或有倏尔远逝者,瞬间又倏尔回归。真正的怡然乐。
除了汩汩地在石间滑过的水声,除了间或的雀鸣和扑翅声,大山和谷地一片静穆。
程志且走且歇,似乎是满怀了珍怙地品味般地细心体察这静穆的美丽,仿佛害怕惊扰了它似的。总编辑那一次肯定走的是这条路,很可以理解总编辑当时尽力压抑着的兴奋。连程志现在都觉得,在沟沿以上的樟树沐子中间横蛮地辟出的那条公路,简直就是一逆刀伤,简直就是一种残忍。
这念头跟他此行的目的,是相悖的。
像程志这样刚刚离开学校的研究生,会自己提出到乡一级的基层来工作,听起来有一点离奇,离奇得让人生疑虑。很多年来,这个县的党政机关从外面调进干部是人事部门一件很棘手的事。调谁谁也不愔愿来,即便是提拔也要推三阻四。那些被硬性规定派下基层来锻炼的人,也常常千不满一年,便千方百计找关系调走。至于那些从县里高中考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更是没有一个分配回县的。一旦回来,便只是探亲,满脸是一副衣锦还乡的睥睨神色。因此当程志舆的拿着省人事部门的介绍信到县里来报到时,竟真的引起了怀疑。
分配之前,他原是同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表达过回来的愿望的。但当时他们都并没有把他的1,当真,以为他不过就是五分钟热血,跟他们套套近乎而已。所谓把一个乡交给他云云,也就是一种对他的不真实的热情的应酬罢了。他们很自卑,见不得人似的自惭形秽。这也难怪。县委书记是全国和省两级的人大代表。他们这个省的代表团在北京开会,不要说国外、海外的记者,国内的记者也从不打个照面,偶有走错了路的,听听不对头,起身就走,仿佛屁股上扎了刺。其实这个省的会议厅同别个省的会议厅,除了装饰风格不同,摆设的质量都是一个档次的。沙发或软椅上而决不会有什么让人坐不安生的异物。毎回要上北京了,代表们心里就怀了一个极其虔诚的奢望,这问能得到一点殊荣和关怀。结果往往被冷落。于是就有了哀怨: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啦;世上无钱难作人,有芯(心)无油总杠然啦,等等;也有很悦慨的,雄出确凿数字,说这个省曾经为革命牺牲多少人,作出过多大贡献,如今因为经济落后就如此得不到重视。总之是很悲哀,很伤心,很觉得自己没有地位,像一个弃妇。到了省里,也一样,这个县的代表更是没有发言的地位。每回都只有缩在角落里,坐冷板凳。要说,也只是你说给我听,我说给你听,等于把县里的会搬到省城开。说完了也就完了,听的人等于没听,说的人也等于没说。
因此,无论如何人们很难相信一个正正经经的硕士研究生,在外喾的名牌大学毕了业,会自己要求间到省里来;回到省里不留在省城,还会要求回到这么个县里来;回到县里,还会要求到这个县最边远的乡里去工作。
不能不警惕哟。
尽管有些惊奇,但是领导们对程志还是表现了足够的欢迎的热诚。让他先问家休息几天(程志的父母都在中学当教师他的要求,他们会认真研究,有了结果,就马上通知他。然后,他们不声不张地派了两名干部,去东方大学作了一次调查,了解程志是不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犯有什么错误。结果自然是很意外。东大方面对他们的这次调查也觉得很意外。说,我们不是在他的档案里写有鉴定的么,你们信不过?两个县里干部中负责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马上解释说,我们是为了郑重行事,对于部也对党的求业负责任么,我们县委的想法是要兎用他,决没有别的意思。回来的路上,他们议论,倘若程志与有什么问题,恐怕就出在生理上了。但这不属于他们考查的范围。
县委最后决定,满足程志本人的志拯。但鉴于程志毕竟刚从校门出来,尚缺乏农村甚层上作的经验,原议的祖任副乡长、独当一面工作怕是不够稳妥。还是让他先担任一段乡长助理,看看倩况再说。
铸躇满志、摩拳擦掌的程志早就按捺不住,听说了决定的当天就开了介绍信,漏夜赶到那个离县城最远的乡政府去报到。
他耐心在乡政府助理了一个月。他的助理只有一项内容,就是陪客。乡一级有乡党委I乡政府、乡人大、乡政协、乡纪委、乡民兵六套班子。每套班子都各有自己的迎来送往。或是从乡以上的机关下来的,或是乡与乡之间交流的,络绎不绝。程志是乡长助理,又没有成家,无论为公为私,是工作需要还是出了:对他单身生活的爱护照顾,每次有客,都少不了让他作陪。人们一片声说,能跟他这么个硕士坐一桌,大家都觉得不易,三生有幸,他要不肯入席呢,那就有摆知识分子架子、看不起泥脚杆的嫌疑(其实那些人都并不是泥脚杆,皮鞋比他的一双旧运动鞋光鲜多了。)
他回回都尽可能自然地令取同这些泥脚杆们打成一凡。但是他回回都觉得是在受刑。他听不得他们那些粗鄙的笑闹,更受不了他们久经磨练的奈迈酒兴。他又老克服不了幻,
心里的那份虚怯。不知为什么一上了洒桌,他就老觉得自己入了剪径的强人一伙似的。他来了没有儿天就晓得,乡几十名干部,连上个月的工资还因为县财政局拖欠着没有发下来。多年来,这已是常事。但乡里的火们从不以为意。每回张罗客饭的时候总是说,工资少不了的,饭也是要吃的。他很纳闷,连工资也开不出,怎么会有钱请客呢。有天夜里,他向乡里那个老会计请教(老会计老婆孩子都在作田,住在离乡镇很远的村子,他不常回去,夜里经常是他同程志守乡政府大院。)老会讣笑一笑,说,你放心,社会主义家大业大,哪里就会吃空了。行政费没有怕什么,不是有乡办企此么。乡办企业的钱不够用,不是还有上面拨的抉贫敉济款、老区开发款么。不要说吃喝了,就是楼也造得起的。乡政府先前是公社,是7个祠堂改建的,现今你看这楼,比先前的县政府还高大。乡长的吉普车也要换了,要换辆进口的轿子车呢,你不晓得?
程志觉得自己没有被说服。有一回县委书记到乡里来,他私下又向县委书记请教。回答说,不都是工作么,盖楼、买车子、开会、交流经验,也就是扶贫工作,开发老区的一部分么。你现在还不了解基层,慢慢你就会懂得的。基层工作的同志很辛苦的,不要只看见他们吃一点,喝一点,是他们在支撑着我们的政权啊。没有他们去蹦、去跳、去叫、去喊,春种秋收,粮棉油猪,就什么也谈不上,那你国家还指望谁呢。
县委记说着,拍了拍程志的肩,满含了体谅的笑的眼睛很分明地在说:小鬼,你还太嫩,太不成熟啊。
裎志很惶惑。就像一个初涉赛场的竞技手,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太无知,还是别人犯了规。终于钶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目前的这种日子,踉他先前的想象栢去甚远。他原是想脚踏实地在最实在的地方做几件最实在的事倩的。先前,他在东大积极参与其事的那个南方预测咨询开发公司所以失败,不就因为那是一个只见声势却不落实的海市蜃楼么!
但是乡长没有指派,他也就不好自作主张去过问一件事,或者去一个什么村子或企业。他们让他在乡政府熟悉业务,他也就只有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打转。闲时,偶尔去乡镇上看看,也是作为散步。他不想给人看出有知识分子的傲气、张狂,锋芒毕露,仿佛唯他是救世主似的。来了这些时,他也觉出乡下的事他确实知之不多,没有理由不夹紧尾巴作人。乡长有时候也带他下去。半上午出去,乡办企业的车间里看看,或儿丘田垅上转转,也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照例又是喝酒。一喝一下午过去,便又打道回府。回来直叫喊累死人、命苦之类。程志也觉得很疲劳。尤其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译种疲劳并不产生任何效益,甚至产生了负效应,也就没有价值甚至反而增加了消耗,他也就更觉得疲劳。
程志孤单而沮丧。静静的夜晚,他抱了书,却看不下去。听着从乡镇上传来的深巷的犬吠,窗子外面,露水在树叶上滴落的声音,他感到无边的虚空和沉闷。这虚空和沉闷又成为一种无边的实在给予他一种无边的压迫。使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而眼泪却被挤压得直往上涌。透过朦胧的泪眼,他又看见东大那片红杉林从树缝间漏下的月色。当时他告诉戴执中和况达明,他要回江西老家,他将担任副乡长。他是认真的,他跟他们谈到了神的存在一人如果没有神,没有形而上的东西,不能超越世俗的诂,那便是失落。他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一直沉默着的况达明忽然对他说:
你真小。我们其老。
但是现在,再这样呆下去,他也会老的。
程志终于下了决心,向乡长提出请求。他在帮助乡长整理文件的时候,见到好几封董源来的拫告。报告是董源村小学写的,荥源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都盖了章。同样的报吿有好几份,写于不同的时间,措词一封比一封急迫,说的都是一件事:董源村小学的危房需要赶快拨款整修,刻不容缓。
莫听他们讲得那么严重,‘刻不容缓’,屁!这样的报告他们前年就打了,真要‘刻不容缓他们今天还有人打报告?蓳源的屋我晓得,都是老屋,花了银两做的,扎实得很,新屋也未必有那么牢靠。他们要修危房可以,乡里没有钱;把报告都给他们转到县教育局去。
乡长凡事心中有数。开导郑重其事的程志:
你要信他们的话,他们能把你卖了。萤源人,我还不晓得!
要不,我还是去看一看……
程志试探着,他觉得这是一个走出乡政府院子的机会。
你要真思去,那就去看看吧。
乡长要接电话,有些顾不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