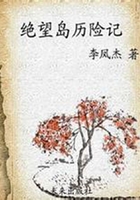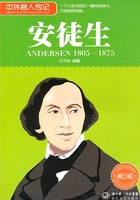历史系的人住在第四层楼。这里整条走廊黑漆漆,空荡荡,杳无人烟。仿佛是刚出土的古墓穴。这里的人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许消失在历史中了,戴执中调侃说。然而他们却在走廊尽头的阅览室的门脚缝中发现了一条极微弱的亮光。里面有人。
他们小心地敲起来。一下。二下。三下。门终于很不情愿地开了。是参加过那次秋游的两位硕士中的一位。看不清他的脸,但可以看出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在他身后,阅览桌上立着一支电筒,光柱直射天花板,在上面投出一个极大的光晕。电筒下面,是一包打开的已经掰晬的方便面。周围,是堆积得老高的大半圈又黄又灰的各类典籍。这位专攻春秋史的历史硕士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奴隶社会同封建社会分期新考的论文,其主旨在推翻这之前所有历史学家的现成结论。被故纸堆所深深掩埋的历史顼士声音嘶哑地请求程志谅解他的不能参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看样子你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啊。分期问题有什么可考究的?黑格尔的突变论可谓精致了,却对付不了一个简单的秃头间题。而分期问题是最大的秃头之一。况且,有了‘三次浪潮’理论,分期说还有什么意义?莫非你不晓得,所谓的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观,只不过是那位苏维埃的伊凡雷帝(系指斯大林)浪绎的结果么。
请尊重敝人的学术自由。
历史硕士安诤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戴执中一眼,声杳微微有些颤抖,然后他向那堆灰暗的历史陈迹退隐进去,重新闭紧了门。
戴执中已经微微喘气了,背心已经被汗沁湿。他开始失去耐心。算了吧: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治的了,研讨什么!下次你换个题,讨论爱滋病的防治,他们就会来了。走吧,找个人扯淡去。
还有谁好找呢?
程志很悲哀。
况达明不在吗?
戴执中最想见到的是自己的论战对手。
他在五楼。
况达明的居室门虚掩着,亮着烛光,戴执中一面喊着,一面就随随便便地一头揄进去。忽然怔住了。他看见一条美丽修长的光裸的腿从床上斜伸到地上。况达明则背对着房间,站在桌边正干着什么。听见人声,那条令人心惊肉跳的腿立刻抽了上去,床上蚊帐的门脸随即闭合。况达明回转身,并不持别意外,仿佛戴执中是预先约好了要来似的:
请进。住所是寒伧的,但心是伟火的。
况达明对戴执中躬了躬身:
阁下的名气很大了啊,它已经比你早到寒舍了:
临分配前,况达明所在省由省委组织部长和劳动人事庁长带队,组织了一个游说队到全国各高校的本省搭的研究生。
和本科生应届毕业生中开展说服工作,动员他们毕业后回省为振兴家乡出力。来东大时,劳动人事厅长还特地同况达明长谈过将近一小时,希错他能在东大的本省籍学生中起个带头作闱。况达明当时不知是哪根祌经奠名丼妙地被触动了,正式分配时,居然不顾艺术学院的女朋犮以绝交为要挟的反对,坚决要求问了自己的省。他原以为省报会为此而作出必要反应,然而他的还乡并没有引起任何注窓,没有任何人觉得他作出了什么栖牲。他由人事部门分到主管部门,洱分到省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又将他分到地处该省边缘县的一个分校。分校倒是重视他,没有把他分到教研室,而是留在办公室。他接受的头一件工作是为该校党总支书记誊写上一学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汇报。他连那个《汇报》的题目还没有抄完,抄着抄着忽然抓起笔猛然把笔尖戳在桌上,就那样把原稿也给钉在办公桌上,间宿舍收拾了行李,不辞而别,重新回到东大。东大当即就抜受了他留校的淸求(校方原先就有过这个考虑),人事部门派人去把他的一切档案、行政关系又调回来。
回来得太好了。我当时就劝过你,不要三分钟热血。
回来了又怎样,哼:
况达明两只眼睛通红,脸色却发青。他显然喝了过量的酒。他面前的桌子象个垃圾堆。凌乱的几本书之间,堆满了打开的和没有打开的罐头瓶、鎺头筒,造型各异的酒瓶子,以及散落得到处都是的碎肉块,发了霉的花生米,被筷子戳得稀烂的豆腐乳,吃剩的肉骨头、鱼刺,痕藉不堪。桌子当中,展开着一张绉巴巴的立纸,上面是一个斗大的酒宇。完全是象形的写法酉写成一个倾斜的长颈陶鎺,偏夯的三点,则是从陶罐口溢出的三颗酒滴。一片醉态朦胧。显然是刚刚完成的作品。
况达明递给两位不速之客一人一小盅酒:
人生不过是流浪,不停地从一个猪窝爬进另一个猪窝。如今的大学,教不知为何而教,学亦不知为何而学,混日子罢了。
他精神萎靡不振。
的确是混乱:戴执中的辩论欲又被激发起来,但是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却是必须的。可怜的中国人现在才想到了资本的原始枳累。代价肯定是惨重的,但是……
谢谢,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兴趣。我比不得你,你永远站在世纪的制高点上况达明无疑喑示了戴执中对上次行为的批评态度和那之后的诸多激烈表现。戴执中脸有些发烧(别人可以理解为酒力所致),但他今天是执意为友好而来的,他打了个哈哈:
我还不知迫阁下你么。愤世嫉俗,这并不是你的真实面貌:
真实?什么是真实?唯一的真实乃是无意识,而整个理性世界不过是一个白痴讲述的荒诞故事,充满了喧哗、愤怒,却又不意味任何东西。
难怪斯威夫特说,‘怨言是上帝得自人们的最大贡物,也是人们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戴执中心平气和。
床上的帐子里,一个香港歌星呼天抢地的号叫越来越响。况达明暴怒地扭头对帐子吼道:
--让那个呜咽不休的香港佬闭上臭嘴吧,他的舌头该帀沫布擦一擦了。
可是音响却反而开得更大,那个香港佬更高亢更悲怆地喊叫起来。显然,那代表着一种抗议。
况达明磨着牙齿,脸一阵痉挛。
走吧,我们出去。
锨执中马上就站起来。他一直被那条美丽修长的羌裸的腿球动得心祌不安。
电还没有来。水电管理处值班的人也许忘了把闸刀推上去,也许根本就没有人值班。又是长长的幽幽的走廊,长长的幽幽的楼梯,这么长,仿佛没有尽头。
数学系的麻将依然推得排山倒海般的响。
下过水吗?
戴执中问,他想换个轻松的话题。
下过。尽输。
况达明回答。
那是合乎规律的。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鸡巴毛!
况达明忽然狠狠地说了一句粗话。他很烦。艺术学院那位公主把他的重返东大看作是对她的屈服他想要摆脱她,但是她却告诉他,她怀孕了,刚刚能坚抟到毕业而不暴熔。
人的存在处境无非是一连串的绝望,桀运,无稽。
况达明自怨自艾。他觉得自己就象大海里的一商水,去寻找另一滴水,结果找来找去却在一片茫茫大海里失掉了自己。
他们重新来到研究生会小会议室程志掏钥匙的手忽然停住了。三个人一起听见了从里而传出来的尽管压抑若却仍是那么忘情那么狂乩的喘息和呻吟。
只好蹑手蹑脚地退避三舍。
他们怎么进去的?程志很纳闷。小会议室只有两把钥匙,研究生会主席一把(现在在他手里),宣传部长一把,而宣传部狡有自己的房间。
。再简单不过了。况达明指着小会议室面对他们的那扇窗户(他们站在离窗户不到五米远的山坡小道上),仔细看看窗棂,
窗棂是直径。毫米的钢筋。其中两根早已向两边弯曲,留出的空隙刚好可以钻进一颗人头。头能进去,身子也就能进去。这类事况达明曾经屡试不爽。
爱愔使钢铁变形。
戴执中赞叹。
程志记起来,今晚七时半到八点之间,有两个人在那窗下技吻。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世界上什么都可能缺乏,但永远不会缺乏爱神。
不妨说,这就是你打算研讨的论题的最佳答案。
况达明瓮声瓮气地对程志说:
骑士时代过去了。人们如今更多的只是关心自己。何必在自己的肩膀上压上一些想象的担子。还是少些深沉与博大、少些沉重与忧患的好。何苦来哉!记住哈维考克斯的话:我们如此狂热寻觅的东西,可能最终只是那匹我们一直在骑的马。
一点也不错:戴执中附和说,人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休谟说,是价欲和虚荣心。比他早得多的东方圣人孔老夫子也承认,吾未见好徳如好色者也。你在这里等待戈多,戈多却是永远不会来的。
不对。程志抬起头,从树缝间漏下的月色,照出他眼睛中的泪光,即便是《等待戈多上也讲到了神的存在一人如果没有神,没有形而上的东西,不能超越仳俗的话,那便是失落:
寂静。
风在红松林打着唿哨。说真的,毕业你打算去哪里呢?
过了好久,戴执中问。他忽然动了念头,希望程志到他那里去。
我已经跟我们县里的头头说好了,他们打算把一个乡交给我,
当乡艮?广先任副乡长。
而且是江西?老区一切实实在在地从头开始,倒是不错的。可是上途漫漫啊,等你一步一步爬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得到什么时候?我没有这样想过。
-直沉默着的况达明注视着这个小个子的江西老俵的小白脸,忽然说:你真小。我们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