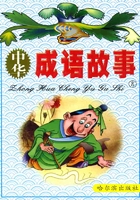人都走光了,尹敏还留在洛室里。外面,烧锅炉的老头把那扇摇摇欲坠的烂铁门踢得蓬蓬响广里面还有人么?到时间了。
尹敏却没有听见。她在专心致志地阅读着自己。象仓库一样大且高的浴室空荡荡的,所有的水龙头都关闭了,把满世界弄得一片混沌迷离的蒸气消失了,没有汾刷过的黑色的腑壁丑陋地裸露出来,尹敏也裸露出来。尹敏好象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开头几回,她在浴室的外间怎么也不能撤下那最后的三点,遭到一苒的抗议和攻讦之后,才不得已完全解除了武装。但总是慌慌张张地钻进去,闭着眼晴上上下下胡乱抹一气,又慌慌张张地逃出来。她怕看赤裸裸的别人,这使她想到别人也是这样看赤裸裸的自己。她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别人在看赤裸裸的自己时的惊羡,以至妒嫉的表情。
自己原来是这么好看。一片安静的白,白得凝重,稠,象一支雪糕。每一个毛孔都吸饱了水,湿津津的茸茸的散发着香皂气息的汗毛就象夏天的暴雨过后山坡上悄悄生出的嫩草,在高高的乳房上闪闪发亮。乳房在轻轻地颤着。那是刚刚毛巾滑过时引起的。乳房颤动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佥身都跟着动了一遍。它很沉重,在全身的重量中占了相当的比例。
它又很结实,几乎象束在乳罩里的时候一样挺。乳头很小,很鲜艳,象一颗熟透的草莓。难怪况达明会那么粗暴,根本不管她会不会感冒,根本不管春天晚上的树林子的潮湿以及那么重的寒气,拉脱了她的乳罩的扣子,把头埋下去,老半天也不抬起来。
从被散在肩膀的头发上流下的水滴,不断地滑落到乳房中间很深很窄的谷底,在那里汇成一条透明的溪流,无声地缓缓地流下去,流进深不可测的肚脐。然后她看见了自己的两条腿,居然会有这样长这样直这样饱满的腿,并拢了,从上到下没有一点缝隙。
瞎。什么地方尖利地沙哑地响了一声。
尹数吓了一跳。抬起头,看见自己正面对若的两片毛毯败的门帘中间夹着的一颗头。那其实不象一颗头,象一颗放大了的蜜枣。是管浴室的那个老女人的头。
嗜那声音又尖利地沙哑地响了一下。那是一种含着敌意的恼恨的嘲风。只有仅仅剩下了惆怅的老女人才会这样嘲讽,似乎是被她嘲风的人抢劫了她的青春。
尹敏一下侧转身子,拚命抱紧了双臂,脸上象火一样烧了起来。那个老女人却带着一种阴沉的微笑盯住她,不肯离去,使她这一辈子都永远不会忘记一颗夹在两片灰黑色的门帘中间的蜜枣。
尹敏穿好衣服走出浴室的时候,一点松决和喜悦的感觉也没有了,心里沉甸甸的,那张老女人的脸老在她面前闪着。很顽强,很恶毒,幸灾乐祸,又仿佛是一种威胁。让她明白她刚才从自己身上看到的一切会消失到没有一点影子,她也会变成一个老女人,有那样难看的一颗头,象个蜜枣。
她已经被拒绝两次了。还能被拒绝几次呢?她已经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当然并不可怕。但是爱情,并不是在预定的时间里就可以找到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规定时间完成,只有爱情不行。
第一次被拒绝的时候,她没有现在的这种惶惑。只觉得有一点委屈。他们从小学一直同学同到高中毕业。她对他的喜欢是认真的,可是他却无所谓。算了吧他满不在乎地说,把她的一张扎着幼儿园时蝴堞结的照片塞还给她,就转身走了。她到大学里来以后,一再给他写信,劝他接着考。他一封信也不回,一直到去当兵。他留在她记忆里的还是一张孩子的脸,精瘦精瘦,眼睛又大又圆,头发一天到晚乱蓬蓬的象鸡窝。
后来就是况达明。
开始,他很温柔,很迁就。每天耐心地等她下晚自习,然后就在树林里呆半小时。
半小时?
你还想要多少呢?这是她在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上精心地计算出来的半小时。
真小气。
有什么办法呢。她怯怯地说,含着恳求。
只有春天的那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忘记了时间。她听任着他灼热的抚摸。月亮从树林的枝叶之间射下来,在她眼睛里照出一片迷茫昏乱。过后她很后悔第二天晚上再也不肯跟他坐到那棵折断的树干上去。
就这样散散步吧她提防着。
你真是。况达明的鼻息又粗又重,声音干巴巴的。
你生气了。
这个不可更改的半小时,是他们恋爱生活中不可逾越的法律。他们中途去参加舞会,到了半小时,不管舞曲是否结束,她也是一定要走的。即便是月全食,哈雷彗星,都不能挽留她一分钟。她对时间的感觉的准确是惊人的。只要她一枱手,况达明就只能是绝望。你被时间奴役了,况达明终于失去了忍耐。时间把你分割成刻板的碎块,你就用这些碎块去拚凑女硕士、女博士。祝你走运。
当时,她满心激动地告诉他,系里决定推荐她攻研究生,以为他会欢喜。结果却导致了他的爆发。她在树林的黑暗中惊惶地睁大眼睛,不知所措。
无机盐!他愤怒地说,然后就摆脱了她的手。
她怔怔地呆了一会儿,才明白广无机盐是指她。那是她的专业范围。
第二天一也就是昨天晚自习以后,他没有在树林里等她。她摸着黑,跌跌揸搐地穿过树林,到研究生院去找他。人家告诉她,况达明到隔壁的艺术学院去了,那里有个系今晚举行通宵舞会。怎么,他没有告诉你?告诉她的人很奇怪。
今天吃过了晚饭,她就去找他。他寝室的人说他上午就走了,到城里的一家化工厂去捻调查,今天可能回,也可能不回。
她想:他是在回避她。她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一种巨大的空虚。不象上一次,仅仅只有一点委屈。她回到自己的寝室。寝室是空的,人都上晚自习去了。她觉得身上冷。便歪到床上,用毯子连头粲起来,又觉得透不过气,又爬起来。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忽然生出洗澡的念头。
还不到下晚自习的时间,路上没有人。她的有气无力的脚步声听起来很响。她走得慢。平时,她总是觉得路长,时间不够。今天夜里相反,路好象太短,时间太多。时间留出了一大片空白。她已经习惯了在路的一侧,那条仲进树林的小路的岔口,有况达明在等若。现在,那里不会有况达明了。时间一下子变得没有了意义。要是没有况达明,全部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每天只留给况达明半小时,实际含猗一种信赖,只是况达明不觉得罢了。她明白,她娃无论如何离不开况达明的了。要是只能在研究生和况达明之间作一种选择,她选择况达明。为了况达明,她应该什么都可以辆牲。况达明是可以理解的。研究生院开舞会,倍受冷落的是研究生院本身的女生。男生在作爱情选择的时候,学位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倒是一种障碍。谁叫她是女生呢。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上,大龄未婚妇女中,比例大的正是知识女性。
路两旁的玫瑰开得茂盛。凤把落得满地的花辩卷到路中间来,在明宪的水银灯底下,什么都显得发白,很难看。落英缤纷,引起的只是伤感。
白格生生的脸蛋,
水灵灵的限,
有这样的好东西,
为不住哥哥。
男生宿舍楼那边,那个山西辂的家伙又在怪里怪气地吧那支家乡民歌。他几乎天天吧这支歌,好像是他唯一会吧的一支歌。但今天听起来,却好象是专门为她吧的。那是灼热焦跺的青春的咏叹。
明天一定要找到况达明,要跟他说,她不打算攻研究生了。她的时间表也要改变。早上不一定非要四点半起来,晚上也就可以有比半小时多得多的时间陪他。今夭晚上,她就没有上自习了。这样想着,尹敏轻松了许多。
她在照着月光的床上躺下去。月光静静地浸润着她的身体。她又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那两个高高挺起的乳峰中间的那个深深的峡谷。她又想起春夭,那个树林里的那个迷乱的夜晚。盼上热起来。后来她很甜蜜地睡转了。
第二天早上尹敏腌的时候,表上的指针指箱四点半。晚上她文去上自习。之后她在树钵里独报桓了半小时。
好多天之后尹敏在路上偁然碰见况达明,况达明和一个娇小的女孩子走在一起。他向尹敏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艺术学院表演系的。
红杉社的人们对于况达明的轻率不无嫉妒地加以谴责。他颇不以为然。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爱情这裉刺是属于青春这朵蔷薇的。只要我们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在青春时期就少不了犯这种过错。也许当我学会如何回避自己性格中的脆弱与荒唐的时候,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费我已经部分地死了。
典型的Blackguard(无赖)逻辑。戴执中义愤填膺,这就是阁下你弘泰的道德传统么!
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况达明不屑争执你们去挑剔好了。我相信一切也蔑视一切,谈不上有什么玄学上的坚定性。象我这样一个人成为批评家们的圣塞巴斯蒂恩(罗马殉遒者?一一二八八)是很自然的琪。
他并且赋诗明志:
跟骷髅接吻
跟毒蛇拥抱
我向世界宣布
我有我自己的嗜好
在棺材里睡觉
在薄冰上停留
我向世界宣布
我有我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