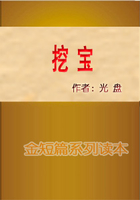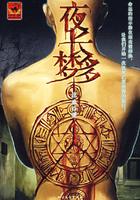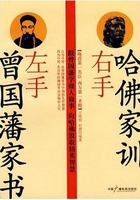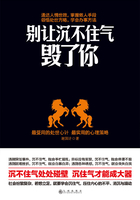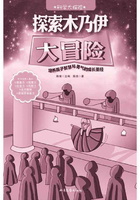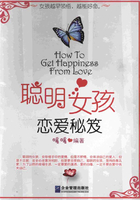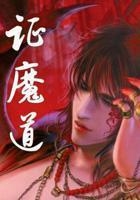■文/杨叛
“量心尺,阎罗旨。强人崩,恶人死。”
量心尺为玄铁所制,长一尺五寸七分,宽两寸七分,重八斤二两三钱。其形如简,不发则已,发如雷霆,是江南第一神捕、锦衣卫百户柳天成的成名兵器。和寻常铁尺不同,量心尺上细分刻度,当真可用来作尺。盖因柳天成为人心细,多谋善断,最喜计万物大小、量人心短长。
虽然柳天成平生破案无数,可若论血腥诡异,当首推庚子年三月徐州府的连环杀人大案。此案之扑朔迷离、匪夷所思,也是其四十三年捕头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也许十年前那起库银大劫案更为复杂凶险——在一尺将巨盗七窍天妖方无诡打下悬崖之前,他险些被方无诡布下的机关取了性命——可和本案一比,却又显得云淡风轻了。
最初案发是在府学明伦堂,死者是学正上官图。上官学正性情刻薄,在士林中口碑极差,若非有一手押题绝活,早被裁撤了。案发当晚,上官图独自在堂内研经。三更时分更夫去查看时,发现他倒在书案边,胸口插着一把铁尺。铁尺上穿了张纸条,上面用小篆写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明伦堂内,柳天成摩挲着量心尺,慢慢踱着步,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他的步子稳而准,每一步都是一尺五寸七分,刚好是量心尺的长度。这样的走法,总能让他产生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奇妙感觉。
半个时辰后,他微微皱起双眉。
凶手显然是个老手,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尸体位置判断,上官图当时正在堂上秉烛夜读,凶手从大门单刀直入,不待上官图起身,便掷出铁尺,杀人后旋即遁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仵作的验尸格目标得很清楚。死者伤在心前肋上,铁尺斜深透内,有血污,是要害致命身死。死者身上并无挣扎痕迹,双手也无伤痕,显然凶手是趁其不防,一击致命。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尸身腰间,那里留有半截红色丝绦,从断口处看,显然是被人扯断的。他当即叫人问过,果然死者身上少了一块随身玉佩,上面雕了老君骑牛,但雕工粗糙,玉质低劣,并不值钱。
柳天成闻言有些失望,看来有价值的线索便只有那把铁尺和上面的纸条了。凶手手段既然如此老辣,为何又要留下那张纸条呢?
柳天成来到书案前,案上摆了几卷四书,还有一册书半掩着,柳天成随手翻开,却是成祖所撰的《为善阴骘》,翻开的一页特意用朱笔描了红:“且人之阴骘固无预于天,而天之所以报之者,其应如响。”
柳天成皱了皱眉,将书合上。
上官图的遇刺身亡,让整个州府都骚动起来。城门封闭,鸡飞狗跳,大街小巷里充斥着鹧鸪般嘀咕的闲人,六扇门的公爷们不断闯进一家家客栈酒楼,将各色可疑人等投进大牢。
“过了,过了,没必要大惊小怪。”知府李余山手捋长髯,慢条斯理道,“案发在明伦堂,又没有失窃,想必不是入室偷盗的强人所为。上官学正治学严苛,平日里得罪的学子不少,定是有人心生不满,这才起意杀人。柳捕头,你怎么看?”
“若是寻常凶案,行凶当用匕首,何故要用铁尺?且是玄铁造的铁尺。”柳天成端量着手中的凶器。铁尺的大小形状和他的量心尺一样,同样是玄铁所铸,甚至连重量也一般无二。若非量心尺此刻正笼在袖中,连他也会误认这是自己的兵器。
“也许是凶手有意栽赃给柳百户?”李知府沉吟道,“尽管放心,本官断不会为这小小伎俩所骗。”
“多谢李府台。不过若是凶手要嫁祸于我,那这张纸条该如何解释?”柳天成扬扬手中沾血的纸条。纸条长五寸七分,宽两寸二分,字迹六分见方,骨力遒劲,颇有火候。
李余山不露声色地向后避了避:“是时文题目吧?上官学正押错了府试的题目,故惹来杀身之祸。”
“这也是一种可能。无论如何,上官学正的被杀肯定和这张纸条有关。大人想必知晓纸上的这句话出自何处吧?”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盖因人之不知己,反而自省我之不知人,此乃仁恕之教也。”
“我记得《卫灵公篇》有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究竟是患不知人,还是患其不能,圣人真正的心意也是颇堪玩味呢……”柳天成笑道。李知府皱了皱眉:“这凶手当真可恶,乱用圣人之言,但愿柳百户早日抓到杀人凶徒,以安民心。”
“这是自然。”柳天成淡淡一笑,告辞而去。
是夜小雨,窗外竹影婆娑,独坐灯下静读,也别有一番雅趣。小妾红娘捧了新沏的紫笋茶上来,然后静静坐在一边,用一块红绸轻轻擦拭着那把量心尺。
柳天成温柔地望了爱妾一眼,翻开《论语集注》,在《学而篇》中找到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句的注解,轻轻读道:“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言罢闭目沉吟。
恍惚间,疾风借雨潜入房中,烛光摇曳,壁上的影子无声地化作妖魔。夜雨溟蒙,沥沥地笼住了徐州,连那一声凄厉惨叫也被雨声淹没。
丑时,第二起凶案发生在城西上清宫。
松色苍苍,生满青苔的巨大石龟驮着残碑,静静望着颌下的尸体。
死者是上清宫的庙祝白溪道长,死状和上官图一样,胸口插了铁尺,为要害致命身死。唯一不同的是纸条上的留言——“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白溪道人出身名门龙虎宗,身高七尺,眉目疏朗,相貌堂堂。除了和一些进香的富贵女眷有些不清不楚外,平日里斋醮布道,画符施药,在本府是小有名气的活神仙。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方外人莫名其妙地被杀,凶器又同样是铁尺,街头巷尾顿时多了不少闲话。免不了有好事者阴阳怪气地将此事扯到柳天成头上,说什么“量心尺,阎罗旨。士人崩,道人死”,居然也有听了嗑着瓜子喝彩的。
柳天成对此无动于衷,一边检查白溪的遗物——一把松鹤檀香柄马尾拂尘,一个紫铜三清铃,一枚黄花梨刻法印,两串铜钱,几角碎银,一册《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一边专心揣摩凶手的留言。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出自《黄帝阴符经》,并不难解,本意是说人心所思所想都来自对万物的认知,可也正因如此,心思必受万物所拘,不得超脱。而物之障心则从目来,目有所见,心即受之,心不可见,因物而见,见物即是见心。
见心?见谁的心?见物?所见何物?柳天成双眉紧锁。
上次是儒门圣训,这次却是道家经典,二者间并无联系。而上官图和白溪道人一为饱学儒士,一为道家高人,两人素无往来,又从何处招来了杀身之祸?一般来说,杀人动机不外乎仇杀、情杀、见财起意、争权夺利、失手误伤等等,可这两起案子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两个死者虽也都和人有怨,却没结过什么深仇大恨。两人一为年过半百的老人,一为出家人,情杀也不大可能。两人虽然都小有身家,被杀后家中财物却没有短少。至于争权夺利和一时失手,就更加说不过去了。找不到动机,自然就推断不出凶手身份,而这也是最让人头痛的情况。
身后有动静,听脚步声,步子间距应在九寸八分,除了红娘,无人有这样纤巧的足迹。
“先喝杯茶,醒醒脑子。”果然是红娘又来奉茶。
“你弟弟的病可好些了么?”柳天成啜了口香茶,随口问道。
红娘的弟弟当年流配边军,在西北熬坏了身子,这些年一直不见好,最近几个月更是卧床不起,看来很难熬过年关了。
“昨日请城东的李大夫又看过了,只说要服药调理,不能受寒,又开了新方子。过几日我要去卧佛寺进香,都说那里的菩萨灵验,希望能保佑弟弟渡过此劫。”红娘轻声说,显然对病情已不抱太大希望。
“去吧,我和忠叔说,到时多带几贯钱。卧佛寺的和尚眼界可是高得很呢。”柳天成微讽道,又指了指桌上的纸条,“红娘,你怎么看?上官图和白溪道人究竟为何人所害?”
“我又不是公门差人,如何晓得?相公平日断案如神,所破大案无数,怎会被区区两起命案难住?”
“断案如神?”柳天成苦笑,“我又不是真的神,总有解不开的难题啊。现在为夫连两人因何被杀都弄不清楚,破案又如何谈起呢?”
红娘轻揉着他的肩膀:“既然如此,相公何不出去走走?以相公的眼光,总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吧?”
柳天成一愣,随即失笑:“倒让红娘提醒了我。出去查访,总要好过在家中胡思乱想。”说完拍了拍红娘的小手,揣好量心尺,洒然去了。
说是查访,该做的早已做过了。死者的亲友、弟子、同门都已一一问过,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柳天成并不死心,他沿着府学向上清宫一路行去,每过商贩店铺,便驻足问上几句。
辰时,柳天成打听到了消息。
提供消息的是四海绸缎庄的李掌柜。身高八尺,大腹便便的李掌柜是四川人,官话总说得带着丝喜庆味儿。据他说,白溪道人遇害那天,他曾经看到有个贼眉鼠眼的小个子跟在道人身后,一直向上清宫去了。李掌柜认得那人叫高飞,是城东一个小有名气的泼皮,剪绺儿的高手,不过倒是很少见他来城西混。
没费多大力气,柳天成便在其姘头花如玉家里堵住了这个小贼。当高飞哆哆嗦嗦地从床下爬出来时,风骚入骨的花如玉正抖着一身雪白的肉在被子里吃吃地笑。
“小的跟着那道人,不过是瞄上了他腰间的一块玉佩,剪个绺儿。哪里又会起意杀人了?白溪道人可是龙虎门的高人,能降龙伏虎,伸个手指头都能把小人捻死,小人又如何敢起歹意?”高飞抱天屈地嚷着。
在柳天成看来,身高不过五尺二寸的高飞分明是只黄鼠狼,自然不会信他的一面之词,当下冷笑一声:“你倒是敢起意偷高人的玉佩。”
“这……”高飞微一犹豫,咬牙道,“不瞒大人,这玉佩不是小人要的,而是有人出钱请小人去偷的。”
“哦?是谁?”柳天成双眼一亮。
据高飞说,托他偷玉佩的是个中年汉子,四十出头,五官丑陋,左脸颊上有个铜钱大小的青痣,声音沙哑,凤阳口音。对方在得意楼搭上了正在吃酒的他,请他喝了二斤花雕,又出两贯钱请他去偷白溪道人的随身玉佩,事成后另有重谢。舌头已经大了的他当场便拍了胸脯。
“玉佩呢?可曾交给那人了?”柳天成急问。高飞略显郁闷:“早交出去了,第二天在得意楼交的货。不过是个普通的如来佩,照小人看值不了二两银子。”
“那人当时说了什么没有?”“那人当时很是高兴,小声念叨了几句,好像是皇帝什么的。”高飞回忆道。
柳天成心中一震,沉声道:“可是黄帝阴符经?”“对!对!就是黄帝阴符经!”
终于连上了,柳天成双目微合,长出了一口气。迷雾就这般乍然明朗。上官图死后被人夺去了老君骑牛玉佩,白溪则在死前被盗了随身的如来玉佩,二者必有关联!
嘴里嚼着张家铺子的水晶红枣蜜,柳天成仔细端详着面前的纸条。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是儒家圣言。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这是道家至语。
失踪的两块玉佩,又分别雕了道宗佛祖。这其中究竟有何奥妙?
佛家,道家,儒家……对了!上官图临终前书案上有一卷《为善阴骘》,而白溪道人身边则揣着本《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这两书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三教合一,劝人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