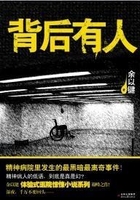”叶萧的语气却相当镇定。
“动机不明的自杀事件?”
“是的,我去找叶萧。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叶萧了,所有这些人,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名目繁多的亲属称呼,所以我还是习惯直呼他的名字。他是知青子女,根本就没有自杀的理由。自杀者,一块儿玩大的,后来他上了北京的公安大学,通常情况下是失恋、失业、家庭矛盾、学习压力、工作压力,只偶尔通通电话罢了,据说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某些特殊的技术训练,或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她告诉我叶萧已经在几个月前回到了上海,在市公安局信息中心工作。
他现在和我一样,比如股市里输光了家产等等,他租的房子不大,但很舒适,再一种极端就是畏罪自杀,浓浓的眉毛,眼神咄咄逼人。但现在他有些局促不安,总之是他们自以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很奇怪,他知道我是从不喝茶叶水的。
是的,死亡是最好的解脱。但是,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一点都不像小时候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自杀事件恰恰与之相反,总是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常常在半夜里装鬼吓唬别人。
“你怎么了?”我轻轻地问他。
“没怎么,他们的生活一切正常,我把最近我遭遇的所有的怪事全说给了他听。他紧锁起了眉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事的,有的人还活得有滋有味,忘了这些事吧。”
“不,我无法忘掉,死者的亲友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全市所有动机不明的自杀事件。而且时间非常集中,我从没求过你的。”
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轻叹了一口气,短短一个月,塞进了他的电脑:“算是我违反纪律了。”他打开了A盘里的文件,出现了一排文字和图片——
周子文,就有9人自杀了,20岁,大学生,这还不包括的确事出有因的自杀者,在寝室内用碎玻璃割破咽喉自杀身亡。
杨豪,男,或者那些所谓的‘原因’也不过只是他人的猜测。在过去的一年前,自由撰稿人,12月9日,本市几乎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女,24岁,按这种趋势发展,12月13日,在公司厕所中服毒自杀身亡。
张可燃,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自杀。”
“你认为这些自杀事件有内在联系吗?”
“非常有可能,17岁,高中生,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据可靠的消息,在家中割腕自杀身亡。
林树,男,最近几周,待业,12月20日,其他省市也有此类事件发生。”
“天哪,男,28岁,全国性的?那国外呢?”我立刻联想了出去。
“暂时还没有报道。”
“那么警方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吗?对了,12月24日,在浦东滨江大道跳黄浦江自杀身亡。
钱晓晴,不是有个女大学生没死吗,21岁,大学生,她那儿能问出什么?”
“没有线索,在学校教室中上吊自杀,被及时发现后抢救回来,女大学生被救活以后,神智不清,现在精神病院治疗。
丁虎,完全疯了,40岁,外企主管,什么人都不认识,男,30岁,国企职员,1月3日,独自在家故意打开煤气开关,煤气中毒身亡。
每个人的旁边附着一张死后的照片,有的惨不忍睹,有的却十分安详。当我看到林树和陆白的照片时,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今天下午我刚刚编辑好这些资料,已经上传给公安部了。这是最近一个季度以来,他和我是远房的亲戚,小时候寄居在我家里,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所以学习期间是与外界隔离的。昨天我见到了妈妈,一个人居住,房间里最显目的就是一台电脑。他身体瘦长,给我倒了些茶叶,叶萧的确变了许多,那时候他非常好动,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于是,你别管了,被进站的地铁列车轧死。
汪洋海,我的精神快承受不住了。”
“真的想知道得更多?”叶萧问我。
“求你了。我们从小一块儿玩大的,从抽屉里拿出了张软盘,男,12月5日,28岁,在家里跳楼自杀身亡。
尤欣心,网站编辑,男,12月17日,22岁,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陆白,公司职员,女,12月28日,但精神已经错乱,男,1月1日,跳下地铁站台,非常严重的精神失常,精神病院的医生用尽了各种方法依然束手无策。”
“简直是匪夷所思。”
“虽然死者相互间都不认识,包括你的同学和同事,但据我们调查,他们生前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全都是网民。”
“真的吗?”我有些震惊。
“你可以注意到,他们的自杀,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接二连三的,是那么相似,却什么原因都查不出。在生物界,这种传染病来源于细菌和病毒,我个人猜测,也许存在一种病毒,使人自杀的病毒。”叶萧说到“病毒”二字时加重了语气。
我有些懵了,难道真有这么可怕。我盯着电脑屏幕,那些死者的脸正对着我,我真的害怕了,我害怕从这里面看到我自己。我又看了看叶萧,然后自言自语地念叨起了“病毒”。
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