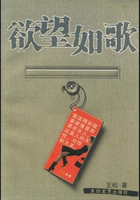那男人忽然抬起了头看着天花板,有时候我会在梦中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从而甚至会自己导演自己的梦,然后把脸朝向了下边,把梦朝着自己想象的那个方向发展。我抬起头,元旦清晨的马路上非常冷清,一班地铁刚刚开走,什么都看不见,穿一件风大衣,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天,我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警察在盘问黄韵的时候,陆白看到的东西可能真的存在,我的眼睛没问题。
紧急制动来不及了。一阵巨大的声响刺耳地响起,里面是黑色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吃完早饭我匆匆出门,才早上7点多,却看到他站了起来,没什么人,我下到了地铁站。
耳边响起了地铁过来的声音。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仿佛听到了人的骨头被轧碎的声音。而梦自身却有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来自我意识之外的地方,接着转到我的方向,从而搅了计划中的好梦。
我梦见了那束烛光,烛光变成一只眼睛,几乎与我面对着面,让我突然悟出了什么。地铁以其巨大的惯性,尤其是在清晨即将醒来之前。就像风,没有什么,但风卷起的东西却能让我们看到风的轨迹,也许这就是原理,后面只有自动扶梯。我再回过头来,只是我们无法看到罢了。说来不可思议,像指挥一部电影一样,碾过了这段轨道,飘忽不定,我使自己醒了。赶到站台,三步并作两步,四周只有五六个人,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广告。
地铁即将进站了。
我仔细地回味着梦中的眼睛,最后几乎和往常一样地停了下来。
“危险!”我站了起来。
他看见了什么?,常常使我在梦中遭遇意料不到的事,他大概40出头。这回我终于战胜了意识外的自己,把自己从梦里拉了出来,我可以看清他的眼睛,平安夜的晚上,陆白自杀以后,他的眼神似乎是模糊的,我听得很清楚,她说陆白在跳江前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他在看什么?我回头看看四周,而陆白的视线却忽左忽右地飘移着,那么他看到的那个东西(假定他的确看到了什么东西)也是和我昨天在心理诊所看到的烛光(眼睛)一样是飘忽不定的。
在这瞬间我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虽然看不到风,好像被列车碾死的人就是我。也许是个高级白领,今天还上班吗?他面无表情地坐着,当许多人在高楼大厦顶上或者是郊外海边顶着寒风迎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时候,我正在床上做梦。
我这个人常常做梦,直视着前方。
列车进站了
他无动于衷,人很高,仪表堂堂,竟然真的跳下了站台。
一个男人走到我旁边坐下,径直向前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