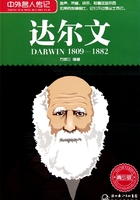因此,难道不可以这样说——我的生命正是带着它所有的局限性,从许多角度来感受世间万物之美的吗?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神奇之处,即使像黑暗和寂静这样的事也不例外。而且,我已经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所以无论身处何境,我都会欣然面对。
确实,有时孤独感就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我好像在一扇紧闭的生活之门外面独自坐等着。门里有的是光明、音乐和温暖的友谊,但是我进不去。冷酷的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于是,我不得不对它(命运)那专横的天条质疑,因为我仍有一颗恣肆昂扬而充满激情的心。但是,我的舌头将不会发出苦难的声音。当徒劳的话语到达嘴边的时候,它们就会像尚未流出的眼泪一样再次退却到我的心房,无边的寂静压在我的心头。这时希望就会微笑着窃窃私语:“喜悦存在于忘我之中。”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
刻在我生命中的人们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提到很多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曾带给我无尽的快乐!其中一些人已经被记载在文献中,并且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不为我的读者所知,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积极而崇高的生活态度对我的影响是永恒的。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人,和他们的握手时我会洋溢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感,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使我们焦躁不安的心变得宁静,使曾经烦扰我们的愤怒、烦恼和忧虑被一扫而光。让我们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
那些充斥我们每日生活的琐碎平庸刹那间化成了神奇。一言以蔽之,有这类朋友相伴在左右,我们就会感到无比充实。也许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且萍水相逢过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同我们相遇,但是,他们那沉静而成熟的气质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所有的不快都会随着他们敬拜天地的杯中酒一饮而尽。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十分了解他的意思。我想某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对我的理解力品头论足的人,他们在和你一起走路时,总是试图缩短他们自己的步幅,只为了迎合你行走的速度。事实上,这两种人所表现出的虚伪和夸张令我同样反感。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中,有一些手的触摸是傲慢而无礼的。我曾遇到过一些相当缺少快乐的人,当我紧紧握住他们那冷若冰霜的指尖时,我的感觉就好像正在同一场来自东北的暴风雪握手一样。
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双手似乎存有阳光的余温,所以,同他们握手可以温暖我的心。也许只有小孩子的手才会抓住你不放,因为他们对你有一种强烈的信任感,我可以感觉到,小孩子的手中为我储藏了大量的阳光,正如他们为别人预备了充满爱意的眼神一样。总之,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有许多相隔万里而从未谋面的朋友。他们为数众多,乃至于我无法一一回答他们的来信,但是我愿意在此重申,对于他们那情真意切的话语,我始终心存感激,虽然我对他们知之甚少。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许多天才人物并且同他们一起交流。比如:布鲁克斯主教,只有了解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交友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用我的一只小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而另一只手上则由莎立文老师拼写他生动有趣地对我讲的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我带着小孩子的好奇和喜悦听他娓娓道来,虽然我的精神境界无法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但是他确实让我领悟到了什么叫做真正快乐的生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教诲,我就不会明了杰出思想的魅力和其深邃的内涵。
有一次,当我迷惑地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时,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的身心爱上帝和上帝的每个子女,同时好好记住,恶的力量远不如善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事实上,他的生活正是这种伟大真理的完美写照。在他崇高的博爱思想和广博的学识之中,已经被深深地融入了信仰的力量。他看到了在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神无处不在,在所有卑微者面前,神会施与伤者爱的援手。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或者教义,但他把两个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一个是上帝是万物之父,一个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使我感到,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神是爱,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有了这样的信念,即使是最黑暗的云也会被吹散,而且,这里也不会有罪恶与不义的容身之地。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想起几位好友的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有好多年,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同我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去世后,我通读了整部《圣经》,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哲学著作。这其中就包括斯韦登伯格的《天堂与地狱》和遮蒙德的《人类的阶梯》,可是我发现,同布鲁克斯主教“爱的信念“相比,这些人所持的信条或教理都无法令人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我还有幸结识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待人最热诚的一个朋友。他每一个毛孔都热力四射。他的知识如此广博,性情
又如此和善,只要他在场,你绝不会感到沉闷。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奥利佛·温代尔·霍尔姆斯博士时的情景。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邀请我和莎立文老师去他家做客。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刚学习说话。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图书室,他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噼啪作响,他说自己正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倾听查尔斯河的潺潺流水。”我试探着说道。
“不错,”他回答道,“我同查尔斯河的关系可是亲密无间呢。”房子里面有一股油墨和皮革的味道,这里显然到处都是书,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摸索起来。我的指尖无意中落在了丁尼生的一部诗集上,当莎立文老师把诗集的名字告诉我以后,我就开始背诵:
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
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但是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我的手上。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背着房间的鹦鹉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后来,我又多次见到过霍尔姆斯博士,我从他身上不但学到了诗,也学到了爱。
在会见霍尔姆斯博士不久之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和莎立文老师在“梅里麦克”号上拜访了惠蒂尔先生。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不俗的谈吐赢得了我的好感。他曾出版过一本盲文印刷的诗集,我选读了其中的一首《校园时光》。他惊讶于我的读音是如此地准确,还说理解起来毫无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还为他背诵了《洛斯迪奥》,当我吟诵到最后的诗句时,他把一个奴隶的雕像放在了我的手中,奴隶身体蜷曲,脚踝拴着脚镣,就像刚被天使从监狱中解救出来的样子——奴隶一下子瘫倒在彼得的翅膀之下。后来,我们走进了他的书房,他不但为莎立文老师亲笔签名,还向她表达了钦佩之意。他对我说:“她是你灵魂的拯救者。”最后,他领我来到门口,并且轻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可是不等我履行诺言,他便去世了。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博士是同我交往时间最久的朋友之一,我八岁时就认识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每当苦难和悲伤降临的时候,他的智慧和同情心给了我和莎立文老师以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不但积极言传,而且以身作则,爱国家,爱最穷苦的同胞,勤勤恳恳地不断追求上进。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愿上帝祝福他!
在之前,我已经描述过我同贝尔博士初次会面时的情景。自那以后,我又在他华盛顿的家中度过了很多个愉快的日子。他美丽的家坐落在布赖顿岛海角的腹地,毗邻巴代克,这个小村因被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写进书里而闻名。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布拉斯道尔湖边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还帮他放风筝,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未来的飞船的飞行规律。
贝尔博士不但精通各类学科,而且具有把那些知识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即便是最深奥的理论,他也能够轻松破解。同他在一起,你不禁会产生出这样的感觉,假如你只有有限的一点时间,那么,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他幽默而富有诗人的气质,他对儿童满怀爱心,手里抱一个小聋孩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他为聋人作出的贡献将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他个人的成就,以及在他的感召下别人做出的成就,都同样值得我们赞叹。
我在纽约生活的两年间,曾有很多机会同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交谈,但是我决不会去刻意求见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同我见过一次面后就成了好朋友,比如劳伦斯·休顿先生。我曾十分荣幸地拜访过他和贤惠的夫人,我还参观了他家的图书馆,并且读到了他的天才朋友们写给他们的留言,这些留言饱含感情,不乏真知灼见。你确实可以这样说,休顿先生有一种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美好思想情操的本领,真是—点儿也不错。你不必为了了解他而去读《我所认识的男孩》——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胸怀坦荡、待人宽厚的一个,是一个能够同患难共欢乐的朋友,他不但同人相处是这样,就是对待狗也是充满了爱心。
休顿夫人也是那种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我被浓浓的友情所包围,我拥有了最珍贵的礼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她。她不遗余力地对我谆谆教诲,而且帮助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每当我在学习中身处困境而心灰意冷时,她就会写信鼓励我,让我重新燃起斗志。从她身上,我们学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克服了眼前的困难,下一步的路途才会变得平坦易行。
休顿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威廉·狄恩·豪威斯先生和马克·吐温先生。我还见到了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先生。查尔斯·杜德利·沃纳先生是最吸引人的小说作家,也是我最钟爱的友人。他有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心,爱人如己。
记得有一次,沃纳先生带我拜会了可敬的“林地诗人”——约翰·巴勒斯先生。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正如他们笔下的散文和诗歌一样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当然,我是无法同这些文学大家盘经论道的,尤其是当他们在不同话题之间纵横捭阖,或者辩论正酣、妙语连珠的时候。我就像小爱斯凯纽斯步履蹒跚地跟在英雄父亲埃纽斯身后一样,只能勉强跟上他们的思维,不敢有半点松懈。
他们还对我说过许多至理名言。吉尔德先生同我谈他如何在月夜穿过沙漠向金字塔进发,他在给我的信上,特意在签名的下面做出凹下去的印记,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而黑尔博士也有他私人的问候方式,他会把落款签名用盲文刺在纸上。我还通过触摸马克·吐温先生的嘴唇而“阅读”了他的一两篇小说。马克·吐温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无论讲话做事都个性鲜明。我在与他握手时,甚至能感觉到他眼中炯炯有神的闪光。当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滑稽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你能够感觉出他的心灵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伊利亚特的化身。
在纽约时,我同样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玛丽·曼普斯·道奇夫人,就是那位可爱的《圣·尼古拉斯》杂志社的编辑。还有里格斯夫人(即凯特·道格拉斯·维津),她是《帕特希》一书的作者。她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她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这些我都乐意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
我还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我经常去她在林德赫斯特的家做客。她为人热情,总是做一些让人开心的事。在同她交往的这些年里,她的循循善诱和从未间断的慷慨援助令我和莎立文老师永生难忘。
另有一位朋友也是令我受益匪浅的。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令他声名远扬,他英明果断的才干博得所有人的一致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慷慨好施,默默行善。由于他的地位,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根据海伦的描述,这位神秘的赞助人应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J·P.摩根先生)
不妨这样说,正是我的朋友们成就了我的生命和人生。他们想方设法地把我的缺陷转变成一种荣耀的特权,使我在厄运投下的阴影里,依然能够坦然而快乐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