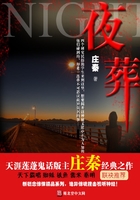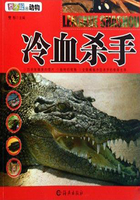“很感谢你对我的忠告,”索密斯说,“可是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
“她已经拿定了,”佐里恩说,眼睛正视着他,“你知道,再要像12年前那样是不可能的了。”
“那就等着瞧。”
“你听我讲,”佐里恩说,“她现在很难处,我是惟一的在法律上对她的事情有发言权的人。”
“还有我,”索密斯顶他,“我也很难处。她这样是自作自受。我的处境也是她造成的。现在我还没有决定,为她本身的好处,我究竟要不要她回家。”
“什么?”佐里恩叫了出来,他整个身体感到一阵战栗。
“我不懂得你这句‘什么’是什么意思,”索密斯冷冷地回答,“你在他的事情上的发言权,只限于付给她的进账,请你记看这个。当初因为离婚使她太现丑了,我才保留了自己的权利,而且,如我刚说的,要不要行使这些权利,我现在还不敢说。”
“天哪!”佐里恩脱口而出,接着发出一声短笑。
“对了!”索密斯说,声音里带有恶毒意味。“我还没有忘记你父亲给我取的译名呢,‘资本家’!我这个译名并不是白白给人取的。”
“这简直是幻想,”佐里恩喃喃说。哼,这家伙总不能逼着自己妻子和他同居。反正,那些旧礼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转过来把索密斯看看,心里想,“他是真的吗,这个男人?”可是索密斯看上去非常真实,端端正正坐着,苍白的脸上两撇剪得很齐的小胡子,看上去很漂亮,一片嘴唇翘成固定的微笑,露出一颗牙齿。有这么大半天,双方都不做声,佐里恩心里想,“我不但没有帮她忙,反而把事清搞得更糟。”索密斯突然开口了:
“从各方面说来,这对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佐里恩听了这话,心绪变得极端激动起来。在马车里简直坐都坐不住。那情形就像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英国人囚禁在一起,和他认为十分可厌然而明知道完全是人之常情、但是无法理解的国民关在一起-这种性格就是英国人对契约和既得权利的强烈信念,和他们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现在在这部马车里,坐在他旁边的恰恰就是确有这种财产意识的具体典型,可以说是它的肉身-而且是他的亲骨肉!这太荒诞不经了,太吃不消了!“可是这里面还要多一点!”他带着厌恶感想着。“人家说,狗是会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的!看见她之后又引起他的馋病了。美色啊!真是见鬼!”
“正如我说的,”索密斯说,“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你能够做好,不要管她的闲事,我就感谢不尽。”
佐里恩咬着自己的嘴唇,他这人一向讨厌吵架,现在几乎巴不得吵一下了。
“我不能答应你这种事情,”他简短地回答他。
“很好,”索密斯说,“那么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了。我在这儿下车。”他叫马车停住,没有说话,也没有打招呼就下车走了。佐里恩上了自己的俱乐部。
街上正叫唤着战事的头一次消息,可是他并不理会。他有什么办法帮她忙呢?他的父亲如果还活着多好!他父亲会有很多办法可想呢!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他父亲所做到的那一切呢?他的年纪难道不够大吗?快50岁了,而且结过两次婚。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成年。“真怪,”他心里想。“如果她姿色平平,我就不可能一再地想到她。美色,当你感觉到它时,真是个魔鬼!”他怀着烦乱的心情走进俱乐部的阅览室。就在这间阅览室里,有一年夏天的下午他曾经跟波辛尼谈过话,即便是现在他还记得自己为了珍的缘故给了波辛尼一大段隐秘的演讲,还大胆提出自己关于福尔赛家人的诊断,而且他当时警告波辛尼提防的究竟是哪一种女人,他自己就弄不清楚。现在呢!他自己几乎也需要这样一个警告了:“可恨义可笑!”他心里想,“真正的可恨又可笑!”
索密斯刚明白自己需要哪一个了。
那句“那么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了”,随便说说很容易,但是他说这一句话时究竟怀有什么意思,可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索密斯说这句话时也不过是发泄发泄自己痛苦着的妒忌本性而已。他从马车里出来时满怀愤恨-恨自己没有看见伊莲,又恨佐里恩看到伊莲,现在又恨没法说出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他不坐马车是因为再坐在他堂兄身边太吃不消了,他一面快步向东走去,一面在想:“佐里恩这个家伙我一点也不相信。一个为人不齿的人,永远是为人所不齿的!”这家伙当然会同情-同情-放荡的(他避免用罪恶这个字,因为对于一个福尔赛说来,这字眼儿未免太戏剧化了)。
这样决定不了自己要的什么在他还是一件新事情。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人家答应给他一件玩具,又拿走他一件玩具,在两者之间总放不平,他对自己感到诧异。不过在上星期天,他的愿望还很简单-只要自由和安妮特。“我上她那儿去吃晚饭,”他想。看见安妮特说不定会重新使他心思坚定,烦躁平息,头脑清楚起来。
饭馆里客人相当满-有不少外国人和外表好像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人。从杯盘声中间传来片断的谈话,他清楚听见有人同情波尔人,并且谴责英国政府。“不要把这些顾客想得太复杂,”他想。他木然吃完晚饭,喝掉另外叫的咖啡,始终不让拉莫特母女知道他来了,一直等到吃完,才小心不让人家看见,向拉莫特太太的密室走去。不出他所料,母女两个正在吃宵夜-这顿宵夜看上去要比他吃的晚饭好得多,他倒有点懊悔起来-她们招呼他时表现的诧异简直就像真正的诧异,使他忽然疑心起来,心里想:“我敢说她们老早就知道我来了。”他偷偷看了安妮特一眼,但是看得很仔细。这样美,而且看上去这样坦率,她会不会是在引他上钩呢?他转向拉莫特太太说:
“我在这里吃的晚饭。”
真的吗?她早知道多好!可以给你推荐几样菜,可惜可惜!索密斯的疑心更加证实了。“我做事得当心点儿!”他突然想。
“先生,再来一小杯最特等的咖啡和一杯格兰马尼尔吧?”拉莫特太太站起来,吩咐这些精美饮料去了。
索密斯现在单独和安妮特在一起了,他说,“怎么样,安妮特?”唇边浮起一点儿防御性的微笑。
女孩子脸红了。在上星期天这就会使他心神不能自持,现在给他的感觉却像看见自己养的一条狗望着自己摇头摆尾。他有一种古怪的权力感,就像自己说一声“来吻我”,她就会过来吻他似的。然而-古怪的是-屋内好像另外还有一张脸、一个身材,而他感到心痒痒难熬的,究竟是为了那一个,还是为了这一个呢?他的头向饭馆那边掉一下,说道:“你们有些顾客很特别,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安妮特看了他一下,眼睛垂下去,玩弄着手里的叉子。
“不,”她说,“我不喜欢。”
“我已经到手了,”索密斯想,“只要我要她。可是我真的要她吗?”她有风度,长得美-很美,很娇嫩,趣味还不算俗。他的眼睛在小房间里溜了一转,可是脑子里已经溜到另外一个地方-灯光半明半暗,银色的墙壁,椴木钢琴,一个女子靠钢琴站着,就像要避开似的-这女子的雪肩是他晓得的,而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是他渴望晓得的,头发好像一堆深琥珀。正如一个艺术家总在追求那不可实现的,而且愈追求愈感到饥渴的东西一样,索密斯在这当儿心里也涌起一阵由于旧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饥渴。
“不过,”他泰然说,“你还年轻呢。你有很大的指望。”
安妮特摇摇头。
“我有时觉得除了做苦活之外,什么指望都没有。我并不像妈妈那样喜欢做活。”
“你母亲真了不起,”索密斯带点开玩笑的味儿说:“她决不肯让者做她的房客。”
安妮特叹口气。“人有钱一定非常好过。”
“哦!你有一天也会有钱的,”索密斯答,仍旧带那一点开玩笑的味儿,“你别愁。”
安妮特耸耸肩膀,“先生是好心肠。”她在自己撅起的嘴唇中间塞进一块巧克力糖。
“对了,亲爱的,”索密斯想,“嘴唇很美呢。”
拉莫特太太捧着咖啡和甜酒进来,谈话结束了。索密斯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
苏荷区的街道一直给索密斯一种财产不得其人的感觉,这时他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在盘算。伊莲过去只要给他生过一个儿子,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局促不安地追求女人了!这种思想从他意识深处那间阴暗的小警卫室里跃身出来。一个儿子-使你能有所指望,使你的余年能活得值得,使你能把自己遗留给他,使自己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有个儿子,”他咬牙切齿地想着,“一个正式的合法的儿子,我就可以像过去那样百事迁就她生活下去。反正女人都是一样。”可是他走着走着又摇头起来。不然!女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往日他过着不如意的婚姻生活时,有不少次曾经企图这样想过,但是总不成功。他现在还是没法这样想。他想把安妮特看做跟另外那个女子一样,可是并不一样,她没有往日的那种情感诱惑。“而且伊莲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我的合法妻子。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使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不能和我复合呢?这是正正当当的事情,法律容许的事情,一点不会引起人家闲话,一点不大惊小怪的。如果她不喜欢-可足为什么她要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个麻风病人,而她-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对象了!”她就像一所空房子,就等着他这个法律上有所有权的人重新住进去。重新占有她,所以为什么他要接受离婚法庭上的那些迁就,那些忍辱含羞和那些无形的失败呢?以索密斯这样一个有城府的人,一想到一点不招致非议就可以悄悄重新收回自己的财产,这简直是一种强烈的诱感。“不,”他沉吟着,“我很高兴去看了那个女孩子。现在我知道我要哪一个了。只要伊莲回来,她要我多么体贴我就多么体贴,她可以自顾自地生活:可是也许-也许她会来迁就我的。”他的喉咙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他顽强地沿着格林公园的栏杆向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故意踏着月下走在自己前面的影子。
第三代福尔赛。
11月里的一个下午,佐里·福尔赛正沿着牛津的高街一路走来,瓦尔·达耳提正沿着这条街一路走去。佐里刚换掉划船的法兰绒裤子,正要上油炸锅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他是新近被通过为会员的。瓦尔是才换掉骑马装束,正要往火坑跳-那是谷物市场的一家马票号。
“你好!”佐里说。
“你好!”瓦尔回答。
这两个表兄弟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二年级的佐里请瓦尔吃饭,第二次是昨天晚上在一个有点外国情调的场合下碰见的。
在谷物市场一家缝衣店的楼上住着那些得天独厚的未成年的年轻学生之一,这家伙父母双亡,承继了一大笔遗产,保护人离得很远,而且天生的劣根性。19岁时就开始搞起那种富有诱惑力、而且为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玩意儿,因为对于一般人说来,一次破产就很够受了。由于备有在牛津能找到的惟一的一座轮盘赌具,他已经出了名,而且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抢前花掉他的未来遗产。他比库伦姆还要库伦姆气,不过比较属于那种脸色红红的,肥头胖脑的类型,没有库伦姆那种逗人的懒洋洋派头。对于瓦尔说来,有人带他去玩轮盘赌简直等于受一次洗礼,接着在若干小时后,又会受一次回校的受冼礼,那就是从装有遮人耳日的铁窗爬进玄。有一次晚间,正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瓦尔一双原来盯着那诱惑的绿呢台子的眼睛抬了起来,在烟雾弥漫中看见对面正是他的这位表哥:“红门啊,单门啊,小门啊!”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
“上油炸锅俱乐部去喝杯茶,”佐里说,两人走了进去。
一个外人看这两个人在一起,定会在这两个第三代福尔赛表弟中间看出一种说不出的类似的地力:脸上的骨架完全一样,不过佐里的眼睛灰得深一点,头发淡一点,而且还要鬈。“侍役,请你来点茶和涂牛油的小甜圆麦包。”佐里说。
“抽一支我的香烟吗?”瓦尔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你的,运气怎样?”
“我没有赌。”
“我赢了十五镑。”
佐里想起自己父亲有一次神经起来,谈到赌博的话-“你被人家赢了去,你会不开心,你赢了人家的,又会过意不去。”他很想把这话重说一遍,但是仅仅说:
“无聊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个家伙我跟他中学同学,一个顶无聊的人。”
“哦,我不知道,”瓦尔说,就像自己信仰的神被人家轻薄时在做辩护一样,“一个漂亮的、杰出的赌鬼。”
两个人默不作声,互相喷着烟雾。
“你见过我的家里人吧,是不是?”佐里说,“他们明天下来。”
瓦尔脸有点涨红了。
“是吗!我可以透给你一点曼彻斯特本月障碍赛的苗头,很难得的。”
“谢谢,我只对老式赛马有兴趣。”
“那种跑马你赢不了钱,”瓦尔说。
“我就讨厌那种跑马场,”佐里说,“又闹又有气味。我喜欢草地赛马。”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瓦尔回答。
佐里笑了,笑得就像他父亲一样。“我就没有意见,我每次赌钱总是输。”
“当然啊,你得花钱学乖。”
“当然,可是只是乱七八糟地尔诈我虞。”
“当然喽,否则他们就会吃你,有意思就在这里。”
佐里显出轻蔑的神气。
“你自己玩点儿什么呢?划船吗?”
“不-骑马,到处去跑。下学期我要打马球了,如果能够叫外公出钱的话。”
“那是詹姆士爷爷,是不是?他是什么样子?”
“比山岳还老,”瓦尔说,“而且总认为自己要弄得倾家荡产。”
“我想我的祖父跟他是兄弟。”
“我觉得这些老古董没有一个是喜欢户外运动的,”瓦尔说,“他们一定是崇拜金钱。”
“我的祖父才不是呢!”佐里热情地说。
瓦尔弹掉香烟上的烟灰。
“钱只适合拿来花掉,”他说,“我真想能够多一点钱。”
佐里眼睛直接抬起来把他看了一眼,这种判断的目光,是从老佐里恩遗传来的,钱是不应当拿来在嘴里谈的!两人再度保持沉默,喝着茶,吃着涂牛油的小甜圆面包。
“你家里人下来住在哪里?”瓦尔问,竭力装得随便的样子。
“住彩虹旅馆。你对战局怎样看法?”
“始终很糟糕。那些波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堂而皇之打一下?”
“为什么要那样?除掉他们自己的这种打法,别的打法都是对他们不利的。我倒佩服他们”
“骑马和射击他们是会的,”瓦尔承认,“可是讨厌得很。你认识库伦姆吗?”
“麦顿学院的吗?只看过一面。他也是那伙浪里浪荡的一个,可不是?纨祷,绣花枕头。”瓦尔用肯定的语气说:“他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