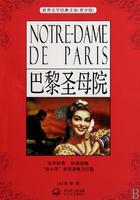“我得走了,”他说,“涅克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次赛马哪个赢。”他给自己的大儿子来这么一下,就走了。这个大儿子在会计上大名鼎鼎,而且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跟他父亲一样从来就不是个跑马迷。亲爱的尼古拉!他指的什么赛马呢?还是他讲的一句笑话呢?这么大的年纪精神还这样好!亲爱的马琳要放几块糖?基里斯和杰斯好吗?裘丽姑太认为他们的骑兵义勇队目前一定忙着巡逻海洋呢,不过,当然波尔人是没有军舰的。不过法国人一有机会,可谁不准会来点花头,尤其在那次可怕的伐苏达恐慌之后,倜摩西弄得极端不安,事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买进什么。可恨的是那些波尔人,待他们那么好,还要忘恩负义-把詹梅生博士关了起来,而马坎德太太一直就讲他是那样的一个好人。国家还派了密尔那爵士那样一个才智之士去和他们谈判!她真不知道波尔人究竟要些什么?
可是,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倜摩西家里真是难得-这都是出了大事情时才会偶尔带来的。
“珍·福尔赛小姐。”
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立刻站了起来,一面克制住旧怨,一面旧感情又在翻上来,一面又对这个“浪子回家”的珍感到得意,几种复杂心情使两个人抖了起来。呀,这真是难得!亲爱的珍-这么多年-她气色多好呀!一点没有变。她们几乎到了嘴边要说:“你亲爱的祖父好吗?”在这冲昏头脑的一刹那,两个老姐妹已经忘掉的那个可怜的、亲爱的老佐里恩已经在地下长眠7年了。
在福尔赛家人中间,珍一直是最勇敢、最爽快的人。坚定的下巴,奕奕的眼睛,头发红得像火,身材又小又矮。她在一把钉了有珠饰细工的金边椅子上坐下,就好像自从上次来看望过两位祖姑之后,根本没有隔开10年似的-十年的旅行、独立生活和照顾“可怜虫”的岁月啊。那些“可怜虫”近来全都是一个类型的画家、镂刻家和雕刻家了,因此她对福尔赛家人和他们不可救药的艺术见解就更加感到不耐烦。的确,她差不多已经忘掉她的族人还活在世上,现在带着挑战式的坦率向周围巡视一下,使屋内的人全都感到极端不舒服。她只是来看望一下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并没有指望会见别人,而且为什么她要跑来看望这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她也简直弄不懂;要么就是这个原因,在她从牛津街往拉狄麦路一家画室的途中,忽然想起这两个被她不瞅不睬了好多年的老可怜虫,感到不过意起来。
又是裘丽姑太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我们刚才还说,亲爱的,这些波尔人多么可恶!那个可鲁葛老家伙又是多么无耻!”
“无耻!”珍说,“我觉得他完全做得对。我们干什么要干涉他们?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可鲁葛全赶走了,那才真叫活该。他们只是要钱。”
由于惊异而引起的沉默总算被弗兰西打破了,她说:
“怎么?你是个亲波尔派吗?”(无疑地这个名词还是她第一次用)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管他们的事情呢?”珍说,就在这时候,女佣在门口说:“索密斯·福尔赛先生。”破天荒加上破天荒!室内的人全都要看珍跟索密斯会面时怎样一副嘴脸,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鬼心眼,尽管并不知道,可总是疑惑自从珍的未婚夫波辛尼和索密斯的妻子演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这两个人就没有碰过面。就因为大家全抱有这样的好奇心,连问候一时都几乎打断了。这时只看见两人的手微微碰一碰,而且只把对方的左眼瞄了一下。裘丽立刻出来挽救这种局面。
“亲爱的珍真是别出心裁。你想,索密斯,她认为不能怪波尔人。”
“他们不过是要独立,”珍说,“为什么他们不能独立呢?”
“因为,”索密斯回答,他嘴边的微笑稍稍偏了过来,“他们碰巧承认了我们的宗主权。”“宗主权!”珍鄙夷地重复一句:“我们就不会喜欢别人对我们有宗主权。”
“他们有钱进项,这总是便宜的,”索密斯回答:“合同总是合同。”
“合同并不全是公平合理的,”珍冒火了,“如果不公平合理的话,那就要取消。波尔人比我们弱得多,我们大方一点没有关系。”
索密斯冷笑一声。“这只是感情用事。”他说。
海丝特姑太最怕抬杠子,这时候身子向前耸起,毅然说:
“在这个年头,这些时的天气会这么好。”
可是珍并不容她打断。
“我不懂得为什么感情用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这是世界上顶好的事情。”她恶狠狠向四周环视一下,裘丽姑太不得不再来打圆场。
“你最近买了什么画没有,索密斯?”
她真不愧是一个天生会说话的第一流能手。索密斯脸红了。要他宣布最近买了些什么画,等于把自己送进轻蔑的虎口。因为不知怎么的,大家都知道珍就是偏袒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天才”,而且最鄙视“发迹”,除非是有她的一把力在里面。
“买了两张,”他说。
可是珍的脸色变温和了,她的福尔赛性格使她看出这是一个机会。为什么索密斯不能买点艾里克·柯布莱的画呢-艾里克是她最近的一个“可怜虫”?她立刻展开攻势:“索密斯可知道这个人的作品吗?真是了不起。这人是要起来的。”
哦,是的,索密斯看过他的画。据他看来,简直是“溅洒一通”,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珍冒火了。
“当然不会,受欢迎死也不来。我还当做你是个鉴赏家,不是画商呢?”
“索密斯当然是个鉴赏家啊,”裘丽姑太赶快说;“他的眼光真是了不起-哪个人的画要起来他事先总能够知道。”
“哦,”珍倒抽一口气,从珠饰细工的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我就恨这种成名的标准。为什么买画不找自己喜欢的买呢?”
“你的意思是,”弗兰西说,“因为你喜欢那些。”
在这刹那的停顿中,可以听得见小尼古拉轻着声气谈维约勒特(他的第四个孩子)正在请人教粉笔画,他就不懂得这有什么用。
“再见,太姑,”珍说;“我得走了,”她吻了两位祖姑,恶狠狠地把室内环视一下,又说了声“再见”,就走了。一阵风好像随着她刮了出去,就像是大家都叹气似的。
“詹姆士·福尔赛先生。”
詹姆士轻轻拄着一根手杖走进来,穿一件皮大衣,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大得有点离奇。
室内的人全站起来。詹姆士真的老了,而且快有两年不上倜摩西家来了。
“这儿很热,”他说。
索密斯帮他脱掉大衣,在脱大衣时,看见自己父亲穿得那样利落,不由得暗暗喝彩。詹姆士坐了下来,人家只看见他的膝盖、肘弯、大礼服和一簇长胡须。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这句话虽然没有什么明显意义,他们全知道是指的珍。他的眼睛搜索着儿子的脸。
“我想还是亲自来看看,他们给可鲁葛什么回答呢?”
索密斯取出一份晚报,念出上面的标题。
《我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宣布战争状态!》
“啊!”詹姆士说,叹口气。“我就怕他们会像老格兰斯顿那样拉起脚来就跑呢。这一次我们可要干掉他们了。”
大家全盯着他望。这个詹姆士!永远是唠唠叨叨。永远是心神不宁,水远在烦神!这个詹姆士老是说,“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还有他的悲观主义和他的小心谨慎的投资。一个福尔赛家年纪最大的人而有这样坚强的意志,简直有点怪诞。
“倜摩西哪里去了?”詹姆士说,“他应当注意这件事情。”
裘丽姑太说她不知道,倜摩西今天午饭的时候没有说什么。海丝特姑太站起来走了出去,弗兰西有点不怀好意地说:
“波尔人不容易对付呢,詹姆士伯伯。”
“哼!你这个情报哪里来的?从没有人告诉过我。”
小尼古拉平和的声音说,涅克(他的最大的孩子)现在经常要去操练了。
“啊!”詹姆士说,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的脑子里想着瓦尔。“他得照应他的母亲,”他说,“他没有工夫去操练,那样一个父亲。”这些隐秘的吐露使得大家全都沉默下来,后来还是他开口。
“珍上这儿来做什么?”他带着怀疑的目光把室内人挨次地看了过来。“他父亲现在是个阔人了。”谈话转到佐里恩身上去,他还是什么时候看见过他的。现在他的妻子去世了,想来他会到国外去走走,会见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呢,他的水彩画说不上来,可是倒出了名了。弗兰西甚至于说:
“我们很想再碰见他,他相当讨喜欢。”
裘丽姑太想起有一次佐里恩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就在詹姆士坐的地方。他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索密斯怎么看?
大家知道佐里恩是伊莲的委托人,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微妙,全带着兴趣望着索密斯。索密斯颊上微微有点红了。
“他的头发花白了,”他说。
真的吗?索密斯见过了他吗?索密斯点点头,脸上红晕消失了。
詹姆士忽然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得。”
这两句话恰恰说出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情,好像什么事情后面都有点儿鬼似的,所以没有人答腔。可是就在这时候,海丝特姑太回来了。
“倜摩西,”她低声说,“倜摩西买了一张地图,而且插上了三面国旗。”倜摩西捅了-一声叹息在举座间传开来。
如果倜摩西的确已经在地图上插上三面国旗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国家在奋起之后是能有所作为的。这个战争等于已经结束了。
佐里恩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佐里恩站在好丽的旧卧室窗口,这房间现在已经改为画室,并不是因为有朝北的光线,而是因为窗外的景色可以一直望见爱普索姆跑马场的大看台。他移到旁边面临马场院子的窗口,向成天躺在钟楼下面的巴耳沙撒吹吹口哨。那只老狗仰起头把尾巴摇摇。“可怜的老东西!”佐里恩想,又移到北窗那边去了。
自从他打算执行委托人义务以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静不下来。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锐的,现在觉得很不舒服了,他的怜悯本来容易激动,现在弄得更加烦乱了,此外还有一种怪感觉,仿佛自己的爱美感找到了什么具体的着落似的。秋意已经侵上那棵老橡树,树叶已经转黄。今年夏天的太阳又大、又热。树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应当活得久,”佐里思想着;“因为缺少热的缘故,我也变黄了。如果我不能作画的话,就上巴黎去。”可是,他记忆中的巴黎并不给他什么快感。还有,他怎么走得了呢?他得留在这儿看索密斯搞出什么事来。“我是她的委托人。不能丢下她没有人照应,”他想。他还能够清楚看见伊莲在她那问小客厅里,而这问小客厅他总共只进去过两次,这使他觉得很奇怪。她的美貌一定有一种强烈的和谐!任何惟妙惟肖的画像决画不出她那种神态来。她的本质就是-呀!对了,是什么呢?……马蹄声把他又唤回那扇窗子口。好丽正骑着一匹妇女专用的长毛小驹进了马厩院子。她抬起头来,佐里恩向她招一下手。好丽近来相当沉默,长大了,他认为是,开始要为她的未来着想了-全都是这样,这些年轻人!时间的确是个恶魔!走得多快呀!忽然感到自己这样浪费时间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他又提起画笔来。可是没有用,他的眼睛就没法集中-而且,光线也暗下来了。“我要进城去一趟,”他想。在厅堂里,一个佣人和他碰上。
“一位太太要见你,叫黑隆太太。”
“太巧了!”他走进画廊-这间房现在还叫这名字-看见伊莲就站在窗口。
她向他走过来,一面说:
“我是闯进来的,穿过那边小树林和花园,从前总是这样跑来看佐里恩大伯的。”
“你来这儿不算是间,”佐里恩回答,“这是历史安排好的。我刚才还想起你。”
伊莲笑了。那样子就像有什么东西使人眼睛一亮,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灵感应-比这还要安详,还要完美,还要魅人。
“历史!”她低声说。“我有一次告诉佐里恩大伯爱情是不死的。唉,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是厌恶永远存在。”
佐里恩看着她。难道她对波辛尼的心终于淡了吗?
“对了!”他说,“厌恶比爱和恨还要深些,因为厌恶是神经的自然作用,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我是来告诉你,索密斯来看过我。他说了一句话使我害怕起来。他说:‘你还是我的妻子!…
“怎么?”佐里恩冲口而出。“你不应当一个人住。”他仍旧瞪眼望着她,心里痛苦地想着,只要哪儿有美色,哪儿就不会风平浪静。毫无疑问的,这是许多人认为美色不道德的主要原因。
“还有呢?”
“他要和我握手。”
“你握了吗?”
“握了。他进来时,我敢说他并没有要握手的意思,可是在屋子里他变了。”
“啊!你绝不能再一个人住下去了。”
“我又不认识什么女人可以邀来同住的,而且我也没法定做一个情人,佐里恩大哥。”
“但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佐里恩说,“这事情真是尴尬;你在这儿吃晚饭好吗?不吃?那么我送你进城去,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进城的。”
“真的吗?”
“真的。你等5分钟我就来。”
在往车站的途中,两人谈到到绘图和音乐,谈到英圈人和法国人性格的对比,和他们对艺术见解的分歧。可是在佐里恩眼中,那条直而长的小径上篱笆间的秋色,一路上随着他们啁啾的碛鶸鸟,杂草烧完后的清香,她的头颈的姿态,一双深褐而迷人的眼睛,不时盯他一眼,以及那个动人的身条,给他的印象要比相互间的谈话深刻得多。他不自觉地腰杆直了起来,步伐也更加有弹性了。
在火车里,他就像向她进行口试一样问她平日是怎样消磨时间的。
她做自己的衣服,上店家买买东西,弹弹钢琴,搞点法文翻译。有一家出版社经常接点稿子,似乎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晚上很少出去。“我一个人独自生活得太久了,你知道,所以一点不在乎。我想我是天生的孤僻性格。”
“我不相信,”佐里恩说,“你熟人多不多?”
“很少。”
到了滑铁卢车站时,他们叫了一部马车,佐里恩送她到公寓的门口。分手时他握着她的手说:
“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上罗宾山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再见,伊莲。”
“再见,”她轻声说。
佐里恩重又爬上马车,不明白为什么邀她一同去吃饭、看戏。她的生活多么孤独,多么枯寂,多么没有着落啊!“什锦俱乐部。”他向车夫说了一声。当他的马车驶上河滨大道时,一个人戴着大礼帽,穿着大衣在旁边走过去,走得非常之快,而且紧挨着墙,就好像身子在擦着墙壁似的。
“天哪!”佐里恩心里说,“索密斯呀!他现在正要干什么?”他在街角上停下马车,从马车里出来,向着索密斯走去的方向一步步走了回去,一直到眼睛看得见公寓的大门为止。索密斯已经在大门口停下来,正在望她窗子里的灯光。“他如果进去,”佐里恩想,“我怎么办?我又有什么资格干涉呢?”这家伙讲的话不错。她现在还是他的妻子,他要找她的麻烦可绝对挡不了!“哼,他要是进去,”佐里恩想,“我就跟着进去。”他开始向公寓走去。索密斯又走近一步,已经决定进大门了。忽然问,索密斯停下,转了一个身,向河这边走来。“怎么回事!”佐里思想。“再走上十几步,他就会认出我了。”他转身就溜。他堂弟的脚步声紧紧跟在后面。他赶到马车面前,趁索密斯还没有拐弯之前就上了车。“走!”他向车窗里说了一声。索密斯的脚步声挨着马车追了上来。
“马车!”他说,“有人了吗?喂!”
“喂!”佐里恩回答。“是你?”
灯光下照出他堂弟苍白的脸上突然显出疑心,佐里恩主意拿定了。
“我可以带你一段路,”他说,“如果你要向西的话。”
“多谢,”索密斯回答,就上了马车。
“我去看了伊莲,”马车走动时佐里恩说。
“真的吗?”
“你昨天去看了她,我晓得。”
“是的,”索密斯说,“她是我的妻子,你知道。”
那种口气,那种微翘的讥讽的嘴唇,使佐里恩忽然恼怒起来,可是他抑着怒气。
“你最好先搞清楚!”他说,“但是如果你要离婚的话,那还是不去见她为妙,你说是吗?人不能一脚跨两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