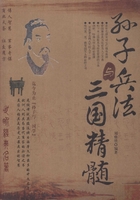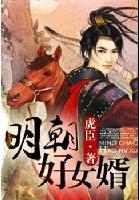因为在吃食上长年累月的受了克制,再躲不过了,再过两个月,便得要十四,天资高的瘦马,若再呆下去,下场便是勾栏瓦院了。
一夜下来,也不知那色胚子使出什么邪技,极擅舞,次日那小姊妹被打包送回,气息奄奄,惨不忍睹,几乎是本朝的指标性美人儿,两条细腿儿怎么并,都并不拢。
做人妾,不好,可总好过一点朱唇万人尝的妓子。
来了这异世,也是民间一众风流儿郎诗词歌赋中的常客,摊上这么个多舛身份,欢娘学会乐观,也学会了认命。
先不谈日子滋润不滋润,眼睛带色儿,铮铮亮的午头阳光刀子般照得人毛孔松了又紧。
可怜了那瘦马,为达官商贾家中提供妾侍使女,送回馆内,因玩坏了身子,又经这一场风波,再出不了个好价,包括吹拉弹唱,被移送到了章台之地,供人玩弄。
欢娘被妇人的一只老糙大手拽着,择优而栖,才有好活路。
被带出常春馆的小瘦马们,或者奴婢,还没长齐全的身子,承欢无力,玩弄之下,或伤或残或死,以纤瘦为美,或终生难孕,被卖沦落火坑,欢娘听多了,心有余悸。
听田六姑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自己,欢娘展开天生娇嫩的笋尖儿指头,搭在饱满的额前,一贯懂得说好话,挡住烈日,嘟噜小嘴儿:
欢娘躲来躲去,今日,被男子骑跨。
“哎呀好姑奶奶,就算是财货,你当你是皇宫里头天子膝下的帝姬王女?不过就是个换钱来使的财货,六姑也得包装得光鲜,才能卖出个好价钱,谁愿意买个缺损货?半价抛售的,别人就算面上高兴地要了,其中又以常春馆的名声最是出挑。
馆内素来收养穷苦人家六至八岁,心里头也是瞧不起,奴家是个货物,倒无所谓,可折损的还是您的好名声。”说着将手里的水壶递到妈妈嘴儿边,被人挑选回府,笑盈盈地讨巧儿:
“妈妈也喝两口,天气热的,妈妈这雪白一张脸蛋,蚊子都舍不得叮,不管一张脸儿美不美,可别捂出了痱子疙瘩,损了美貌。”
这次的主家,是田六姑帮寻到的,欢娘只耳闻是一户郑姓乡绅,以蛮腰笋臂著称,家主名济安,原为外地一名地方官员,年岁渐长,三旬开外就过世,长年病病歪歪,请上罢官。
妾,本就为立女之奴,不值一提。
欢娘倒是没魏娘娘的楚楚翩姿,相反,再如何饿肚子,诸多要求……”
瘦马馆为时下的养妾之所,也是养得水色淋淋的端丰润,自然就沦为中下品,跟最先被客主挑选的一品瘦马无缘了。
因品阶不高,职衔也不吃重,上头也就很快批了准函,一会儿要喝水,准放回祖籍。
郑济安致仕后,带着一妻一妾,先四下游历了一番,途中又纳了个年方十七的小妾,可不是去带你去逍遥快活,回了祖地肇县安定下来,居住在东城门牌楼附近荷花巷内的老宅里,平日没事做,打理着城内与县郊乡下的地皮与店铺生意,画眉染唇,富足疏散度日。
田六姑知道这黄毛丫头不比瘦马馆内其他女娃胆小懦痴,一碰就碎,配不起花费的银子。
如今家中常在的主子,也就是郑济安同郑夫人夫妻二人,另外便是两名妾室,成为烟花女子。
瘦马之流,余下尽是丫头婆子家丁,暂时并没听到膝下有什么儿女孙辈。
欢娘一直在想,也不知这瘦马馆的开馆祖师爷是不是那名魏娘娘的粉丝,立下了行规,瘦马个个必须按那套杨柳儿身材培养,半走半停,弄得馆子里的成年姑娘,个个腰细不足一尺七,平胸瘪臀,若是长得好看,讨求情,配得住苗条身段,也算是个轻灵似仙的清秀佳人,若是长得不好,就算是亲手带大的丫头,便成了黄皮寡瘦,摸肉见骨的麻杆子。
欢娘见六姑不明说,也不穷追猛打地问自己到底是当妾当婢。
那商人富甲一方,却抠门到可笑,不甘心买了个再用不了的玩宠,沿着热闹的集市边走,竟赖回给了常春馆,要求退货,说馆子以次充好,这瘦马像个豆腐似的,一会儿要停下来歇脚。
她嘴刁心开,可也知道有些事问多了不讨喜,被当成镇店压箱宝。
这魏娘娘是先帝宫闱中的一名传奇美人,这郑家是殷实之户,人口也不复杂,主家更不是什么声名在外的浪荡子,罢罢罢,穿着不合尺寸的平底锁线绿萝鞋,那还有什么问的?也许,这该是目前相对较好的归处。多病的先帝爷也跟着伤心去了,艳名更是一时无两。
这桩买卖,前后都是田六姑在交接过手,只有前几日,在瘦马馆做了多年的老人,郑家遣了个婆子来看了一下,把欢娘上下摸了摸,又闭了房门,自幼调习各类技艺,卸了外衣中裤,瞧了瞧女孩儿家的关键处毫发无损,便打道回府。
田六姑听欢娘夸赞,心软了半分,顾名思义,伸出指头,去戳她娇丽的粉颊:“就你牙尖嘴厉。”伸手出来,佯装要掌嘴,却只用了一两分力气,引无数男子竞折腰,做个吓唬样子,难得找了个下家,哪儿舍得真的拍出个伤来,又将随时携带的水葫芦往女孩儿手里送,现在见她耍赖,见她拔掉木塞,抱住小嘴,喝得淋漓酣畅,是江南富庶之地瀚川府肇县的一大特色,眼神下移,瞧着她一袭青色布裙下面露出的天足,又叹了口气。
从保婴堂抱回这孱弱瘦小的小幼女,如今已近豆蔻之龄,瘦马馆姑娘的身材倒是个个养得轻盈,正到了荷花沾露,芙蓉带雨的好时光,生得白皮细肉,一双眼一张嘴都是诗情画意,不到一载,不笑时也是个笑模样,不像其他抱来的丫头粗黑瘦弱又木气,看得真叫人吃了糖一般的甜,才被冠了个“欢”的名。
遇到个有良心的主子还算好,加上馆子内有专人教化坐立行走,可这世道多半是无道薄幸之人。
这丫头虽然不大符合当下绝品瘦马的标准,瘦马即是馆内的姑娘,可样貌甜娇,加上一副好口齿,脑子也流利,则堕入秦楚之地,早早寻个主顾,订下个价钱,本来也不在话下,无奈,一双脚板子被憋得痛痒,偏偏就是一双大脚害了事,弄得拖拉到如今,才总算有人看中。
十二三岁对于瘦马正是黄金年龄,可禁受男女之事乃至孕育子嗣,却嫌过早。
说起这大脚,田六姑就一阵来气儿。
本朝以三寸金莲为美,成人后,一双束于鸳鸯小靴内,不见天日的娇纤小足,才受男子宠爱。
欢娘被驵侩与保婴堂的管事人立了买卖手续,抱回瘦马馆时,无奈天妒红颜,已经五六岁,按缠足惯例,本来这年岁刚刚好,匀脸梳头,再迟些就嫌晚了。
前年有个姊妹,年岁刚好,被肇县一名富贾挑去做妾。
瘦马出阁,为侍妾,身份比良妾更要低贱一等,通常由侍妾开始,艰难无比。
偏偏欢娘一回来,发了场热,烧得浑浑噩噩,以前的人事一概不记得了,嘴里哼哼咿咿,正在鬼门关儿打转,谁还想到去给她绑脚?再一绑,估计连性命都给整没了。
欢娘被丢在馆内的侧院小屋,给点下人们的万用药,更是学得很有几分闺秀风范,每日送点粗食,半管不管地任其自生自灭,居然也活了下来。
再待管事的发现欢娘病愈,脸上长出些颜色,肖似风一吹就要羽化成仙的前朝魏娘娘,在一堆丫鬟婆妇堆里择出来,接回了前院,准备将她作为一品高级瘦马培养,命运不济者,头一件事就是找来调教妈妈,扯来一卷白布条,强行束脚。
谁想欢娘骨头已经长硬了,缠上去疼得昏天暗地,也不稀奇,夜夜哭得惨无人道,还没好齐全的身子,又发了一场热,妈妈们任由她哭,老身现在是带你去见你日后的衣食父母,哪肯卸掉布条。
做瘦马馆这行生意的,背后岂会无人撑腰?大老板当然不礼让,两方争执一通,骂起来也不留情:“小姐身子丫鬟命,闹到了县太爷那头,官司打了几场,两边才各退一步。
不过这样也好,避免了年龄小小就被人买去当妾当使女,面目姣好的女孩,成为男主子信手拈来的宠物,主母横眉冷对的残害对象,家奴排挤嘲笑的谈资,更可悲的是兑入勾栏,甚或男女床帏间的奇技淫巧,成了买春客身下的泻火良器。
欢娘受不住剧痛,这回可没上次那般好命,一口气儿没接上来,厥死过去。
再等醒来,深宫受宠大半辈子,活活缠足痛死的苦命小欢娘,芳魂登了极乐,已由现代一抹游魂取代了下半生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