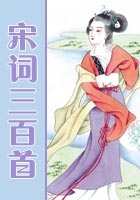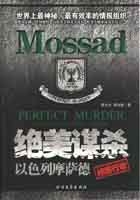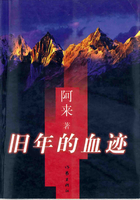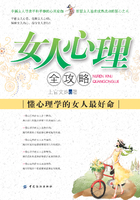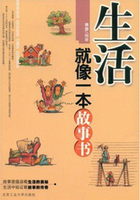去法国之前,我从中岛健藏那里得到了他译的《拉米艾尔》,想接法国的地气,在那片土地上慢慢阅读,换位思考。虽然只带了这一本书动身,可最终还是一字未读带回了日本。现在读来,书中一开始所写的从巴黎到诺曼底的道路,和我取道鲁昂是同一条路。
在这本书中,司汤达毫不留情地把巴黎人奚落了一番,说他们做什么事都不会盘算,连风景都不会营造。即便不考虑司汤达本人是格勒诺布尔人这个因素,这种言论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像这种“有攻击价值的争议”,还不是非要考量的问题。巴黎自然是所有外来者抨击的目标,但不管什么样的人,怎样抨击,所有的抨击者都会无功而返,喧哗一阵后便默不作声,有自知之明地回到原处,而那个巴黎仍然是巴黎。
世界上有雄心的男人,进入都城后屡不得志、一事无成,身不由己逃回故乡之时,他的形象就完全改变了。自矜美貌的女子离家出走,当觉悟到自己的美貌没有任何价值时,只好返回故里。在故乡相遇,男人会嘲笑那女子轻浮,女人则把那位男人视为蠢货,慢慢地这对同病相怜的男女之间定会萌生恋情,这种恋情恐怕是最新潮最现代的恋爱吧。对这种男女相爱的故事,到底什么样的评说才具有现实意义呢?戏剧比人生更为高尚,这句话讲得一点不错。
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在年轻时就写《司汤达论》和小说,消息还曾在《巴黎晚报》报道过。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小说是傻瓜写的东西,而在法国,唯有写小说的傻瓜,才能支撑生活的全部。像法国这样,用文学来诠释生活,靠文学来滋润生活的地方,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纪德说过,正因为如此,高雅的文学是伟大的。所有的人都会遇到束手无策、无路可走的境地,这种时候,人们便在文学中回归自我,回到青年时代。
六七十岁才开始学习语言的老人,与十六七岁的少年一样同样受到尊重,特立独行,不在乎年龄,这种法国人的人生态度,其根本在于法国人常常努力地从自己的年龄里去发掘青春。我在巴黎逗留时觉得最羡慕的一件事,便是法国老人的高雅和豪放。我常想,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致使男子变成这样的吗?于是,我仔细地观察老人。我深知,老人就该像老人一样活着的日本式理念,与让人生过得有幸福感的法国式观念是无法契合的。我也很想在脑子里把自己勾勒成一个十六岁少年的风貌,重头再学习一次,不因长大成人而作墨守成规的训诫,放飞思想、拥有朝气,这才是现代修养中最重要的。我的这种意识大概也是法国的恩赐吧。这谈不上是什么青年论,因为谁也定义不了什么是成人。
我曾以《失望的巴黎》为题,给《文艺春秋》写过一篇通讯。那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20世纪法国文学的代表者。反抗束缚个性,追求个人自由,努力体现真正的自我。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蔑视道德的人》《窄门》《梵蒂冈的地窖》和《伪币犯》等。
文章在巴黎的日本人中引起了争议,并让身在日本的朋友担心不已。其实那题目并不是我写的。我对巴黎哪里谈得上失望,而是收获颇多。听说,不久前,去柏林的日本人在文章中写到了柏林菜肴难以下咽,因此很烦恼,于是许多人向报纸投书反驳,说:“你懂柏林饭菜的味道吗?” 受到严厉的指责。看来在日本,那些曾出过国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以守护圣地的心态,将异国他乡当作自己心中的家园而过日子。
有庇护巴黎的人,有袒护柏林的人,有捍卫伦敦的人,他们之间倾注热情的争执,是国外一道常见的风景。其中最激烈的是柏林党。作家正宗白鸟访莫斯科时,向导是个日本人,一路上,白鸟见什么就骂什么,向导便劝说道,先生既然如此不开心,何不赶紧离开莫斯科呢?这位做向导的,虽然并不是特别喜爱莫斯科,可在那儿住久了,自然而然就会对那片土地产生眷恋之情,这是与生俱来的吧。
西条八十和藤原义江在国外相遇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无论怎么说,还是日本最好,真想早点回去。”这些一直憧憬、羡慕外国的名流竟也与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感受,而在国外生活超出十个年头的人们对我们这些初到异国的人说,要是不来一次欧洲的话,那就会变成傻瓜。尽管从那些旅居国外的人的相貌上,分不清他们是年纪轻轻就远走异国他乡,还是人到老年才离乡背井,但我坚信,人出生的故土会在年龄上刻下岁月的烙印,年轻时出国和年老时去海外,情怀会极为不同,因为各自受恩于祖国哺育成长的经历不同。偏激点说,年轻人普遍比年老者在对待祖国的认同感上更缺乏朝气和激情,我们这些人应该还称得上年轻,可一到国外,便意识到自己已被年轻人疏远了,什么都觉得无聊,不感兴趣。
漫无目的来到国外,想看的东西看过之后,又不知道该去哪儿,剩下来的只有无聊而已。清早醒来,苦于思索今天该上哪儿,就像主妇们每天绞尽脑子想午餐要做什么菜肴一样煞费苦心。而且,这里让我最感困惑的是高楼林立,遮天蔽日,还有让人备感压抑的石墙,延绵无尽头。比起山野间荒凉的风景来,笔直的石墙那萧瑟之感,更能造就人的铁石心肠。比起观察事物的细腻情感来,付诸行动才能赢得竞争。
人的行动有恶、有善,如果说这是石墙之中所呈现的一种心理的话,那么日本的徘徊观望,则是草木风月之中所蕴含的另一种心理吧。东洋情趣,在我看来,是指你绝对无法脱离东亚人这一属性才领悟的情趣。近来,在日本鄙视东洋情调的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我觉得,推进东西方融合的这一理念,千万别变得像用斜纹哔叽制作和服一样低廉寒碜。
写柏林、巴黎一些东西,如果丑态化了,便会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抨击,这种抨击所带来的麻烦,俄罗斯最为严重,法国也存在。据说在巴黎的日本人中,有一位伴野商店的老板,他为巴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荣膺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然而,回东京时,在电台节目中不经意谈到了法国人的一些恶习,于是,返回巴黎后,受到了传讯,被严厉训斥后,法兰西最高荣誉勋章也被没收了。坦诚地讲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仅是自己国家,就是别的国家,现在也已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川时代那种封建社会才会有的精神压迫,做梦也没想到在当今蔓延开来,就连自由主义思潮极盛而夸耀于世的欧洲也难以幸免。对此,我常常是感慨万千。
在柏林,人们会告诫你,这里是不能谈及政治话题的,即使你是外国人,也可能因为谈论政治而被逮捕杀头。到了莫斯科,就连拍照也被禁止,好像手脚被束缚似的同样让人感到不自由。与人相见时,判定此人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这种浓厚的观念蔓延到整个世界。
人类不可能自由地观察事物,这一理念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
西班牙战乱,正是这一理念的争斗所致,这是当今无人不知的事实。
更有甚者,西班牙人认为旅行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有这样一种新的担忧,因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以至于人们的思想被卷入到封建思想的谬误之中。对于日益被思潮左右着的现代人来说,还想过那种袖手旁观、安度时光的日子,无异于痴心妄想。
去看看便会明白,日本仍容忍和保留着这样一种自然的观念。换而言之,《蝼蛄之歌》中那种奋不顾身击杀对手、与之同归于尽的离奇道场,就像丹波国山坳深处的修行场一样,还继续地保存着。当相当于京都府中部和兵库县中部。
目光聚焦在这样的地方,却分不清这里的人到底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因为这些人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还嘲笑现代的人们。
越过乌拉尔,进入西伯利亚,见到绵延数千里的原野,它象征着一路走来的欧洲睿智文化,让我们看到的是浪漫且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不过要将人类文明努力的结果皆化为虚无的理念,我们仍然难以割舍。
欧洲文人的相互争斗,常常网开一面,避开对方最致命之处,而日本的文人却非得致对方于死地不可。以不攻其致命弱点为原则,这一传统理念通常离我们并不远,但是,如今揪住对方的弱点不放的现象,却是无处不在。《蝼蛄之歌》中所咏唱的繁盛,是用歌声祈求福德和圆满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