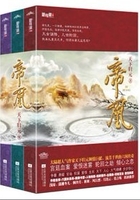在远征军,纪永年学过一些日语,能勉强听懂日常对话。武田好像在说,一套竹编套壶八十多元人民币,在日本可卖六千日元以上,扣除运费、关税等,至少能赚三千日元。佐藤得意地说道:“我父亲在中国待过,我了解中国人。他们太穷,急于赚外汇,价格还要压低。”
狗东西,换着法子侵略中国!纪永年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看完样品,开始审查设计稿样。佐藤看得非常仔细,甚至拿出放大镜,挑剔地查看工笔勾勒的细微之处。李伯成玩弄着一个精致的防风打火机——日本人送他的小礼物。打火机色泽深红,漆面锃亮。他爱不释手地打燃又关上,关上又打燃。
佐藤看完图样,压低声音对翻译说着什么。
“佐藤先生说,其余都没问题,价格也好商量。他非常佩服纪先生的中国文化功底,只是,有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这张‘渔村落日图’,应改名为‘渔村朝日图’,太阳应占画面的二分之一。”翻译说。
李伯成凑过来,拿起稿样细看。纪永年是这样设计的:无边的海面波涛汹涌而来,冲打着左侧一个小岛,岛上几间低矮的渔棚,似乎即将在波浪的冲击下坍塌;渔棚旁,一轮落日黯然无光,即将沉入大海。
“改一下吧!从视觉上讲,这个画面有点压抑。”李伯成没当一回事。
“李厂长,这恰巧是中国文化韵味。如果照他们所说,太阳占了一半画面,太直太露,太不含蓄,还像我们中国的艺术吗?”纪永年不慌不忙地解释。
李伯成觉得这番见解也有道理,转头正想对翻译说什么,佐藤突然用中国话说:“不行!必须得改!”
“佐藤先生喜欢汉语,能说中国话。”翻译有些尴尬。
“我认为,没有修改的必要。”纪永年平静地说道。
“你的,在侮辱我们大和民族!”佐藤傲慢地站起来,“你的知道,大日本国的国旗的是什么?太阳,熊熊地燃烧、光照四方的太阳!你这太阳,不行的,必须改的!”
纪永年毫不示弱地起身:“我提醒佐藤先生,第一,要有中国韵味,是你们提出的设计原则。这幅稿样难道没有中国艺术特色?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大海落日就是一种美;第二,请佐藤先生冷静,今天的中国,不是‘二战’时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欺凌的中国人。”
气氛陡然紧张,像导火索已经点燃、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魏科长和李伯成慌忙做好做歹,劝佐藤和纪永年坐下。
“纪老师,这是商业行为,没必要牵涉太多。我看,干脆把太阳设计大一些,放在画面正中,尊重客户要求嘛!”魏科长商榷道。
“就照日本人说的办。纪老师,你清楚,厂里下月没产品做了。这是三百多万啊!……”李伯成凑近纪永年耳朵,哀求地说。
“李厂长,我早说过,要用都用,不用都不用。我不会改,也不能改。”纪永年神情坚定地回答。
李伯成一脸懊丧,有苦说不出。
“你的不改,订货的取消!”佐藤激怒地威胁道。
纪永年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收拾好稿样,走出样品厅。
“订货的取消!我的不相信,中国的没有竹编厂!”佐藤怒气冲冲地嚷着,要魏科长送他们回宾馆。
“佐藤先生,我们重新设计,完全照你的意思办。”李伯成低声下气地说。佐藤摔开他的手,沉着脸走出样品厅。
这笔订单落空了。几天后,纪永年听老陈讲,佐藤赶到省内另一家竹编厂,签了订货合同。
消息传出,全厂一片哗然。大多数职工的矛头,纷纷指向纪永年。
“这个老头,又犟又倔,仗着有点本事,不认天不认地,难怪要成历史反革命!”
“是嘛,太迂腐了!管它太阳在西边还是东边,只要有钱赚就行!”
“他上不养老下不养小,我们却眼巴巴的靠着工资吃饭。我本来盼着拿些奖金,买台电风扇,这下全完了,还是只有摇芭蕉扇。”
个别偏激的,甚至恶作剧般对他进行报复。他的自行车,连着几次被放掉车胎气,后来干脆用刀子,将外带刺了几个小洞。他的办公桌上,一天出现一团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几块阴沟里拣来的石头,报纸上用墨汁写着:又臭又硬。
小张素来敬重纪永年,愤愤不平道:“从艺术角度看,纪老师设计得相当好。日本人不懂,关纪老师啥事?”
老陈比较理解纪永年,但也委婉地劝道:“其实,可以策略一点,让他们提供稿样。不得罪客户,也不得罪外贸公司和领导。”
对听到的各种议论,纪永年不生气,不辩解,照旧默默地上班,默默地下班,很少与人说话。
自从那天佐藤扬长而去后,见到纪永年,李伯成就没给过好脸色。他测算过,如果拿下那笔订单,工厂不但大有盈利,还能超额完成全年产值和销售计划。工人有奖金,他也有业绩,还可能被提拔重用。订单一泡汤,希望全部落空。最要命的,厂里快没产品做了。他急了,三天两头跑订单。省里开进出口产品展销会,他带着两个业务员,守了一整天,订了六万元的货。“还不够塞牙缝!”他愤愤地骂道。一次,与一个东北客户谈订单。客户说,只要他喝完一瓶白酒,就签三十万元合同。他横下心,把酒倒在三个碗里,端碗就喝。结果,喝了两碗,他就醉得一塌糊涂。合同没签成,他的头痛得像要炸开,死尸般躺了整整一天。想起这些,他的怒气就发泄在纪永年头上。“如果日本订单成了,哪会这样?……”越想,他对纪永年就越怨恨。
他召集全厂管理人员开会,总结一季度工作。会议一开始,他就大倒苦水,强调工厂面临的种种困难,然后话锋一转,把一切归根于日本订单的落空。
“……没拿下这笔订单,设计室纪永年要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在于两点:一、顽固地将个人偏好强加给外商,将个人行为凌驾于工厂利益之上,无视企业的效益和发展;二、不服从组织,不仅拒不修改设计稿,还将稿样拿走,致使外商动怒,谈判破裂。”
“我有话说。”纪永年镇静地举手。
李伯成颇有气度地叫他讲。
“我认为我没有错。佐藤说,西落的太阳是对他们国家的不尊重。我想问,太阳在正中就是对他们的尊重吗?是他们联想太多。在一个小小的竹编产品上,也要摆出不可一世的模样。试问,哪有升起后永远不落的太阳?”
有人窃窃地笑起来。
李伯成叫纪永年坐下,板着脸继续说:“鉴于纪永年给工厂造成的重大损失,结合他的历史问题,厂部决定,纪永年调离设计室,到后勤部门打扫清洁,停发一个月工资。”
纪永年静静地凝望着李伯成,眼光中,含着深深的悲悯。
四
这是纪永年第二次离开设计室。第一次,是“文革”开始不久,他先被揪斗,然后关进杂物间办“学习班”,继而到车间打扫清洁,到仓库当搬运工等,一干就是十年。直至“四人帮”粉碎后,厂里设计任务重,才让他回来协助工作。他交设计室钥匙给老陈时,素以“老好人”著称的老陈也愤然了:“厂里做得太绝情了!还有半年多你就退休了,何必呢?”
“没关系,不就打扫清洁嘛,轻车熟路,还能锻炼身体。”
纪永年照旧默默地上班,只是更加孤僻,更少与人说话。没事时,他就坐在传达室旁木椅上,久久地望着天边。
四个月后,上级对他的历史问题落实政策:为他平反、恢复荣誉,补发两千多元工资;鉴于他临近退休,不调回工艺美术公司,仍留竹编工艺厂,享受正科级待遇。轻工局一个姓付的处长,当面向他宣读平反文件,还郑重地给他本人一份。李伯成尴尬地征求意见:“纪老师,你还是回设计室吧,当当顾问。”他淡淡地婉拒:“我就当清洁工。几个月来,我身体好多了,酒也能多喝二两。”
一天上午,李伯成接到轻工局通知,说总参某局一位领导,是纪永年的老战友,这次来锦都出差,通过政府部门,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点名要见他,局里很快派车来接。李伯成不敢怠慢,立即通知纪永年。纪永年想了好一阵,实在想不出是谁。
还是那辆接送佐藤等人的上海牌轿车。车上坐着轻工局胡副局长和付处长,加上李伯成和纪永年,一共四人。
军区招待所一幢古朴的灰楼前,一个军人正在焦急地踱步。汽车开来,他快步迎上去。
“纪永年,你没变什么,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军人爽朗地笑着,同纪永年握手。
纪永年困惑地打量着他:斑白的两鬓,刚毅的大眼,线条粗犷的脸庞……他觉得依稀像一个人,但不敢确认。
“我是刘心田啊!那年打腾冲,不是你把我背下战场,恐怕连我骨头都找不到了!……”刘心田眼里泪花闪烁,紧紧地握住纪永年的手。
小餐厅里,刘心田设宴款待纪永年等人。他俩一面喝着“五粮液”,一面畅叙几十年的曲折经历。刘心田一九四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他当副师长,在战场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总参,“文革”中饱经磨难,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问起纪永年现状。纪永年说,还好,在打扫清洁。
“怎么,打扫清洁?我记得,当兵前你学过美术设计。是不是有点浪费人才?”刘心田责备地瞥着胡副局长。
胡副局长连忙解释,说落实政策后,纪永年应该调回工艺美术公司,考虑到他快退休,仍然留在竹编工艺厂,但享受同等待遇。
“我说老伙计,政治待遇、干部身份还是应该要的。”刘心田关心地说。
纪永年讲起这次当清洁工的原因。
“你做得对!中国人,应该有民族气节。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来,为你这个‘渔村落日图’,我敬你一杯!”刘心田豪爽地端杯饮尽。
胡副局长附和地点头。李伯成闷闷地喝着酒,心里很不以为然。
他俩谈起同在远征军的日子,谈起滇西战役,谈起倒在腾冲城下的弟兄,谈起预二师遣散后四处散落的战友。他们一杯杯地喝着,喝完一瓶,又是一瓶……
纪永年脸色通红,兴奋地畅饮着。他告诉大家,这是他平生第三次如此喝酒:第一次是日本投降时,他醉了一天一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喝了一个通宵;这是第三次……“难道,我不应该喝够喝高兴吗?……”他抢着要酒喝。
刘心田醉了。秘书扶着他,踉踉跄跄地回房休息。纪永年更是醉得一塌糊涂。李伯成同付处长抬着把他塞进轿车,直接将他送回家。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李伯成接到杜苹英电话:纪永年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他立即带着老陈赶到医院。纪永年在抢救室,杜苹英坐在轮椅上,与几个邻居在外守候。杜苹英噙着泪花说:
“几个月来,他天天喝酒,闷着不说话……昨天夜里,他醒了一下,含含糊糊说太高兴了,喝。后来,我见他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也越来越红,着急了,大声喊来邻居,把他送到医院……”
李伯成安慰杜苹英,说厂里一定全力以赴。他留下老陈在医院打理,匆匆回厂上班。
两个小时后,他接到老陈电话。老陈哽咽着告诉他,抢救无效,纪永年去世了。
握着话筒,李伯成的手,软软地垂下。这时,莫名其妙的,他想到那幅“渔村落日图”;想到昨天吃饭时,刘心田同纪永年叙谈的一切……他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