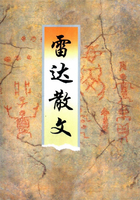中午吃午饭时,谢淡谈起汪户籍介绍车床的事。姐夫淡淡地说:“我认识这个户籍。十多年前,我给他们讲过课。这个人,品质不错,心胸狭窄了点。”姐姐不放心地提醒谢淡,一定要有全套手续,按正规途径办理,要保证产品质量,不能出娄子。谢淡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在浙江,我卖了好几部车床了。”
快下班时候,谢淡来到前进电机厂。他计划,如果一切顺利,他准备请段楠吃晚饭,再沟通一下。他太需要这次成功了!车床销售出去,厂家答应给他百分之二的奖励,扣除所有花费,还能大赚一笔。何况,由前进电机厂开始,滚雪球似的,还能打进其他厂。哪怕申诉再等两三年,他也能耗下去。
他对段楠报出价格:C620车床每台五万元,另要十吨钢材指标;签订合同后,首付百分之三十货款;工厂派人去浙江验货,付清全款才能发货;运费等均由生产厂家承担。段楠一一记下来,说明天一早向厂长汇报。
“我姐夫说,你是大学生,还是学中文的。仅仅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了?”车床事情谈得差不多时,段楠好奇地问。
谢淡苦笑着点点头。
“就提点意见,会被判刑?一九六六年,我初三毕业,刚好十六岁……”段楠怀念地叹口气。
下班铃声响了,张胜平走进来。他换了一件簇新的白衬衫,假发也打理得整整齐齐,看去很精神。瞧见谢淡坐在写字桌旁,正热烈地同段楠交谈,他便故意放重脚步。
“小段,下班了!我们一起走,请你吃晚饭。”他热切地说。
“这……我的事还没谈完,你先走吧。”段楠仿佛有些为难。
谢淡知趣地声明,该谈的全部谈了,准备告辞。
“不!发运时间要多久?假如我们没有钢材指标,价格咋算?锦都这边的搬装费,哪个承担?……”段楠找出好几个理由,态度坚决地挽留他。
谢淡只得坐下。
张胜平怀疑地扫视着他们,脸色一下阴下来,闷闷地走去。
目送着张胜平的背影,段楠疲软地靠在椅背,说自己忽然头晕,叫谢淡先回去,一切等厂里研究了再谈。谢淡有些莫名其妙,只得走了。
可能因为电机厂急需车床,谢淡报价也较合理;也可能,因为他是汪户籍介绍的,而他姐姐、姐夫在省公安厅,信任感强一些,两天后,合同签订了。谢淡提出,浙江那边给他百分之二的奖励,寄来寄去太麻烦,付款时,电机厂少付一千元,直接给他现金。厂里犹豫一下,想到金额不是很大,同意了。签完合同,谢淡坚持请段楠吃饭,说要感激她。恰逢张胜平也在,谢淡一起邀请。张胜平说有事,婉拒了。
“味之腴”饭店里,谢淡要了当家菜“东坡肘子”、“凉拌鸡块”,还要了三两白酒和一瓶汽水。他端着酒杯:“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好!”段楠正想站起来,突然,看见张胜平在饭馆外闪过。她稍一犹豫,蓦地灿烂地笑起来,高兴地拿起汽水,“干杯!”
几杯酒下肚,谢淡的话渐渐多了。他谈起大学时的生活,谈起分配到丹巴后的种种理想。
“我想当作家,又想当诗人。后来,接触到藏区湛蓝的海子、无际的山峦,你猜我想做什么?”谢淡自问自答道,“我只想当一个山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终生不离那个童话般的世界。那时,我充满梦想,何等的纯真啊!我以为,生活像蔚蓝的天空,只有阳光和白云,没有黑夜和阴暗。”
“所以,你就专给领导找麻烦,最后成了反革命?”段楠调侃道。
“不,除了提意见,还有其他原因。”谢淡难堪的一笑。
“呵?”段楠颇为好奇。
“我读高中时,中苏关系还未破裂,上面组织两国学生相互通信。与我通信的,是苏联基辅市一个女学生,叫罗瓦杰娜。我一直保留着她的照片,在丹巴,还常拿给朋友看。我说,如果中苏仍旧友好,我一定要去找她。这句话,后来成了罪名之一,说我里通外国,羡慕腐朽的修正主义制度。”
“那个姑娘漂亮吗?同你通了几封信?你们写中文还是俄文?还有照片吗?……”段楠大感兴趣地问了一连串。
“照片?抓进去时没收了。”谢淡不想就这个问题谈下去。他略一沉默,自嘲般地笑起来,“其实,直到两年前,我才骤然想通:仅仅因为写了上告信,未必会判刑。关键,我得罪了县上一个主要领导。这个人没有生育能力。我随口讥讽,说在魏忠贤手下,哪能干出男人的成绩?人家不懂,我还引经据典地发挥。这话传出去不久,我就被抓了。”
“魏忠贤?”
“明朝的奸臣,是个大太监。”
段楠反应过来,用手指着谢淡,笑得前仰后翻:“你啊,太刻薄了!是我,也要把你抓起来,多判几年!”
那顿饭,他们吃得很开心。分别时候,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彼此感到意犹未尽。
几天来,谢淡兴致很高。在段楠介绍下,他又跑了几家企业,对方都需要车床,答应研究后决定。他喜滋滋的,安排着即将到手的奖金。他准备买一部“红灯牌”收音机——姐夫习惯早晚听广播,现在用的小收音机质量太差,噪音闹得脑袋发晕。他还打算给姐姐买一些衣服。这些年,他亏欠她太多。
国庆节后,车床发运回来了。谢淡去电机厂结清手续。突然,汪户籍带着联防队员,冲进办公室,不由分说地将他绑起来。
“你们干啥?”段楠极度惊怒,挡在谢淡前面。
“我在执行任务。小楠,你要冷静。”汪户籍温和但却坚定地说。
“请问,我又是啥罪名?”谢淡嘲弄地问。
“投机倒把罪,合适吧?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上次抓过他的联防队员,重重地冷笑。
谢淡被送往拘留所。汪户籍将段楠叫到一边,严肃地说:
“我介绍这个人来谈业务,没叫他从你们厂拿一千元现金,更没叫他干别的事。你的觉悟很成问题,竟然还同他一起吃饭。你说,这是什么性质?幸好,张胜平警惕性高,不仅给浙江那边通了气,还挂电话到丹巴了解情况,及时到所上反映。他还记下谢淡每次到厂的日期,逗留的时间,说过的一些话。不然,我也会跟着犯错误。”
“可他没说任何出格的话,没做任何错误的事啊!”段楠几乎绝望地叫道。
“没有?还要怎样?”汪户籍惊讶地打量着她,“你看看你自己!自从认识这个人后,你忽然爱打扮了,话也多了,有事没事,总要谈起车床,谈起谢淡。这些变化,你姐早看出来,为你着急得不行。”
段楠的脸,瞬间变得通红。她的直觉告诉她,谢淡的被抓,堂皇的理由是投机倒把,藏在后面的真正原因,是她对谢淡萌发的好感。不仅自己家人担心,身边所有的人,没谁支持她同他发展下去。反革命罪、劳改释放犯、无业游民,这些帽子中的任何一顶,足以将人吓得半死。
“莫名其妙!无聊透顶!”她羞恼地骂着,转身就走。
稀里糊涂地被抓进去,第九天,谢淡又被稀里糊涂地放出。拘留期间,没人提审他。他似乎已被遗忘。
拘留所里,每间牢房上下铺,住着十二个人。伙食是“二三三”,早上二两稀饭,中午晚上各三两糙米干饭。饭能勉强填饱,菜却很少,油气更少得可怜。这里关的,大都是偷盗、斗殴之类的罪犯。狱友问他怎么进来的,谢淡说自己也不清楚。大家帮他分析,认定是汪户籍捣鬼。汪户籍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大家说不明白,谢淡也云里雾里。想来想去,他隐约觉得与张胜平有关。虽然仅仅见过几次,他看出,张胜平与段楠,似乎有些感情纠葛。张胜平投向他的目光,也始终显露着不加掩饰的敌意。他心地坦然,没在意。
谢淡放出前两天,街上的爆竹,持续不断地响着。牢房有人偷偷说,“四人帮”被抓了。目睹政治人物沧海桑田似的沉浮,谢淡早已麻木。他不想关心政治,而他的命运,偏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直觉告诉他,声声爆竹,在预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出拘留所大门,姐姐在等他。姐姐说,他被抓后,派出所只通知送生活用品,没说什么事。段楠来了,说出张胜平等原因,她才如梦初醒。她找到公安厅同事,要他们帮忙,给下面挂电话。“要不是‘四人帮’粉碎了,政治局势变了,你不知还要被关多久。你啊你,今后接触人,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姐姐的眼睛一红。
“我没做啥啊!”谢淡委屈地辩解道。
“汪户籍说,你最好离开锦都,更不能与段楠接触——车床的事,可大可小,说挣点钱养活自己也行,说投机倒把也不过分。要是你不听警告,老账新账一齐算。”
离开锦都,又去哪里?谢淡忽然想起这十多年的经历,觉得荒唐得如同一幕滑稽戏。他神经质地笑起来。
“还笑?”姐姐责备道。
“我在想,我们都不清楚,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不过,乌云再大,终究遮不完天空。”望着高阔的秋空,谢淡想着自己怎么办。他不会离开锦都,车床,仍然要推销。他必须要活下去,要等待申诉结果,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他期盼着,眼前,忽然冒出段楠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