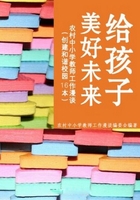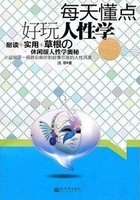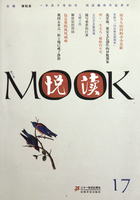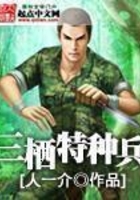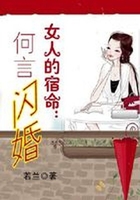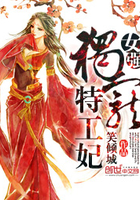3.城乡之间形成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板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悬殊
在所有制结构上,城乡之间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不同所有制,城市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农村以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为主。在城镇,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1978年为76.7%,1992年为69.6%,而非国有单位职工和劳动者占1/3左右;在农村,国有农场职工仅占乡村劳动者总数的1.8%,从而在城乡之间形成具有不同经济特征、运行机制和经营环境的城乡两大类型经济板块。在资源的总体性配置上,这两大板块之间的机会是不同的,并进而形成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较大差距。
4.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城乡之间的传统产业分工,城乡交往关系复杂化
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生产和经营单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经济结构凝固化,城乡之间的传统产业分工十分明显。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农民脱贫致富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创举,不仅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换,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缩小城乡差别,形成城市工业、农业、农村非农产业三元经济结构。中国城乡经济关系不仅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而且包含城市产业部门与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农村内部不仅是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了农业与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同时,这意味着城乡交往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城市工业和农村非农产业不仅由于其相当的同构性在资金、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而且由于较大的互补性在劳动力、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
总之,中国城乡关系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城乡居民双重身份、双重境遇及其所形成的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以及资源占用与分配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二)城乡矛盾的主要影响
城乡矛盾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城乡差别是中国社会三大差别之一,城乡矛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1.经济结构的错位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影响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城乡矛盾在经济结构上的特征之一是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错位。产值结构的主体是以工业为代表的二次产业,就业结构的主体是以农业劳动力为主体的一次产业。以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15.4%,就业比重为50%;第二产业产值比重51.1%,就业比重为21.4%。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研究结论,在同一收入水平上,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高于产值份额,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低于产值份额,因而就业结构的转换一般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同样,缪尔达尔对南亚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差,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
如果产值结构反映着供给结构,就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着需求结构。相对于工业部门的庞大生产规模,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则过于狭小,导致了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调,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循环中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一般来说,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反映着一个国家消费和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城市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基本上依赖于市场交换,而农村居民消费则有很强的自给性特征,因而服务产业所占比重的上升与一个国家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成正向变化和同步趋势。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全体居民消费中不需要通过服务产业实现的部分占很大比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之受到抑制,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受到约束。
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人口质量和数量失衡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工业化或者说产业结构转换与该国的城市化密切相关,并呈现正向变化。198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为72%,欠发达国家为30%,中国只有17%,不仅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而且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非农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7%,而城市化率只有43.6%。这与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使得城市化通道阻断不无关联,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不仅非农产业发展的空间狭小而分散,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大量农村人口仍然滞留于传统产业,长期沉淀在农村已经超载的土地上,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口结构凝固化,农民身份世袭化,不能实现人口的经济社会职能转变和空间迁移。城市已经实现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农村仍处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高峰时期,并未能根本实现人口生育形态的转变。在农村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膨胀就容易导致劳动力数量供大于求而质量供不应求,形成劳动力失业和人才相对缺乏的双重压力。相对于庞大的仅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大中城市为其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同时,从事简单技能甚至是无技能工作而获得的低工资无法支付在城市定居的生活成本,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或者放开之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并定居的机会仍然是有限的。农民工依然会因其流动性而成为农民工,不能实现人口迁移和定居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3.城乡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工农二元和城乡分割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城乡之间不但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上有很大差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以及在思想意识上也有较大差距,诸种因素导致农村相对贫困,而且这种相对贫困并非朝夕之功可以改变。城乡分割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1978年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分别为2.36∶1和2.90∶1,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有所缩小,1985年收入差距降为1.72∶1,生活费支出差距降至2.24∶1,但1986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3年,在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农民纯收入仅增长2%,而城市居民生活收入增长10%,为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5倍。数据表明,城乡居民差距水平已恢复到1978年的状况,其中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已接近解放后工农消费水平差距的最大年份,即1959年,其比值为3.17∶1。最新的统计数据仍然表明城乡差距在继续扩大,这种继续扩大必然潜藏着流动的势能,也隐伏着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此基础上,城乡之间缺乏协调一致,工农关系失调,因而城乡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较大地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工业化长期从农业部门积累资源,导致农业积累能力不足进而农村的自我发展受阻,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仅切断了农民对农业进行投入的资源途径,而且可能加速农业内部生产要素外流,这些因素严重制约农业生产集约化和“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农业的发展进程。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乡村发展的停滞和农业生产的长期徘徊,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现代化的进程受到巨大影响。
$三、中国城乡矛盾的基本解决办法
从城乡矛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城乡矛盾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的伴生物,城乡之间的距离和城乡矛盾的存在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矛盾不会自然消解,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会更加突出。从更深层次来看,城乡矛盾的存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工业化战略是尊重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适时调整社会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如果说城乡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上致力于消除城乡之间生存状况的巨大差距,坚定不移地统筹城乡发展。
1.“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和农业的基础地位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为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均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揭示了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客观规律。但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存在着许多问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从城乡关系上来说,“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城乡商品交换不平等,工农业发展不平衡。1978年前,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资金平均每年为100亿—300亿元。1978年后,“剪刀差”总体上有所缩小,但绝对额仍在增加,1990年代仍然达到600亿—800亿元;同时,在短期内仍然有所扩大,例如,1989年至1992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仅上升5.3%,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34%,“剪刀差”扩大16.1%。在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同时,对农业的给予却并未同步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对农业的投入是逐年减少。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基本建设投资比例是1960年代16%-20%,1970年代11%-12%,而1980年代只有3-4%。1978-1994年,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从13.6%降到9.2%。另有数据表明,2000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8%,低于1990年10%和1980年12%的比重,大约每10年下降2个百分点。1996-2000年,中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最高的不超过9%,而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10-20%。同时,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业发展资金流失,工农业发展失衡的状态长此以往,农产品供求相对平衡就会变成供给严重不足,并将无力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与城镇居民的较快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并有加速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差距为2.57倍,在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1995年为2.72倍,2001年为2.91倍,2002年为3.11倍,2003年为3.23倍,2007年扩大为3.33倍;加上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居民享受了各种福利和补贴,实际城乡收入差距约为6倍。从绝对数据来看,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中国经济社会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不协调性。城镇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农村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必然高于农民收入增幅,因而如果农村没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难以扭转。第三,城市繁荣和乡村落后形成强烈反差,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从消费水平来看,1978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7%,农民消费占总额的67.6%;1990年,农业人口占79.1%,农民消费占总额的53.2%;2003年,农业人口占70.8%,农民消费占总额的35.1%。另外,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总体水平落后;教育科技发展滞缓,农村教师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教师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卫生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征地补偿等方面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加,农村社会治安需要进一步加以综合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需要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总的来讲,中国农业相当落后,农村生活水平低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对农业生产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从经济增长的特点来看,经济增长较快和经济波动较为频繁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并存的两大显著特点。在通常情况下,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滞后性和递减性的,而且农业波动幅度高于经济波动。如果从波动系数看,粮食总产值高于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又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为薄弱的部门,农业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农业波动尤其是粮食生产波动是中国经济震颤和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由农业波动导致的经济波动对城乡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受到冲击,而且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受到抑制。在经济波动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下降,甚至出现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