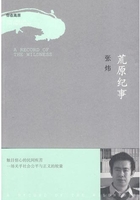陆润仪再度摔了苏妤送的东西,苏妤冷声一笑,吩咐先前的霁颜宫阖宫杖责二十再加二十,接着直接下了逐客令。
在场嫔妃那么多,此事自然而然地传开了。先是有人禀到了章悦夫人和佳瑜夫人宫里,两位夫人的回话如出一辙,均是坐视不理。
之后便禀到了娴妃处。阮月梨急急地去找苏妤,眉头紧蹙地问她:“你当真是不怕死!她到底有着身孕,若是气急了,那孩子当真有个什么闪失……”
“她胎像稳得很。”苏妤悠悠道,“敢动旁人不敢动的人才好立这威不是?再者,若她那孩子真没了,陛下赐我三尺白绫倒也痛快。”
立威和寻死,这两个想法可说是截然相反。阮月梨愣了一愣:“你到底怎么想的?”
“要么活得舒心,要么死得痛快。很难懂么?”苏妤悠哉哉的样子和阮月梨的焦灼对比鲜明,莞尔一笑,继续解释道,“反正最终结果我也知道了,横竖都是一死,干什么那么委屈自己?向头两年那样事事当心着?我累!”
心真宽……
这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梦见了棺材迟早要在眼前于是索性笑个痛快。
阮月梨白了她一眼,却是劝无可劝。苏妤的梦太准,她如此是“破罐破摔”也好,是想断气前再活个痛快也罢,都在情理之中。
突然觉得苏妤现在的话简直可称为“遗言”,阮月梨只觉尽量替她完成心愿才好。自是循着苏妤的心思,从楚充华宫里指了若干宫人到霁颜宫去,完事后才差人回了两位夫人,二人也都未说什么。
娴妃差去蕙息宫向章悦夫人禀事的宫人告退后不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字不落地禀到了成舒殿去。
皇帝听着宦官的禀报,一句岔也没打。直待说完,他才抬了抬眼,问了句:“又摔了?”
……什么又摔了?
那宦官想了一想,揖道:“是。听说那玉佛摔得粉碎的……”
皇帝嗤声一笑:“摆驾绮黎宫。”
同样好奇着事态发展的苏妤听到那一声“陛下驾到”时心里有了七八分的猜测,行至殿门口与迎驾,便觉出皇帝入殿时衣袍夹风——或者说是带着怒气。
这是兴师问罪来了。
苏妤沉容下拜:“陛下大安。”
皇帝在她面前停了脚步,面色沉的让殿中候着的一众宫人都屏了息。其实早在苏妤发落了陆润仪身边的人时,众人便觉得苏妤胆大得过了头,竟直接拿有孕宫嫔开刀。
诚然,他们自不知道苏妤本就同时存着两种想法,且“死得痛快”还比“活得舒心”的想法来得更强烈些。
他不开口,苏妤也不吭声。贺兰子珩淡看着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纹丝不动的苏妤,不知从何处觉出了两分清晰的赌气意味。
他也很想和她赌气,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
这个想法在他心中持续了短短一瞬便荡然无存。若论“僵持”的本事,他委实敌不过苏妤。
无声一喟,还是皇帝先开了口,冷冷笑道:“刚封了充仪胆子就大了?你明知陆润仪有着身孕。”
“是,所以臣妾才不曾罚她。”淡淡漠漠的回话。皇帝又一声笑:“那你还有意和她争?若她的孩子有什么闪失……”
“那臣妾给那孩子殉葬就是了。”这毫无所谓的口气,清清淡淡却又有着几分她在他面前常有的生硬。
贺兰子珩心觉自己这阵子简直不该由着她赌气。
“还讥刺陆润仪爱听玉碎之声,朕看倒更像是你爱听才总激得她去摔。”
皇帝的声音沉缓却平静,喜怒难辨。苏妤默了一默,叩首道:“陛下说是就是吧。”
“……”皇帝几乎在她面前僵了。终于绷不住,一把扯了她起来,哭笑不得地问她,“你就非得和朕这么顶着?”
苏妤的神色间似乎有一瞬的黯淡,贺兰子珩听到她喃喃说:“不管臣妾顶不顶……陛下要问罪都还是要问的。”
他倏然无言以对。
是,他从前对她如何,根本和她的态度没什么关系。她顶撞也好、服软也罢,他终究没多听过半句。
执着她的手很是琢磨了一会儿如何打破这沉寂,他淡淡道:“不是来问罪的。刚才那些话……”皇帝干咳了一声,“逗你的,别当真。”
苏妤点点头。
“这些事是章悦夫人差人禀给朕的。”他自顾自地解释着,明知她一句也没问。顿了一顿又道,“朕想说……如是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
苏妤羽睫微抬,静等后话。
皇帝问她:“你能不能自己差人来禀给朕?”
苏妤的担心又一次多余了,皇帝半点责备也没有。笑谈几句就施施然坐下,怡然自得的样子。
苏妤也随着他坐下,抬眼瞧见折枝满脸担忧。她知折枝安排了人下去,不住地打听霁颜宫的事,生怕陆润仪有个什么闪失。
她却是不担心的,因为她依稀看见陆润仪平平安安地生了一个孩子,继而画面一转,又看到她身着妃位朝服受封。
可见是不可能小产。
长秋宫,除却一正在禀事的宦官,旁边的一众宫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坐于下首之人听罢后,胸口几经起伏才平复下来,犹有几分不信任地问他:“陛下当真半点责怪也没有?”
“是……”那宦官一揖,“除却几句有意地假责,就没再怪云敏充仪什么……”
猛地一击桌案,却在瞥到旁边那人的轻笑时压住了怒火。
佳瑜夫人笑看着章悦夫人的怒不可遏,徐徐道:“我们都轻敌了,是不是?”
章悦夫人银牙紧咬,思来想去还是不肯承认,只狠然道:“不可能的……当年陛下肯为了皇裔废了她,怎么可能容她再伤皇裔一次……”
“那就只能是因为她还没真伤着皇裔了。”佳瑜夫人笑意不减地思量说,“不过这事倒真有意思,也不知她是有怎样的通天本事,从前陛下厌恶她那般,如今竟还能复宠至此,啧啧……”佳瑜夫人摇了摇头,“也是陆氏忒蠢,眼瞧着势头不对还硬要寻晦气,活该连陛下也不拿她当回事。”
章悦夫人重重舒下一口气,只觉自己丢人丢到了长秋宫。
“行了,你也别气。”佳瑜夫人笑睨着她,“后位之争,到底只能是你我一争,轮不到她。”
看着佳瑜夫人的自信满满,章悦夫人很是受挫。只有她自己清楚,皇帝近来虽是仍常到她的蕙息宫去,却是和衣而眠很久了。她一直安慰着自己,如若她是这般的境遇,窦绾必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看窦绾这般的神色……难道不是?
按捺着心中纷杂,叶景秋衔笑抿了口茶,目光微凝:“是,只能是你我一争。”
但在此争前,能除掉的绊脚石还是除了为好。
陆润仪被这一出弄得寝食难安。
没想到苏妤当真敢动她,罚了她阖宫的宫人不说,为了她能“好好安胎”,索性跟大监打了个招呼不让那些宫人回来了。
于情于理,大监也没理由不答应。
是以霁颜宫中竟无一相熟之人,好在楚充华那边调来的人做事也细,也不敢轻视她这胎,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
陆氏却是连安胎药也喝不下去。只觉这日日都要喝的安胎药比往日苦多了,苦到难以下咽。勉强喝了两口就搁到一边,在近前服侍的那宫娥倒是不像从前在身边的人那样苦苦劝她,觑了觑她的神色,轻轻道:“娘子若是实在喝不下去……便莫要勉强了吧,奴婢拿去倒了,晚些让她们煎新的?”
“倒就倒了吧。”陆润仪随口应了,眉心紧皱。她是当真不愿意从前在身边的宫人死了,且不说是不是担心他们的安危——她目下怀着孕,总要为腹中的孩子积德。
一时也有些后悔。她从来不是个聪明人,连她自己也清楚。常常心直口快的,说话做事皆欠考虑。
不同于叶景秋有时还给苏妤留点面子,她从来没把苏妤放在眼里过——不就是个弃妇么?她有什么了不起?
只是从前她位份低、苏妤亦避世,两年下来不曾有过什么交集,看不起也就看不起了。
可气的事,她有孕之时刚好是苏妤转运的时候。按理说嫔妃有孕该是宫里头等的大事,她却就生生让这么个弃妇抢去了风头。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抢风头。
心里自然是恨苏妤恨到咬牙切齿,倒要看看这么个弃妇敢拿她这有孕的嫔妃怎么样,可苏妤还真就动了刑。
确是她太莽撞了。陆氏不甘的一声叹,心里多少有些后怕。苏妤罚了她阖宫的宫人,皇帝却一点表示也没有。这还是她有着身孕,那等这孩子生完了之后呢?苏妤可还会饶她么?
陆润仪想着想着银牙紧咬,踌躇再三,终于一狠心发了话:“备轿,去绮黎宫。”
贺兰子珩毫不理会苏妤的不安地在德容殿看了一下午折子。苏妤不安归不安,经了上次的事、僵持了二十几日、加之今日这一出……眼见着皇帝半点也不怪她,总也不好再和他僵下去。
是以态度有所缓和。
研墨添茶,这些事苏妤做得也娴熟。贺兰子珩不动声色地瞧着,见她分明面上仍有惴惴,大概一开口就又是尴尬。
于是整整一下午,候在德容殿里的宫人听得最多的话,便是皇帝在充仪做了什么事之后,很是客气地道上一句“多谢”……
一屋子静默。
然后皇帝传了膳,二人同席而坐、同案而食,照样话不多,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隔阂,同时又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徐幽与折枝对望一眼,均是心中腹诽:这奇怪的气氛。
有急促地脚步声远远地朝这边奔来,徐幽定睛望过去,是个宦官。待得他到了殿门口,徐幽伸手将他拦住,眼见他跑得气喘吁吁,徐幽的问话显得更是慢条斯理:“你不是韵宜宫的人么?”
“是……”那宦官匆匆一躬身,“徐大人安,充华娘娘差臣去了霁颜宫……”
一听这话,折枝立刻挑了眉头,轻一笑道:“霁颜宫的人还敢来?莫不是知道陛下在这儿有心要告一状?别费工夫了,早先那些事,陛下根本不怪充仪娘娘。”
那宦官擦着汗也皱了眉,还没开口却见折枝神色一惊。
疾步而来的二人……是她吩咐去探听消息的人。虽知陆润仪胎像稳固,她还是怕出岔子,如今来得这么急……莫不是……
但见二人在她面前一揖,急道:“折枝姑娘,陆润仪来绮黎宫的路上动了胎气……”
折枝一惊:“什么?”顿了一顿又道,“她来绮黎宫干什么?”
“臣不知……”其中一人缓着气禀道,“只知润仪娘子突然说要来绮黎宫,臣便跟上了,谁知到了半路就……”
折枝还要再问,却听得徐幽重重一叹,向那三人道:“进殿跟陛下回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