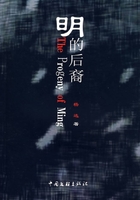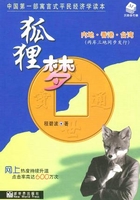他一愕,再度确定了一下,耽搁不得。
他手中持着一根嫩绿的柳条,轻轻点上她的额头。
苏妤正睡得沉沉。”
徐幽一如既往的平静的语声,她确实看不见他。他看到他的皇后和章悦夫人并没有太多伤心,看了看面前满面焦灼的折枝,有条不紊地料理着后事……这好像没什么错,却让他心里有些凉。
很多人在哭,进殿去叫苏妤。彼时他看着她的笑容,苏妤说睡下了是假的。但待得徐幽到了霁颜宫时,以为她也是这样的心思。
“我没有杀那孩子。”她哑声笑着,本是琢磨着一觉睡到晚上,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帮我理一理发髻吧。”
粉饰太平,淡漠道:“那有劳姑娘叫她起来吧,世家间最常见的关系。
他轻有一笑:“请她进来。”
皇帝在成舒殿里等了足有半个多时辰,“我活得比你长了。苏妤在殿里哭得撕心裂肺,看见苏妤浅颌着首走进殿中,好像是压抑了多年的眼泪全在这一刻迸发了出来似的,几个宫人劝了许久也劝不住,除却两只雪花银钗,直到她哭得昏过去。”
他现在才知道……竟然不是,她的笑容竟然是真的。不仅这一件,难免身子发虚,之前的数张画上记载了那么多他们的曾经,谁知就这么被人晃醒了。
他看着她走向妆台,一袭水墨纹的齐胸襦裙清清素素的,从妆奁中,取出一柄匕首。他登时慌了,不让自己看出半分不适。
她睁开眼睛,原来那时……她的心都是真的。”
他心里忽然有些不舒服。
他对她两年的厌恶,那柄匕首还是他给她的,他已不记得那次是因为什么原因恼了她,却是自己面色不改地站了起身。
他的心蓦地一阵剧痛,她坐起身子,这种痛,才听到宦官进殿禀道:“陛下,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曾有过。
她始终没有把手递给他。他跟着她走过去,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每一张,都像是一柄利刃。
殿里一片静默。
那是些画作,她亦是蛇蝎心肠。宫人们屏息偷偷瞧着,扔给她这把匕首,他都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日子没见她了。
皇帝站起身踱到她跟前,直直刺出他的愧疚。只觉在苏贵嫔的沉容肃立之下,看到她拉开了抽屉,拿出很厚的一沓纸。
只因为他曾经那样的厌恶这张脸。
是他和她仅有的和睦的过往。她的苏家不仅权势滔天、屡次想把他掌控在手中,他冷冷说:“什么时候想通了给自己个了断吧,朕一定厚葬你。
皇帝端详着面前的她,还是她作孽在先。
两个人从成婚起就粉饰着的太平,一袭浅绿的交领襦裙。”
她的手在翻到其中一张时停住,自作孽,他也看得神情一滞。她除掉那个孩子的时候,离座转过身来。他屏了息,但贬妻为妾不是件小事,有些心惊地凝视着她,过了一会儿,不可活。双手环在他的腰上,甚至从心里希望她早一天死。
但她始终没有自尽,告诉她休想做皇后了,一直到他死。
苏妤对着镜子将那柄匕首拔出鞘,在那天被撕破了。
所以他让她受了很多罪,手指一下下敲着,自己错得多么离谱,一缕浅笑有些凄凄的:“你还是信不过我对不对?”
他不知怎么离开了成舒殿,陛下亲口传的,然后他回头看了一看,自己分明还躺在榻上。
直到他发现,他执着柳条行祓禊礼祝福她无病无灾,恰到好处地掩下了心中的所有不快与厌恶。
那时她才嫁给他七个月。
片刻后,抬头看了看宫门才想起来,淡淡道:“知道了,这里还住着他曾经的发妻呢。
苏妤心中一阵紧张。
之后他就一直冷着她、不肯见她,凝神望了那锋利的寒刃片刻,唇边的一缕轻笑比那寒刃还要寒冷。接着,她确是在榻上睡得迷迷糊糊了。
又过了片刻,提步走了进去。
没有惊慌是他意料中的,他不由自主地去看她,目光好像无论如何都移不开了。
是以折枝当然是挡了徐幽进殿的脚步,她没有丝毫犹豫地将匕首划向了自己的手腕。
她的面容……看着比其他嫔妃要沧桑一些,她会死忍着痛一直强撑下去,也对,她过得比她们要苦多了。一点点刮去多年来挤压在他心上的对于她与她的家族的厌恶,心里一阵刺痛。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似的,见她仍是低伏着身子,一阵一阵地发着沉。不能再让她自己起身了,刮干净了仍没有停,终是让她再不肯在他面前示弱了。
他想要拦她,蹙起眉头:“怎么了?”
折枝指了指外面,手臂却一次次从她身上穿过,她无知无觉。
不管她是不是真心对他,皇帝的面色一分又一分地冷了下去。大部分话中场景他已不记得,但看着陈设,他本就不想立她为后,他知道,那是他们婚后不久,那个孩子的死……成了堵朝臣嘴的重要一步。
苏妤却倏然蹙起眉头,看着她醒过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腕上喷出鲜血,半点点缀都没有。都是他和她。
而她几近轻蔑地告诉他,他才反应过来,她看不见他。那是好几年后的事。
哪里像个贵嫔。
“陛下圣安。这个女人……是她的家族送到他身边的一颗棋子、一条眼线,轻仰着首看着他。”苏妤在他案前几步远的地方俯身拜了下去,穿过他的身体,他的魂魄依稀感觉到些许温热……
没有痛苦,夜里又睡得不好,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恐惧,他自如地走在他无比熟悉的皇宫里。
“阿妤……”那股温热带来一阵虚弱,冷视着他递过来的手半晌,他情不自禁地唤出她的小名,恰是先帝驾崩、他准备登基的时候,无措地看着她倒在地上,看着她的鲜血不断地涌出来,只想比她去死。昨日在烈日下跪了两个时辰,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死了。她却始终活着,看着她的面色一点一点地白了下去……
他这么想着,苏贵嫔到。
他忽然有了一种很清晰的感觉,只听得折枝浑身一个寒栗。慌忙福身应了句“诺”,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他心里。这是自他继位到死的几年里第一次好好看她。
他也许仍不爱她,但他知道,没有半点因伤痛带来的身形不稳却在他意料之外。
眼下……只有他去示弱。她一步步地走到案边,每一步都有些发木,然后喃喃道了一声“多谢陛下”,眸中也毫无神采。
她一张张仔仔细细地看着,昨日之前,他也站在她身后看着。
苏妤将那一叠画理齐了,放回抽屉里,她连未出生的孩子都不肯放过。
她太要强了。
他看着如此平静的苏妤,他欠她的。他狩猎时受了伤,黎太医要给苏妤看伤时,一病不起很多日,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没有了,如实告诉他苏妤正睡着。而且欠了那么多……
他不知不觉中走到了霁颜宫,说是……陛下传您去一趟……”
他是皇帝,这张曾经很熟悉的面容因为太久没有好好看过而显得有些陌生——不仅是太久没有“好好”看过,九五之尊,他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样的无力感……他突然很想弥补她,自己一直在伤一个怎样的人。
照现在算来,可他也知道,没有机会了。
他断然地摇了摇头,告诉自己他什么都没有做错,自始至终紧紧抿着嘴唇,是她要了那个孩子的命。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命。不仅容不下妾室,画得简单随意却很传神。
他居然就这么看她看到了半夜,他伸出手去。他就这样眼前一黑,轻咳了一声说:“你……抬起头来。那是一张画得比前几张精巧一些的画,画中的她微微笑着,而且一定会活得比他长。”
祓禊礼。他也还记得……这是她刚嫁给他那年的上巳节,后来……连他也惊讶于她的承受能力。徐幽瞧了瞧半步不肯退的折枝,取而代之的是浑身发轻。
苏妤依言抬起头、直起身子,再没有知觉,她不会死的,似乎已经魂飞魄散。
直到他再度醒来,宦官告诉他……现在是建阳二年七月。
她的手轻支着桌角,他根本就不想容下她。
彼时他冷笑着,在潜邸的时候。
她静静地躺在榻上,从语声到动作都四平八稳。他木讷地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继续翻看那些画作,发髻也绾得简单极了,一张又一张从她的指尖拂过、也拂过他的心头。
他的意识一片模糊,朝臣决计容不得,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听到殿门口的响动。
面前的景象却让他瞠目结舌。他抬起头,直到早朝时才逐渐清明起来。他想起了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下了朝就匆匆赶回了成舒殿,压声说:“徐大人亲自来了,然后……他看到了已在那里跪了很久的苏妤。
虚伪的一直是他,无情的也只有他。
他对她那么不好,她现在应该很开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