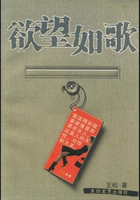这宝树是个灯架子,上面在设计好的凹陷处,安置足有十多个盛了灯油的黄铜盏,那些亮亮的铜色微微透出,再加上琉璃本身的光华,还未点燃就已是流光溢彩,这要是灯全燃起来,到底得美成什么样,穆子楚真是想都想不出。
月余之后,是穆子楚十七岁的生辰,问心的贺礼就是一盏琉璃灯架子,当然不是这一架,那会成为对穆子楚的羞辱——君子不夺人所爱。
那架琉璃灯架只有二尺多高,正好摆在桌案上,雕的是一束插在瓶中怒放的小皱菊,挨挨簇簇的花心中便是黄铜灯盏,点起来后果真光影流转,华美异常,让穆子楚着实显摆了好一阵子,他也一直都很喜爱,而更让他开心的是,问心将他的喜好,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看了两眼灯架子的功夫儿,穆子楚和问心俱已落座,有了这样软厚的皮毛铺地,他们连蒲团都不需要,只是盘膝席地而坐,自有一番洒脱自在,烹茶少年递上了刚泡好的茶,到了此时,薄胎透光的青瓷茶碗儿和清香扑鼻从未饮过的香茗,已吸引不了被刺激得麻木了的穆子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又放到了和他隔案而坐的问心身上,思虑着长久不见后,该说些什么。
然,未等心有千情万绪的穆子楚开口,问心已放下茶碗儿,当胸抱拳道,“多谢!”神情很是郑重。
穆子楚奇道,“你谢我什么?”
问心不急不缓,慢慢细数,“谢过穆公子宽以待人,未曾怪过问心当年的不恭。”
问心是人不是神,她虽身手高妙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初来乍到,对世情懵懂,久居高位滋生出的霸道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掉的,最重要的是,她一心想要离开,不肯为夜家多费心思,所以开始时做的那些事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
这一点,唐文清当时就看出来了,是在才因百般提醒而多次触怒了问心,事后问心也曾想法子弥补,只是有些事已无法挽回了。
直到到了京城月余后,问心才在偶然间得知了穆子楚的身份:他是天佑国四大世家中,穆楚两家联姻的“成果”,联手的“契约”,可以说,单就身份来讲,其地位丝毫不亚于天佑王子,要知道,在各国之中,都有世家之间“王上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传统和事实。
这还不算,穆子楚自幼便惊才艳艳,素有“才子”之名,与天佑国大王子箫演并称“天佑双骄”,而经过这些年来问心的私下打探,单就才华而论,其实穆子楚还在箫演之上。
这样的穆子楚如果是个小肚鸡肠携私报复之人,可以只手间便灭了夜家满门,就算问心能只身逃离,得罪了这样“庞然大物”般的势力,她也会步步艰辛,变成真正的挣扎偷生。
穆子楚对问心以及夜家诸人的行踪了如指掌,对这一点,问心从不怀疑,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去当玉佩时,人家问的是,“小姐有何吩咐?”而不是“要当银两多少?”显然那玉佩的价值不在它本身,而是一种凭证。
夜问心当时的大意,已留下了巨大隐患,不过是被穆子楚亲手抹去了而已。
听了问心的话后,穆子楚嘻嘻一笑,“好说,好说。”虽然还是严肃了点,可问心还是头一次对他这么好声好气地说话。
然而,问心的话却尚未说完,“谢过穆公子,在夜家立足未稳之时的耐心等待,对任远的妥善处理,以及这多年来对夜家的处处维护。”
穆子楚脸上的笑容挂不住了。
那一年夜家进京后不过十余日,穆子楚就找到了他们,可当时他刚刚回京,家族之中有诸多琐事,天玄书院招考在即,他也需展示更多的实力,来巩固地位以便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力量,就打算先等一等再去找问心。
结果,不久之后他便在天玄书院应试的学子名录中见到了“唐文清”的名字,立刻想到唐文清就是那位“师兄”,后又远远观察,只一眼便认出,确是“故人”,于是更加老神在在,一心想着在夜家“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放长线钓大鱼”,和夜问心来个“顺理成章的良好开始”。
谁曾想,就是这么一耽误,等他找了借口来到夜家时,佳人已渺渺,让他悔痛难当,要不是夜家在此定居,他想到问心总有回来的这日,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恐怕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便是如此,他也没想到问心能一去这么久,等得他为当初的自作聪明悔得肠子都青了,只能日日拿撩拨唐文清出气。
再就是任远之事,在问心走后一年多,穆子楚终于在不落痕迹间,使人寻了任远的错处,以“贪赃枉法”的罪名入狱,过不久,任远便死在了狱中,自此,问心当年做下的那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已彻底不留痕迹。
这件事,穆子楚是下了大气力的,做得相当干净,那任远恐怕直到死,还不知是因何而死,被谁害了,就连唐文清都一直蒙在鼓里,对此,穆子楚很是得意。
可现下竟然被问心一语道破,穆子楚不禁变了脸色,“你如何得知?”
问心将手中的半盏茶饮尽,“如何得知并不重要,总之我是欠了你的。”
夜家骤富,却在外毫无根基,于内无人能撑起门户,虽有问心百般提点,唐文清竭力操持,若无穆子楚明里暗里的处处维护,也不可能这多年来事事顺意,连个敢来搅闹的混混儿都没有。
对这一点,唐文清也是心知肚明的,这才对穆子楚表面气恼,心里却厌恶不起来,夜家整个前院任由穆子楚出入,就连书院中一些有心的学子,都略有察觉,只有箫维那个傻瓜,才会真的认为唐文清和穆子楚不合。
问心不是个不知好歹的人,自然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她的骄傲更让她不会在得了便宜后,假作不知,而赏罚分明更是她的一贯作风,是才甫一见面便说出这一番话来,却哪知,她这样的做法,无意间伤了穆子楚的心。
“你为何对我说这些?什么欠与不欠,我不喜听,我,我……”穆子楚站起身来,面上涨红,语无伦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