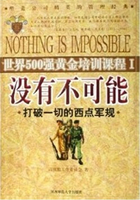“阿汐,这方子是阿晨从大内弄来的,不可浪费。”阿挽叔的声音像是被隔了层雾,疏疏离离的听不真切。
但是方子怎么会是从大内弄来的呢?
她身上的东西……那分明是武林人士呀……怎么可能是大内呢 但,脑海中不受克制的想起那个莲蓬钗的主人。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再,多喝点。”她听不见自己说的话,像是只吐泡的鱼。
她咳了咳,却发现依旧没有什么声音。
轻轻握住了阿晨的手,朝他安慰的笑着。
他有些紧张,连手都是那样冰冷湿滑。
有什么好紧张呢?
每一次都是这样,从希望到失望,再到新的希望……生生不灭。
她能隐约看见阿晨面上的动作,还有微张的口型。
就连医痴和那个人,都齐步走了过来,满脸担忧。
但是,他们到底在担忧什么呢?
他们的脸孔,在她的视野里。都像划破了涟漪的水波一般,苍白模糊的脸上浮动着急切的表情,连声音都变得摇荡不定忽远忽近,好像从深海传来的回音。
她试图去反抓阿晨伸过来的手,却发现自己使不上气力。就像是深水中挣扎着,拼命划动着手脚却无法上浮,像有绵软而力大无穷的水流绑住了四肢。窒息的恐惧瞬间扼住了她的喉咙。
手中的那碗药,也已翻到在地。
“汐娘!”白晨忽然厉声叫着她的闺名。
她虚弱的笑,很想像小时候一样骂他没规矩。
他握住她的手,手劲很大很痛。
一道血水却自她的嘴角溢出,她笑着,慢慢抹去了那血水。
哪里知道,喉头微甜,那血水却是越擦越多。
白晨的脸色巨变,好像在她的耳边大声说着什么话。
但是除了虚无,她什么都听不见。
其实,她想说。
没什么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
这样边吃边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早就牢不可分。
只要……只要他不嫌弃她胖走了样,嫌弃已看不出小时候半分清秀的颜面。
她愿意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这样苟延残喘的陪着她的阿晨 她嗫嚅着,准备开口。
却喷了阿晨一脸腥黄的血水,真的好抱歉。
紧接着,她放弃了挣扎,疲软的往后倒去 一只手掀开了稠帘。
他走了进来,也搅散了些许房中浓厚的药味。
这是一间女性气息很重的闺阁,彼时正错乱有致的摆放着数枚蜡烛。
蜡烛的正中间是一件石榴纹路的朱红嫁衣。
红的那样周正,缠绵。
那蜿蜒的花枝和张口欲裂的榴子,像是一霎时就要自嫁衣中生长出来般鲜活……美得那样动人心魄。
这来自于长辈对子女的殷切期盼。石榴多子,也隐含着对新嫁娘的美好祝福。
亦同样隐含着,那人的心意。
他的步子很轻,但还是惊扰到了人。
白晨一身玄色锦衣走了出来,见是他,没有做声,转身又往内间而去。
他有些诧异。毕竟在自己看来,认识多年白晨,却还没见过他穿月白以外的衣衫。犹记得白晨嗜白如命,又极度重视自身的容貌。
所以,就算他的妻子重病缠身,他也不肯自己没有梳洗就出来见客。
但怎么会是别的颜色呢?
不穿月白色……白晨也有怕触霉头的日子么?
这么想着,人已经跟在白晨身后缓步踏入。
宝象七珍焚烧的香气盘旋着,凉悠悠地缠在人的肩头。纵是如此,也掩盖不住内室的浓重药腥气。
霎时,他的眼神接触到了那里。
罗汉绣床上沉睡着的那个女子……她的蛾首浅蹙着,表情有些许痛苦。那哪里是个胖女人,分明是他的……他的呼吸渐不稳。
那对金色长睫此刻正安稳的停顿着,途留下一片鸦翅般的扇形阴影。
眨了眨眼,霎那的幻觉消逝。
她依然还是那张圆圆的睡脸。
他苦笑了一下,胸口噗通跳着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逝。是有多久,没有这样看着她了?
她早就不是记忆里那番模样了。刚才――哪里可能呢?是多少年了?
他记忆中的那朵小白梅,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
那年,他第一次……她在彼端,他在这头。
纵使只是一条没有任何意义的白色素稠,他也窃喜不已。
那时,他还不懂为什么要窃喜。
然而,每到午夜梦回时,那雨中的撑伞少女,她的四季歌。
“你有何事。”
他立时回过神来,连忙双手微曲,作了个武礼:“楼主……”
白晨坐在榻边,替睡着的她擦拭着盗汗。
彼时因为她梦魇而发出的哭喊,而将她拥在了怀中轻拍着。
“我已经不是玉贤楼主了。”白晨淡淡说道,语气和他的神情动作极不相符。
“白先生,难道你就能这么轻易的舍下你打下七七四十九个擂台,才从老楼主手中夺来的位置么?”他眉头微蹙,张口又道:“就算,白先生是为了夫人才做的这个楼主,难道真能轻易抛下这些兄弟的么?今日,属下是……”
“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汐娘的影卫。”白晨眉睫不抬,专注于将汐娘伸在外的一只胳肘送入暖裘。“何况我一开始就说过,夺下楼主之职是为了汐娘的病。若不是为了可以有足够的分量结交更多有可能医治好她的高人,我不会来到这里。”
他的面色有些赫然,纵然一开始就知道白晨的原因。
可是,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
怎么可能说放就放?
只因为,玉贤楼主的身份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吗?
因为她的毒,已经不是光靠结交奇人异士就能解决的吗?
这个男人,怎么冷漠如斯……怎么可以对除了她以外的别人,冷漠至此?
这些日子,他呆在她的身边。
所以对白晨的事情,只粗粗知道一些。知道他最近去了次大内,也知道他带回来了一剂药方。
但……效果并不理想。
那日,他听见白晨和医痴,挽先生讨论她的病情。
知道她用身体喂着那东西这么多年,那东西已经贪心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
所谓的吃食,早就不能压制下去了。
只怕,早在更久以前,身体的衰败就开始了。
知道她已经等不了了,他不得不加快速度寻医求药。连以前那些从来试都不敢试的险法子,都要一一用过。
但,她的身体依旧每况越下。
他咳了一下,轻声劝道:“既然夫人的病已经药石无用,白先生何必坚持离……”蓦然住了口,因为一只雕花瓷盏正险险从颊边飞过,溅起一道浅丝血痕。
彼时,正一滴接着一滴,缓慢的滴落。
白晨已经起身,一身玄衣飘炔,满脸戾气未收,冰冷的面孔上杀气凛然。
“出去!”白晨冷道。
“楼主!”他放弃了叫白晨为先生,就算方才一千个一万个顺着他的心意。一旦触碰到了她……他的逆鳞。他依然会出手,就像方才那样,只要再矮一寸,划破的就不是脸,是他的脖子了。
“你,也是说客么。”
“属下……”
“出去。”白晨咬牙切齿的打断:“你的脸,每一次看见,总会提醒我一桩事。”所以才会让他去做影卫,去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这辈子,白晨最痛恨的就是如果,可能这样的措辞,因为这样的措辞,总会让人不自主的替自己做起个保护罩来。将所有的事情,规避到了别的人身上。
但,自打汐娘那年受伤,他克制不住一次的想过。
如果,如果当年他的武可以习的很高,就可以从容躲过那次,而不用她替自己受苦。如果,如果当年他习的是医,他就可以救治她,让她不用受这么多年的苦。如果,如果当年这个所谓的玉贤楼左护法,根本没来过!
但,哪里有那么多如果?
如果,是懦弱人的借口。而他,是白晨。
影卫面色如纸,禁不住有些黯然。
他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如今再说什么,全是枉然……如果硬要给当年的事情找一个背负者,他无疑是最适合的。
“出去。”白晨言简意赅,眼风更是冷漠:“我并不想迁怒你。”但再继续在他的面前出现的话,就不能保证了。
知道这个男人所决定的事情,很难再改变。影卫只得黯然离开。
白晨,你知道不知道你丢弃的不止是玉贤楼。还包括了,整个武林啊!
但,恐怕就算白晨知道了,亦同样会宣布下一任的楼主人选。
因为与他而言,这个世界上除了司空汐,再没有值得他关注的事情了 好自私,好任性的男人啊!
但……这涩涩的心情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连想要自私和任性的权利都没有不是吗?
是因为,那个人,从来都不属于自己。
掀开厚重的棉帘,见那苍劲的树桠被北风刮成了个扭曲的形状,皑皑的雪景铺天盖地。风一起,便扑朔朔的挥洒着细小的,莹白的雪片。
乍见这满眼的白光,影卫忽然有些许盲晕;他连忙紧闭双眼,转身看了眼暗室,待渐渐熟悉了这番雪光,才沿着小路朝外慢慢走去。
他,细细回忆着方才所有一切都是灰白的,没有任何色泽,光亮一片时的模样……忽然有些庆幸,起码自己还有视力继续坏下去的能力。
只是,记忆中的那朵白梅……那人的眼睛,如今的她,目力还能再继续坏下去吗 一觉醒来,身下的床铺有轻微的震动声。
闭上眼睫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在马车上。
她的小手勾啊勾,果然不用睁眼也能将那篮子准确的摸到怀里。
她小心的抠出一块黏糊糊的蜜糖糕,往嘴巴里塞去。
嚼嚼嚼……再嚼嚼嚼。
那双淡金眼睫不期然的慢慢睁开,她的手凑近,直到那块糕点快凑到了鼻子前才停下。
果然是蜜糖糕啊……她想。
听见马车内有轻微的响动,白晨单手撩帘,回首看向她。
“醒了。”
“嗯。”汐娘点头,转而扶着车身坐了起来:“阿晨不用驾车么?”
“是匹老马。”白晨回答,静黑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紧盯着她的举动。
“哦。”这个意思是不用他亲手驾驶,也不会走错什么岔路。这点小小的领悟,她还是有的。
“我们回家,怎么不见挽叔?”她抠着蜜糖糕,撕下了小小一块丢进口中。嚼了一会儿慢慢咽下,继而再撕下更小的一块。
“我们暂时不回家。”白晨凑近,捏过她粘在颊边的一颗糕饼粒。
好闻的男子气息喷在她的脸上,薄面立马红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