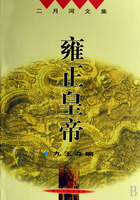义军汹涌纷起,国势衰倾,谏议大夫萧泽、左骑督将军薛皋、尚书仆射梁率等趁机上书皇帝,请治单氏。天铭平帝得闻单邯平日作为,不禁大怒,亲数其罪,削其封邑、夺其田产、罢其苛捐,并行诏全国,称凡已夺单氏田产者,皆承认其自有,只此一笔,单邯便损失巨大。
吴历三百五十七年春,最后一股奴隶军头领白波上表请降,这场历时三年多的民变才告终结。而在沉重打击了单氏的基础上,天铭国经济亦受到沉重打击,丞相何堃威望大减,使得萧泽等改革派复又登上政治舞台。
摩陂禁宫。
“长海秋平”殿。
天铭都城摩陂,距天焦邱都一千七百里,伏氏奎城一千三百五十里,昂州骑月城三千一百九十里。文帝昭和元年,天铭举国户口计有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三百户,人口七百零三万一千五百十七人,堪称大国。
摩陂乃天铭国祖、敬德武皇帝比繇在位期间所筑,费时七载,尚称坚固,而禁宫各殿,却华丽奢靡、所费巨亿,可谓宏伟之极。如今除宣帝年间因火灾而毁的三处殿宇外,尚存七座,分别名“山川锦绣”殿、“峦平风清”殿、“云波霄汉”殿、“社稷安泰”殿、“丰谷比年”殿、“长海秋平”殿和“明潮东升”殿。其中题有“社稷安泰”、“长海秋平”匾额之二殿为主殿,各有九进,为正式朝会时聚所。
谏议大夫萧泽,此际正从容走进殿中。他虽年近七旬,仍不显老态,步履稳健、身形巍然,此人乃天铭名臣,文帝时便赐“赞拜不名、入朝不趋”的特权,且此公持正嫉恶,擅涤旧劣,因而备受朝野钦仰与尊重。
天铭平帝比真看见萧泽上殿,笑道:“老大人如此操劳国事,朕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来啊,赐座!”
萧泽躬身拜道:“谢陛下!老臣受君荣禄,自当如此,且臣对理政治民之事甘之如饴,故不觉劳。陛下恩宠,老臣已有愧矣。”
比真哈哈大笑,道:“老爱卿上殿议事,也是朕的福祉啊!快坐下。”
萧泽谢过,未及坐便道:“老臣得闻伏氏国出兵子绛之事,未及更衣,便径自入宫,还望陛下恕罪。”
比真摆摆手,以示无妨。缓缓敛容,拈须道:“原来卿也得闻了,朕正因此烦忧。老爱卿有何计较,但请说来,朕洗耳恭听。”
萧泽欠身道:“不敢。臣儿妇乃昂州人,故甚知吕澍其人。此子今为伏氏秩禄比公的大将军,掌窃权柄,其妻单氏,霸国故奉车都尉后,曾荣忝天焦国公主之号。此二人皆有机谋识断、远大抱负,故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天铭平帝深以为然。校尉陈原出班躬身道:“萧公所语确凿。那单勰虽是女流,却极擅用兵,未尝失手,先是以退为进,全歼雨师,斩其帅许勇,后分兵奇袭,突拔其国,再后又行军古阴平道,奇出黄泽以击柳丘。其胆识勇气,令人瞠目!而今只作南下之姿,便迫降敌将,全获十万兵马,威震南邦。恐怕即使李竞大人用兵,也不过尔尔。”
李竞者,吴朝时人,与许远、楚邵、单鑫、令狐眉等并称“广铭六俊”。六俊之首乃天铭开国君主比繇。
吴历二百九十七年,李竞率天铭、天单国联兵十四万攻天焦,围军事重镇大作,使卫衡一年未解,名震吴陆。其拜大司马大将军时,年仅二十一岁,风度雅美,少年英豪,故常为人乐道。
李竞在天铭的名望,好比贾昆之于土益、孟乔之于伏氏,况且此名已被代用为“年轻有为”的同义词,常有青年英杰,被誉“子岂非当世之李竞耶”?多显荣光。
终李竞一世,为天铭开国所作出的贡献,远远不止围攻大作这一件。他七次担当领兵大将,抵御天焦军南侵,六次大胜,一次因粮尽退兵。十二次领率方面,征伐小国,开疆拓土,无往不利。后因打猎,马失前蹄坠崖而亡,年仅三十二,比繇为哭之九日不朝,命在摩陂西北雄鸠山起筑墓室,其高处立碑,遥眺天焦,以纪念他围攻大作的功勋。
如今天铭国中有李弋者,便是李竞后人。其家传兵法,所识在常人之上。数年前也曾带兵征战,获得将军之职,然而因小人谗言,惹怒君上,故被罢黜回乡。如今教授子孙、经营田庄,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陈原继续道:“如今雨、子绛悉定,依二子野心,岂能不犯天单?故萧公急迫如此,情势所然也。”
萧泽微微颔首,道:“陛下,陈校尉所述,亦老臣之忧也。一旦伏军来犯,天单势必求援于我,陛下诚宜择派良将,遴选精兵,以主守关狙敌之事。”
平帝比真叹道:“天单国早有羽檄在此了!朕因此事,正与众卿议得头昏脑胀……”
近臣王秀朝萧泽阿谀地笑道:“皇上也正为选将之事烦恼,萧老大人若能举荐贤良一二,领兵东陈,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萧泽拈须呵呵笑道:“以老夫看来,王大人便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王秀顿时面如死灰,肥脸一颤道:“不不不,小臣、小臣不是为将的料,萧老抬举,抬举了!”
殿中群臣相顾莞尔,暗地里不禁窃笑起来,平帝比真只作未见,微笑地道:“看来老爱卿已有人选,不妨说与朕听听。”
萧泽起身拜道:“臣想先听听何相之意。”
丞相何堃在皇帝目示下,赶忙出班奏道:“既然萧公发话,臣斗胆,仍向陛下推荐西部都尉岳彬,此人现补为丞相府计掾,受秩比千石!”
岳彬乃比真嫔妃岳氏之弟,何堃曾举其贤良方正,而任以丞相府职奉,后又多方极力“推举”,以招媚主上。不过岳彬此人体格健悟,又曾游学天焦,深得皇帝赏识,常蒙召会,深受宠信,故宦途一直顺利。
萧泽哈哈一笑,问道:“诸位大人还有什么其他人选吗?”
尚书秦朗沉声道:“臣举左骑督将军德乡侯薛皋。”
顿时有人附和,亦有另举荐卫尉荀清或将军戴武、寇奕等人的。平帝比真问道:“老爱卿以为何如?”
萧泽回道:“依臣看,这些人选当中,薛将军、荀大人皆为将佐之才,可担重负。然薛将军年事已高,荀大人负责禁中安危,皆不宜授领方面,而岳彬等人,资历尚浅,无将帅之望,故又难堪大任。”
何堃忍不住暗中冷哼,斜睨了他几眼,朝主上拜道:“萧公此言失矣,吾所举西部都尉岳彬,乃上之御亲,陛下常欲使他领征伐之任也。其在相府供职,亦秉烛明义,多有才望,如今举荐为将军,抚使镇东,似乎并无不妥。”
萧泽不假辞色地斥道:“正因岳彬乃是王亲,无上阵讨贼经验,故拜兵封将,最是忌讳!一旦失利,他罪行重大,连陛下亦须担察人不明之责,至于何相举荐庸官之失,朝议之上,又会当何如呢?”
何堃心头一凉,暗道若此情状,连带削官贬职还算轻的。嘴上兀自不饶道:“我为天铭江山社稷,哪能顾得那么许多?如今群臣所荐,萧公皆不以为然,那么到底何人领受将职,方算妥当呢?”
萧泽淡然道:“陛下,臣之所以慎重,盖因伏氏国有吕单之流,皆世之大贼也,两岁之间,先后数度征伐,军锋一出,无往不利!而此际伏氏疆域竟也超出我朝多矣!陛下若不遴选资望相当的名将出战,恐怕难遏其势啊!”
平帝比真闻言,也自沉思良久,方才点点头道:“老爱卿所言是也,不知有否适当人选哪?”
萧泽沉吟少顷,毅然道:“臣举荐者,十年前数度拜将,东征西讨,无可当其锋锐者,而两次平定西变,一次救援先帝之功,其名更是人人知晓。”
平帝比真思忖半晌,恍然道:“爱卿是说那李弋吗?”
萧泽道:“正是。李弋有良将之资,用兵稳健,攻守兼备,其不为我用,乃国之失也。当年有人进弋谗言,以至触怒陛下,削其爵禄,贬为庶民,如今看来,他根本没有造反之意,而是有人居心叵测,陷害忠良!”
何堃面上一阵红一阵白地,默默垂首,群臣无不看在眼中,心道果然是他!原来,当年比真初登大位不久,适才平定西部诸郡叛乱,忽然接到密章,劾将军李弋心存反意,大为吃惊,乃招其进宫,罗列诸多罪名将其革职。那时若非萧泽等苦劝,恐怕天铭史上又将多一件冤案。
何堃心中有数,若非那卷奏简“更立大功”,自己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国相的位置。十年来,皇帝对他信任有加,以至单何之盟根深蒂固,终至有奴隶爆乱之事,其实若非如此,何堃仍可以只手遮天。
看皇帝意动,萧泽继续劝谏道:“李弋有功于朝廷,不蒙封赏,反为贬黜,令贤良寒心。今陛下诚宜张圣明、举才干,号令天下。若如是,则伏氏大军前来,也必无功而返。”
比真沉吟道:“依卿之见,该复以李弋为将?”
萧泽道:“正是!”
此时殿下群臣多有赞同之声,御史大夫边韶道:“陛下,李弋乃竞之后人,于军才、名望之上,都不亚于吕澍卓羽之流,此人领率镇边,必能保寸土不失,望圣上明鉴。”
廷尉周擎从朝班之中斜跨出半步,微微躬身道:“臣以为:李弋获罪自省,至今已有十年,早该重新录用,以弘我朝之仁慈宽厚。陛下若拔之,则又多一臂膀,可谓两得。”
平帝比真终下决断,缓缓颔首道:“那就依诸位爱卿之议罢。传旨,即日诏李弋入宫,朕自观之!”
群臣躬身道:“陛下明见!”唯丞相何堃等人表面恭敬顺意,暗地里早又起了无数歹念。
(第十节
吴历三百六十年三月。
土益国发兵十二万自淄洮渡河北上,攻击岱地的熊军。其前,武城公主单勰命帅青自原子绛国境中发兵五千相助,而天焦国则遣其后将军徐叔并其营兵马二万人入境参战。
其月上旬,联军与熊子战于平氏,小胜;熊军疾出蓝口聚,袭土益军后路,败土益国威远将军马炎。
乙亥日,联军围重镇孝化,攻十余日不下,熊国援军至,为后将军徐叔击溃,败走临含。己丑日,熊军全面败退,联军遂取十五城,尽掠岱地。
四月丁酉,熊国御弟大督杨炯遣使求和,条件十分丰厚,王乾允之,而土益军帅,车骑将军庄鉴激烈反对。王乾便临阵换将,遣平北将军、宗亲王福为帅,与熊军议和。
五月丙寅,熊国御佐(熊王诸位兄弟配属之首领幕僚)杨翼与王福会商,乃决议熊国供牛羊马匹共四十万五千头、黄金白银各十万镒为和议之费,两国自比阳、朗州、新息一线分疆,熊国归还岱地与土益国,而土益国则停止对熊国作出额外的领地要求,息兵止戈。
王乾此议,震动国内!原本土益北境,尚有雉县、阳翟、郦都、商丰等九城,因戍边之需,常迁内地户民实之,如今议和后,土益只取回对岱地十数城的统治权,而北境险隘之所,竟承认了熊军的主权!王乾贪利妄为,令国中风云涌动、民变纷纷。
而此时,打了“胜仗”班师回国的帅青,也并无兴奋或自矜之色,而是星夜上表,分别送武城公主并邱都“北地王”吕澍府邸。
“土益可伐,若不早图,必为他人所取!”
帅青虽与庄鉴在此战之中有所交往,也钦佩其为人,但对于其国,却无半分好感。土益吏治混乱,朝廷中奸小并行不悖,而忠良受害,独独一个庄鉴,也是时贬时谪,真是无道之至。
天焦邱都。
城西耀贤里北地王府宅。
此邸府开四门,其中正南御道门前设王府正亭,立恒帝亲书御碣,百官下马。
府邸三重六进,门前斗檐直飞七尺,四根朱漆粗柱,一人也合抱不来。府外白玉龙凤围栏并镂雕之玉石地面,直通往深深的照壁之前。两扇正门以精铜铁铸成,其厚九寸,上赤下玄,以示主人地位尊崇。首进照壁以五狮五虎为边饰,中镌司徒穆丹题“覃思德懿”四个大字,显赫非常。
前庭与中庭间有名曰“镜池”的小湖,十亩水域,微风轻澜、波光粼粼,湖边杨柳成荫,奇石异木星罗棋布。湖上有多基拱桥跨越而过,共二十七孔,漆以白色,清新雅致。湖岸对面有亭台楼阁,乃是王府中心,恒帝卫召曾数次前来,与吕澍把酒畅饮,赏景赋诗,以示其恩重。
然而,皇帝的这番宠信与厚爱,并未影响吕澍清醒的思考,加之傅宪从旁劝谏,更使他坚定了不结贵胄、不用权势、藏锐避锋的主意,自受拜以来,小心谨慎,未尝延请帝胄门阀,亦未刻意交好权贵,不居功自傲,一切随遇而安,故更得上心。
此际已华灯初上时分,府内外皆有左右羽林都骑军战士巡逻,执戟来去,意气奋发。
而天焦国“北地王”却在镜湖南面的雅阁中,与心腹傅宪秉烛夜谈。
吕澍轻轻地哼了一声,道:“近得奎城密函,乃是校尉帅青劝谏用兵土益,吾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傅宪深体主上用心,闻言淡然笑道:“此际与土益反目,实是有害无益,将军宜先定南麓诸国,再缓图之,方为上上之选。不过帅大人方从岱地回来,深知其短,恐为熊子先趁,故有此谏,将军也不必太过苛责于他了。”
吕澍摇了摇头,又看了对方一眼才道:“帅青此人,确有过人之才,然不宜太骄,否则必败,吾欲寄书公主,由她定夺,不知傅兄以为如何。”
傅宪抚须颔首道:“如此甚为妥当,公主身边有玉况等人,皆非凡愚,想来对此必有见教。”
吕澍称是,忽地展颜一笑,“对了,近来还有消息,说公主攻下子绛国后,改其名曰‘绛州’,以蒋毅为牧伯,王贞为长史,又命四营讲武于奎西,大操十万兵马,看样子是欲对天单有所动作!”
傅宪闻言踌躇半晌,小心地摇了摇头道:“只观公主未有表章,便可见其取功心切,此不利战也!将军,今伏氏急下两国,如蛇吞象,士气已竭,哪里还再有精力往西用兵?更何况天单乃天铭附庸,其国危倾,平帝焉能坐视?在下以为,将军宜快马发书,劝阻此事,免得公主轻率致挫,得不偿失。”
吕澍眉头一皱,用手指轻轻扣案道:“这么说来,攻伐天单之事,还要再缓一缓?”
傅宪素知吕澍有并吞南域、争霸两陆的王道理想,然近来连连取胜,也不免稍稍显出骄气。单只他这么一问,霸气、野心、博志便都赤裸裸地显露出来,大异平日气象。
微微躬身,平静地道:“用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今公主数度征伐,连取雨、子绛,境土扩张,此诚地利也。然而二国初定,州郡甫建,如此情形下若再兴征伐,苛捐必起、税赋必增,百姓未见仁政,却陷身于水火之中,岂能不乱?一旦变起,我军势不能两头兼顾,而吞并天单、天铭之计必沮也!”
再起身致礼道:“将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谋。罢戈修政、变迭劣制,使郡县足而百姓丰,使财货足而国家强,则诸侯贡献、四方咸伏,将军亦可坐收其利,岂不善哉?用兵之事,还请将军三思!”
吕澍沉思良久,不露声色地缓缓点头道:“傅兄所言,万金之策也,澍多有疏忽,又不曾斟酌,以致冀妄穷兵黩武,徒贻笑大方,以后还要赖傅兄多多点醒才是啊!”
傅宪谢过,复又禀道:“将军在昂州施行之政,不妨用在绛雨二地,在下以为,尚书丞单融老于政治,可担此任。”
吕澍颔首笑道:“就依傅兄之议,明早即函奎城,着玉况办理。”
两人议论良久,话题慢慢转到天焦国与恒帝身上。傅宪劝道:“将军应早作决断,不可栈恋繁华,否则称霸之计,必将折废半途。”
吕澍稍显苦恼地长叹了一声,悠悠道:“非是吾想如此,这两日,澍也数度入觐,剖表心志,无奈皇上坚意不允,仍命吾安心在邱都休养,澍也正在为难之际呀!”
傅宪呵呵笑道:“依将军之才志,孰能屈之?我王不能,恒帝亦不能也。将军今在两朝皆有秩号、封邑,一曰大将军、一曰北地王,荣宠以极,日久则必生祸害。况卫氏意在将军改投门庭,效忠天焦,将军如此推脱君臣之义,恐其后皇帝亦会对将军做出不利之事呀。”
吕澍起身,推开雅阁旁雕工精美的小窗,仰望皓月,良久方叹道:“伴君如伴虎,吾岂有不知?此地荣华富贵,在吾看来皆是虚幻,又怎会有丝毫爱恋?傅兄,此事上汝还要为吾仔细筹谋。”
傅宪长揖道:“在下必尽绵薄!”
奎城。
伏氏内宫长秋殿外。
尚书令司政院。
武城公主单勰之车阵仪仗,浩浩荡荡地向前驰来,司政院外,以玉况为首的伏氏臣子列队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