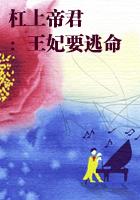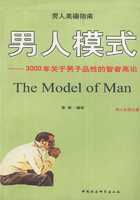丁吉嗫嚅着讲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擦汗。焦百颤声道:“丁大人,吕贼取得虎符,想必早已将大王控制在手中了!我等跟随鄚妍,哪知是这样的下场啊!”
丁吉勉强喘了口气,指戳着急促地道:“问,问问玉况,他说了算!”
焦百点了点头,登上望台。高地之下,旌旗遮日,人马无数,那情景顿时令他头晕目眩,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提高声音叫道:“玉大人!奔潮太守焦百有礼!”
玉况拈须颔首,并不答言。
焦百无奈,继续道:“还望玉大人谅解!焦某与丁大人亦是受了那奸贼的盅惑,假传王诏,命我等前来。如今见到王符、节印,才知其然!还望玉大人能在大将军面前为某等开脱一二,则不胜感沛!”
段、卓等相视微笑。玉况冷哼一声,道:“焦百!王符令信在此,由不得汝等滥言!大将军已有命令,及时悔悟尚不算晚!若假托鄚贼伪诏之事辩白,不是显得太可笑了吗?汝等所来奎西,难道也是奉了诏命的吗?”
焦百差点瘫倒在望台之上,被甲士搀扶着慢慢走下。丁吉竭力稳定肥胖的躯体,哽咽着道:“如今走投无路,不如向吕大将军请罪,还好保全性命!”
焦百脸色煞白,呆滞地点点头。寨中,那天关营校尉提缰跃马,高声道:“请二位将军随我下山!”
营门重新开启,方才布置的三千弓箭手也随着主将的乞降,垂头丧气地各自收拾起来。玉况安坐马上,冷冷地看着焦百、丁吉二人连滚带爬地来到面前,叩首如捣蒜一般,连声称罪。
眉头一皱,厉声道:“汝等甘为鄚贼走狗,进犯奎西大将军部曲,又不顾自郡戍守、率兵入京,按理当斩!今大将军宽仁宏义,尔等自缚请罪去吧!”
命将之羁押起来。高声道:“奔潮营、望海营将士们!焦百、丁吉谋逆造乱,罪有应得,却与尔等无干!今大将军明睿天下、智察万里,平定朝廷丑佞,只在顷刻尔!如今我命太仆冯勤代领奔潮营,城门校尉孙镇代领望海营,其余将士各按其职,不得有误!”
二营兵士耳耳相告,各自欢喜,不多时便多传来欢呼之声。冯勤、孙镇抖擞精神,跃马驰其营中,接管将命,原本一场两派之间的生死大战,竟在玉况等以虎符节印与心理战术的攻势之下,消弥于无形。
卓羽、段授望着玉况冷削从容的侧面,心中之敬佩又更增几分。
奎城大将军府。
是日夜。
玉况请交还将军节、印,吕澍免冠相迎。
吕澍笑拜道:“玉大人劳苦功高,今又出奇策,不损兵卒,便攻克望海、奔潮二营,果然是韬略如海啊。”
玉况揖道:“此皆将军神威,大王虎符之力也!”
吕澍抓住他的手,笑道:“若无玉大人如此宿将重臣,怕焦百、丁吉等辈也不会那么轻易归服吧?”
玉况连称不敢,道:“还有一事。适才向二营施威,玉某未经将军允准,已先行许诺保下丁、焦性命。”
吕澍哈哈大笑道:“大人何罪之有?放此二人,如赶鸭出笼,无伤大雅,反倒是玉大人临机施变,做得很好!”
玉况见吕澍正在兴头上,趁机谏言道:“如今四营皆在我手,将军除奸涤恶,指日可待。下官还有一事,要乞求将军恩准!”
吕澍颔首道:“玉大人请讲。”
玉况道:“下官初起之时,蒙徐栈照拂,恩累经年,能得今日之位,亦多赖此,如今他随鄚贼为逆,虽该尽诛,但还请将军念在玉某平日些许微劳的份上,放他一条生路罢!”
吕澍脸色倏变,立住脚步不前。
玉况见状,忙跪伏在地,叩首急道:“将军仁厚宽怀,朝野素闻。何况徐栈三世老臣,忝荣虚名,若斩之必伤人望,不如开恩暂释。玉某诚心以求,望将军恕罪!”
吕澍叹了口气,缓缓道:“玉况啊,我吕澍当真是不如徐栈么?为什么你两次三番,为他请免,却不能顾及我的感受呢?”
玉况闻言,涕泪横流,连连叩首,“下官该死!下官该死!将军对玉况信任有加,恩重如山,此生若某不能答,来世亦当结草衔环,以报圣明!”
吕澍长叹良久,这才搀扶起他,“大人不必如此,吕澍无能,却有大人这样贤才辅佐,何其幸也!所请之事,便请酌情去办吧!”
玉况闻言,更加感动,泣道:“将军何厚也,玉况拜服!”
奎城内宫德阳前殿。
翌日。
宫门四边,号角齐鸣,鼓声震动。忽正南殿门开启,百官着朝服依次行入,步伐整齐。大殿四处,金甲武士执兽旗立队,彩带鲜织,随风而舞,光耀夺目。
朝会在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
百官进贺,依次在殿中排开席位。左边是各级将军、校尉;而右边,则以太常李获、廷尉鄚妍为首,公孙述、齐堃等赫然在目。
御史王贞喝道:“大王命五郡贡献——”
伏氏举国分三州,即文州、平州、昂州。文州治所亦名文州,平州治所下杭。文州下分三郡,即奎郡、马邑郡、雁西郡;平州下分二郡,望海郡与奔潮郡;昂州尚未分郡。朝会中除昂州外,另五郡献上贡物则是例行规矩。
廷尉鄚妍向左首微侧,轻声道:“丁吉和焦百二人怎么没有来?”
齐堃道:“下官不知,该是在奎西正与昂州军作战,故而缺席罢。”
鄚妍眼中凶光一闪,咬牙道:“吕澍这狗贼!”
望海、奔潮二郡别驾献上贡物,拜谢退下,见他们的上司未至,王贞的眼中,不由得露出一丝讥嘲的笑容。
伏王单珲以稚嫩的声音道:“孤继位以来,承各位爱卿相扶鼎力,终有小成。彼年又风调雨顺,故兆民丰足,朝野安定……”
光禄勋余靖缓缓颔首,似对自己所教十分满意,喜色洋溢。他哪里会关心眼下伏氏国内外交困的惨淡局面?连附庸雨国也敢进犯昂州,早已没人再将这个南麓大邦放在眼里。
群臣听毕,无不躬称万岁。鄚妍下阶奏事道:“启禀大王,原左丞相近鹿侯徐栈,因事贬黜在先王陵茔前静思,现已期满。徐相深孚人望,百姓称道,应早复职位,以安众心。徐太后亦念父心切,同上表章,还请大王圣裁!”
单珲早知其事,喜道:“王舅早该赦免,都是那吕……来人,宣王舅上殿!”
尚书令单贺起身道:“大王,臣有一言容禀。”
单珲不悦地瞪了他一眼,恨恨地道:“讲!”
单贺神色悠闲地环视着脸上俱有惊悸之色的大小官员,微笑道:“徐栈为党魁恶首,向与单因并称,所在奸秽,并行不悖,不为废杀已属万幸。况且,两党争乱,律法空置,百官兢兢,无人再愿看到有人秉权为乱之象!如今,大王却把徐栈从黜废之中加恩开释,未免太过!此事还望三思!”
单珲转向余靖,口中道:“这……”
余靖见百官议论纷纷,不禁大怒,指着单贺道:“竖子安敢有辱君上!徐栈乃太后之父,身份高贵,岂容汝等加秽!且大王与之有亲眷之恩,叔侄之情,汝又怎可造言非常,鼓惑人心?”
单贺冷笑道:“依余大人之见,便该当将那徐栈放出来,重任为相,继续前朝之事喽?”
余靖一时语塞。单贺毫不客气地继续道:“徐栈为相,政治潦倒,而致民生困苦,他又一力截挪公田官储,移为私用,在位十载,有宅邸百余座,奴仆数万人,试想这样的人,又能让我如何加秽?”
余靖连连冷哼,却是无法辩驳。鄚妍见势头不对,出班道:“臣闻吕澍行为不端,劣迹彰于朝野。而单贺与之勾通,数有不轨,臣等早想劾他!如今吕澍畏罪称疾,私设部曲于奎西,又交通内外,图谋叛反,大王应尽早除之。”
单珲大怒,道:“单贺,可有此事?”
单贺拜道:“大王岂不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鄚妍损坏邦纪,祸乱百姓,他才是真欲谋反!吕将军神勇忠义,却平白遭此诬陷,怪不得会称病不朝。还望大王明鉴!”
司农校尉刘禹道:“鄚妍图谋造反,早有蛛丝马迹,其假借王诏,密令望海、奔潮二营屯文州,牵制大将军,又多招猛士谋刺大王,如今反诬在吕将军身上,着实可笑!”
虎贲中郎将蒋毅朗声道:“正是!大王耳目闭塞,才会偏听偏信,使鄚妍这等小人混迹于朝,吕大将军有大功于伏氏,不见加赏,反要加害,这必会寒了忠臣之心啊!”
殿中顿有多人应声称是,鄚妍大为惊心,狠声道:“你们……你们都反了!大王,该当将这些叛臣贼子统统斩首不可!”
单珲还未答话,猛听殿外有人高声道:“该斩首的,怕只是你自己吧!”
百官闻言震动,皆往殿门望去。只见一人戍装隆重,腰佩宝剑,缓缓跨入中门,殿中甲士俱执戟不敢稍动,敬畏之情,溢于言表。此人,正是伏氏大将军、骑月侯吕澍!
他的身后,紧随五人:卫尉曹侯玉况、骁骑将军汕乡侯卓羽、大将军司马段授、太仆领奔潮将军冯勤、城门校尉领望海将军孙镇。昂州甲兵,随之四散分屯殿下,顿时取代了原内宫卫士军的地位。
众人参见大王。吕澍沉声道:“大王年岁尚小,故而受人蒙蔽,不知忠奸好恶。鄚妍狡儿顽徒,其所结交,俱为故单因党羽。李获、公孙述、齐堃、孟介等人,纠集群丑,无视法纪,淫乱宫闱,横行乡野,个个都够得上抄家灭族!大王不咎其责,反来问我吕澍,岂不怪哉?”
单珲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
鄚妍见陷入吕澍圈套,强自镇静道:“吕澍!你带兵入朝,目无圣上,难道这不是死罪吗?”
吕澍呵呵笑道:“除恶务净,铲奸必清!死到临头,还这般嘴硬!”疾向单珲躬身一礼,“大王请下旨诛杀此人,原鄚妍朋党,尽皆抄没。臣已命四营兵甲驻防城中,以策大王万全!”
余靖怒道:“吕澍!你要造反——”
玉况冷哼一声,昂州甲士顿时四下围上,将他按倒在地,脖上并架多剑。不多时,鄚妍等惊呼四起,亦在被擒之列,殿中百官悸殚、兢兢战战,鸦雀无声。
吕澍冷冷道:“余靖,汝以邪妄之说迷惑王上,已犯大罪,待死之人,还敢在此唁唁狂吠!拿下了!”
昂州甲士七手八脚地将之拖出殿外,其暴喝长嘶之声犹然在耳。
单珲牙关颤抖,不由自主地蜷缩在王位的一侧,御史王贞见状,拖长了声音叫道:“大王准奏——”
吴历三百五十八年春正月,伏氏大将军吕澍先诛王师余靖,后族灭鄚妍、公孙述、李获、齐堃四人,连坐其党徒共三十余。当月抄毕鄚妍等百余座豪奢宅院,共搜缴财物折钱二十四亿两千七百多万,超出当年伏氏全国赋税总和,乃皆纳入府库,诏免了全国半年租赋。流徙阴谋勾结、妄图篡权的徐栈,并以庇短护私,杵违先王之罪废杀徐太后,确立了在朝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凡见识吕澍在这场宫廷争斗中的表现者,多死心蹋地,无敢再生贰意。
(第十节
吕澍自取得朝政大权后,肃清对立,废除丞相,建立以大将军为中心的新朝组织。大将军府自慕掾属,掌握举国兵马,隐隐已有朝廷的构架。原卫尉、曹侯玉况位迁尚书令,代统政务,传达将军府令,号令诸营,俨然成为伏氏新的权力中心。吕澍更延聘师兄单融为尚书丞、政务令,为玉况副贰。
诸营整饬,向来为吕澍所重,故拜段授为护军将军,代统氾水营;卓羽职秩不变,赐金一百斤、増邑千户;奔潮与望海二营不再属边郡统领,迁城门校尉孙镇为建威将军,统望海营;另拔原尚书曹髦为偏将军,统奔潮营。
内廷方面,原内宫卫士令姜率调任将军府掾,现职由御史中丞孙温执掌;正式除蒋毅为殿中军指挥,增邑二百户;城门校尉部由玉况所荐故耒阳侯肖重子肖笠统领,一时将鄚妍等所遗留下的祸害,清逐得干干净净。
吕澍上台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改革弊政,恢复生产。伏氏国山多地少,难以大规模屯耕,本无丰年,若遇大旱大涝,颗粒无收,则百姓流离,仓檩空虚。官吏隐瞒田亩,蓄养奴隶,更是为害惊人,哀王时登入籍册之田亩,至今余下不到三分之一。
重登田籍、削弱奴隶主势力,无疑是吕澍当前推重的主要决策。
除此之外,他更有水利、工程、渔业、冶炼等方面政令出台,推行新政后,除“家无薄田、室无余财”的玉况坚决拥护以外,单融、单贺、刘禹、孙温等亦积极响应。
二月庚午。
奎城大将军府。
雨。
吕澍眉头紧皱,正自对着桌上文呈发呆。
这封羽檄乃昂州骑月城加急发来,报告雨军入侵的消息。武城公主单勰求请援兵一支,依计行动,挫败敌师。
而吕澍考虑的,不单单是击败敌人那么简单了。如今天焦正忙着和五国结盟共战熊子,无法对南麓用兵,正是取得南域的绝好时机。不过,若是真的统一了南麓,天焦恒帝是否会害怕伏氏坐大而加兵威胁呢?天焦迟早要与一战,然而此时对垒,无异于蚍蜉撼树,力量不足时,应隐忍为上,半分也急不得。
新任光禄勋单贺,此时正在他对面品茶。难得春季好雨,难得闲情雅致,又岂容错过?
吕澍见状,不禁微微一笑,请教道:“单兄,你看这文檄……”
单贺淡然道:“雨师来伐,凭公主之力退之足矣。如今远来求援,不过想扩大战果罢了!抑或公主也有吞并雨国之心,故而急迫。大将军该不会为这点点小事而烦恼吧?”
吕澍轻怔,尔后大笑,道:“单兄果然知吾!”当下便把适才所想原原本本讲与他听。
单贺凝神片刻,审慎地道:“大将军不可轻言与天焦对敌之事。其国自明帝卫衡以来,雄踞东陆,且地大物博,兵精甲多,难以相持。今熊国能制恒帝者,马战也。其骑师勇猛、多变化,临阵冲锋,无可抵挡,故恒帝且自沉吟。然而五国会盟,同心协力,熊子败局几定。待恒帝扫灭北方,难保他不会对南境用兵啊。”
吕澍颔首道:“不错,这也正是我所担忧的呀。为今之势,须趁天焦无力南顾之机,结盟示好,才是上策。”
单贺道:“武城公主未奉使命,逃奔昂州,天焦会不会借机向将军要人呢?”
吕澍淡淡一笑道:“恒帝若想如此,早该遣使奉告了。再说,恒帝也非气量狭小之辈,相反,有些地方澍自感并不如他。”
单贺微微一怔,心道你与恒帝自比,不免托大。未敢答言。
吕澍笑道:“单兄,此事还须汝亲往邱都为我去办。”
单贺起身郑重道:“敢不从命!”
懋乡西北广丘。
二月癸酉。
铫文广、帅青等率军滞留此处已有十日。广丘西,是南域仅次于观象山龙岩峰的第二高峰玉清峰,此处山峦众多,雨林遍布,故而是掩遮行藏的最好场所。
林间用硕大的树叶和枝干搭起了一个仅容数人坐卧的简陋小屋,此刻,两位初次率兵征战的将领便在内议事。昂州兵对将军单兴、段授并不陌生,亦很愿听命,然而对帅青这样的文人,却小有抵触,然他不以为意。
此时,帅青指着在地上所画小图,道:“雨军粮秣仅够维持数日,许勇必遣人急报沁泽送粮。我等所在此处,为骑月、平乡之间运输必经之道,想必雨军辎重会在这两日送达。”
雨国在昂州西、伏氏东北,恰似嵌入两邻之中的一片叶子。其平原面积占了国土二分之一强,都城沁泽附近,更是其粮食主要产地和集散地,往年伏氏大灾之年,每每往沁泽请援,而作为附庸国的雨国只能无条件地送粮。
铫文广点点头,忽然又皱起眉,摇了摇头。
帅青知晓其意,道:“雨军围城猛攻,其实早已粮尽;许勇好武恃蛮,未获全胜又怎忍退兵?兵粮未至,军心浮动,若此批粮秣再能为我所截,恐怕他不战也自乱了。”
铫文广眼中闪出笑意,道:“烧!”
帅青忽然脸红了红,没有作声。适才他心中所想,正是希望截敌粮草引为己用,或视雨军援兵速度再作烧粮打算,但此来目标便不能明确,且许勇若果断撤围来战,己军很难有把握全身而退,而铫文广知晓此举在于断粮,其它诸事取舍坚定,表现出稍异于他的军事素质。帅青暗暗为其言所悸,惭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