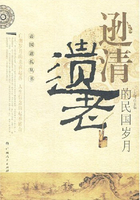袁劲梅(美国)
袁劲梅,女,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现任委员。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有小说集《月过女墙》(工人出版社)。作品曾获中国台湾“联合文学奖新人奖”、“汉新文学奖”、《侨报》五大道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中篇小说《忠臣逆子》入选“《北京文学》2004~2005年度文学作品排行榜”。多篇作品入选中国《2005年最佳中篇小说》《北大年选——2005散文卷》《2005中国年度随笔》《读库0603》《散文精选2006》《散文精选2007》等多种。2009年中篇小说《罗坎村》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1.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薄嘴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
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电子游戏玩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这个当爹的更疼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给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一、每天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写二十遍;二、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晒到中暑为止;三、自己选一条皮带,让老爸打一百鞭子。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选哪条都构成儿童虐待罪!证据二: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算我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过来掉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老邵的“儿童虐待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老邵应该入监下牢三个月;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而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谁都知道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标准: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入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在美国当人,自由与不自由中间的边界是‘法律’。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设计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规范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村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会不会父亲权力太大,儿子没有权力?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罗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严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个联系起来。白墙依照里面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油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群小铁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线一松,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作天经地义。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部”,猪场叫“祠堂后”。“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的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去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叽叽哇哇在村部哭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