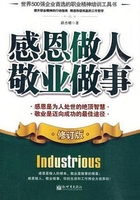顾思晓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沉声道:“是,我是故意的——他活该!”
虽然已经猜到了,可听到顾思晓说这话,顾石头还是倒抽了口冷气,“你为什么这么恨顾福?”
“我——”我是顾思晓啊!是那个你曾经抱过的孩子,是那个被害了的顾家的小娘子……
有些哽咽,可是最终顾思晓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呖了下去。
“我从前在街头乞讨,有个长得很和善的小娘子,常常施舍给我吃的——我还记得,她笑起来很好看,说话也是温温柔柔的,不像别人把我看成小叫花子,恶声恶气的……”
她幽幽地笑着,低声道:“那个小娘子,她姓顾——这里,本来该是她的家的!”
怔怔地看着顾思晓,顾石头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你、你是说小娘子?画儿小娘子?!”有些激动,顾石头的眼角已经湿润了,“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过小娘子,提过扇王顾家……”
抹着眼角,他忽然皱眉,“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该——出了人命可怎么是好?”
“他活该——”咬着牙,顾思晓开始情绪激动。
“师傅,你有没有听说,顾家大官人入葬祖坟的事情?”
顾石头沉默了半晌,才叹道:“自然是听说过的,这座老宅是怎么到了东顾手上的,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呢?”
“那师傅你可知道,当初是谁代表西顾和东顾谈判的?”顾思晓冷笑了一声,“这个顾福吃里扒外,明明是西顾的人,却暗中挑唆,让东顾用祖坟之事胁迫西顾,不仅用一百两银子买了这栋老宅,甚至还让西顾另出了五千两银子……”
合了下眼,她仍是心绪难平,“说那五千两银子,是用作修缮祠堂,可实际上,这银子根本就是落进了东顾的口袋。除此之外,顾福更是中饱私囊,从中捞了不少好处。难道师傅您没听说,顾福比乡下土财主还要有钱吗?不只是在下方桥附近集市有两家铺子,还在邻近的王家村,也有五十亩良田。”
“这钱,顾福是怎么来的?这些年,他在顾家到底捞了多少油水?!这些,不可查也不好查,可是他顾福背主,在背后插刀却是事实!像这样的小人,他不该死谁该死?!”
顾石头默然,这些事他也听说过的,也有没听说过的。
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事,画儿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可是,他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郁闷不平,也能感觉到那滔天的恨意。
这,真的只是因为画儿感念当日小娘子的温善关照吗?
想不明白,但此刻,他望向顾思晓的目光却透出慈爱。
“画儿,小娘子在天之灵,一定很感激你——但,以后不要这样了,恶人自有恶人磨,早晚有一天,他们都会遭报应的……”
点点头,顾思晓没有固执地在老人面前坚持己见。
可在老人转身往屋里走去时,却是低声呢喃:“恶人?我不就是吗——我就是他们的报应……”
顾福不是个好相与的人,睚眦必报,斤斤计较,是绝对的小人。
可那天被顾石头吓跑之后,居然没有再借机报复,反倒厨房那边不再克扣吃食了。
“这小子,大概是等着看我哪天得罪了官人,好直接下刀子捅我呢!”
顾石头玩笑,却并不在意。
那天他说的也不是假话,给顾永送过两把白纸扇后,顾永倒真是让他开始制扇供他把玩了。
因为这个,顾思晓能够看的,学的就更多了。
虽然还没亲自动手制作,可是光是看,已经让她受益非浅。
空闲时,她从后书房里偷了笔墨,在白纸扇上画扇面。
这个,她早前是画惯了的,只是现在手没有前世那么稳,虽还记着感觉,可到底手是生疏的。
再一个,后书房里找不到其他颜料,她练手也只能单一味墨色。
头一个扇面,她画得自信满满,可第一笔描下,就知道破了功。
手颤笔抖,一张墨荷图画得满是黑圈圈,布图虽然不错,可是这画功却实在太差。
她自叹自怨,顾石头却是在后捋着白须,有些奇怪地问:“你之前画过扇面?嗯,这布图和用笔不错,还真有几分我家主人的风骨,可惜,手太生了——还得好好练啊!”
这个不用师傅说,只有苦练才能回复从前的力道。
笔墨偷用后过洗干净可以再放回书房,可纸却是有数的。
顾思晓也就不用纸,还照从前的法子,用树枝在地上划。
不只是这样,还学着从前兄长练笔时的方法,手腕悬空,笔吊重坠,以练习笔力。
这样子练,常常一练就是小半天。
因为顾永近来几乎没有回过后书房,小院里也没有什么事。
倒是彩衣,在养伤期间仍是惦记着买药的事,常常追问顾思晓,却总是被敷衍过去。
顾思晓心里其实也没底,孙天仓再能干,可到底只是个少年,去买春药这种东西,还是挺为难吧?
不过还好这些天,她一直关注的那两人看来进展顺利,说不定没有她的药助兴,也能成就好事。
顾家虽然人也不算少,可是那种事儿,却是不好瞒人的。
这些日子,绿萝想方设法的讨好顾福,早就有明眼人看在眼里。
渐渐的,宅里也就有了些风言风语。
别说下头的小丫头,就是许妈妈也都曾玩笑似地说过“这都眼看着快深秋了,怎么反倒像到了春天似的呢?”
这自然是暗指园中春情泛滥,说的就是绿萝。
其实,照按常理,听到这种事,许妈妈第一要做的就该是和娘子汇报,然后立刻捉了犯事的丫头仆人,或是施家法或是直接发卖了事,总之是不能纵容的。
可是这一次,许妈妈却没急着有所动作,反倒还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让这小道消息越传越广。
后宅里人人都在说,春花自然不可能听不到。
起先,还是只说是后宅里有丫头勾搭前院的仆人,也没点明是谁,春花还跟着好奇地问了两句。
可渐渐的,这话就越传越不是味儿,先是有人说,那个前院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仆人,而是顾福福管家。
也是,要是寻常仆人,哪儿有机会进后宅来呢?
头一回听到,春花当场就愣住,站在那儿愣是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那说小话的仆妇一扭头,看见春花也是满脸尴尬,挥着手招呼着同伴,慌慌张张地走开。
虽然没有聘书,也没定亲,可顾家里,没有人不知道春花要嫁给福管家的事儿。
“你们给我站住!”厉喝了一声,春花醒过神来,先是拦住那个说小话的仆妇。
“谁让你满嘴胡说八道,编排福管家的?说!你说的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被她一吼,那仆妇也是有些慌,眼珠乱转,闪烁其词,半天也说不上来。
春花见状,更觉这是有人恶意传出来的谣言,“不要脸的东西!舌头长长了就剪下去!当这家里,谁都是你可以胡乱编造的吗?”
她骂得太狠,那仆妇也恼了,一把推开逼近的春花,“靠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有口臭啊?!我说春花,你是娘子院里的丫头,可是丫头也只是丫头,又不是管事娘子,还真当自己是公主娘娘,谁都管得着了呢!”
挺了挺胸,她冷哼道:“我告诉你,刚才那话可不是我胡乱编造的!那,可是有人亲眼看到的。说是福管家,和那丫头两人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搂搂抱抱的,还嘴对嘴的——唉哟,那样丑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用手扇着风,睨着气得脸发青的春花,她哼哼道:“说实在的,我也是同情你才不全说出来的——不过呢,你啊,也别太生气了。再怎么说你也还没嫁给福管家呢!就算是真嫁了,这男人还不都一样,偷腥这种事免不了的,忍忍也就过去了……”
“你,你——我撕了你这张臭嘴!”春花气得发晕,扑上来撕扯,却哪里打得过专做粗活的仆妇。
又有旁边的拉偏架,不过几下,就被人分开,没落到好处,反倒头发也散了、妆也花了。
恨恨地推开拉她的仆妇,春花捋了捋头发,转身就往前院跑。
可跑到半路上,她又清醒过来。
去质问顾福?!问他为什么变心,为什么又勾搭别的丫头?
她是该这样问的,可是要是把顾福问急了,和她翻脸又怎么办?
其实,刚一听人说时,她已经信了大半。当初,顾福可不就是这么勾搭上她的?
这男人,的确是爱新鲜,总是勾搭一个又一个。
要是从前,她一准闹翻,请娘子、小娘子为她做主。
可是现在,换了一家,别说她现在根本就没得到娘子的信任重用,就是她能站稳脚,也都是靠的顾福。
要是这时候闹翻了,她可怎么办?!
就不说还能不能成管家娘子,就只说她如今连身子都是他的了,以后她可怎么嫁人?!
缓下脚步,春花收了找顾福算帐的心思,转了身又慢慢往回走。
且不去找顾福,就真有其事,她要收拾的也该是那个狐媚勾人的贱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