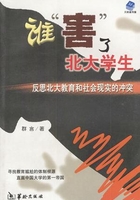一星期过去了,罗切斯特先生音讯全无。十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要是他从里斯直接上伦敦,再从那儿去欧洲大陆,哪怕今后一年不在桑菲尔德再次露面,她也不会感到意外。原先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这样出人意料地不辞而别。一听这话,我就莫名其妙地感到浑身发凉,心直往下沉。我竟然还任由自己去体味了这种令人难受的失望心情,不过我竭力恢复了理智,重又记起了我的原则,很快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说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怎么能那么快就调整了这一时的忘乎所以,并消除了这种错误的想法——把罗切斯特先生的行踪看成我有理由十分关心的事!我并没有低声下气,怀着奴性十足的自卑感来贬低自己,相反,我只是说:
“你和桑菲尔德的主人之间,除了教他的被保护对象,接受他付给你的薪水,感谢他因为你尽职尽责而理所当然地对你的尊重和厚待外,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明白,这是他所认真承认的你和他之间的唯一关系,所以,别把他当做你抛洒柔情、喜悦、痛苦等的对象。他和你不是同一阶层的人,你还是待在你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吧。你要自重自爱,别把你全身心灌注的爱,虚抛在不需要甚至轻视这份厚礼的地方。”
我继续平平静静地干我每天的工作,可是脑子里时不时地闪过模糊的暗示,提出一些为什么我要离开桑菲尔德的理由。我还常常不由自主地草拟出广告,并对未来的新职位作种种猜想。我觉得没有必要阻止这类念头,要是它们能开花结果,就让它们去开花结果吧。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两个多星期后,邮局给费尔法克斯太太送来了一封信。
“是主人写来的,”她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说,“我想,现在我们就能知道是否要等候他回来了。”
我则继续喝着我的咖啡(我们正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自己脸上突然升起的火热通红归因于它。至于我的手为什么会发抖,为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把杯里的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则干脆不去想它了。
“喔,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太清静了。可是现在我们却有机会要大忙了,至少得忙上一阵子。”费尔法克斯太太说着,仍然把信纸举在眼镜前面。
在我允许自己请她解释以前,我给阿黛勒系好了碰巧松开的围裙带子,然后帮她又拿了一只面包,给她的杯子里倒满牛奶,接着我才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很快就回来吧?”
“可事实是,他很快就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就回来,那就是说在这个星期四,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来。我不知道里斯有多少绅士淑女和他一起来。他来信吩咐把所有最好的卧室都收拾好,书房和休憩室也都要打扫干净。还要我到米尔科特的乔治旅馆,和我所能找的任何别的地方,多找一些厨房帮工来。太太小姐们还会带来她们的使女,先生们也会带来他们的听差,所以我们会有满满的一屋子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连吞带咽地急匆匆地吃完早饭,就匆匆离开,着手办事去了。
这三天里,正如她所说的,确实忙得够呛。我原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间都收拾得整洁漂亮,可是看来我的想法错了。找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把油漆的家具器物等又是擦,又是刷,又是洗的,拍干净地毯,把画取下又挂上,擦亮镜子和烛台,在卧室里生了火,在炉边烘了被单和羽绒床垫,像这样的架势,我在以前和以后都没看见过。阿黛尔在这几天里简直变野了。为客人作准备,等待客人来临,使她高兴得几乎快要发疯了。她要索菲娅把她叫做“服装”原文为法语。如无特殊说明,本章楷体内容原文为法语。的所有外衣都检查一遍,把“过时”的都翻翻新,把新的也都晒一晒,准备停当。至于她自己,却什么也不干,只顾在前面那排房间里蹦进蹦出,在床上跳上跳下,又在烧得烟囱里轰隆隆直响的炉火跟前,躺在床垫上或者堆得高高的大小枕头上。她的功课都免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把我也拉去听她调遣,我整天待在贮藏室里,给她和厨子帮忙(或者帮倒忙),学着做蛋奶糕、奶酪饼和法国点心,捆扎野味翅膀和装点甜食碟子。
客人预定星期四下午到达,正好赶上六点钟的晚餐。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我相信自己像任何人一样活跃和欢乐——除了阿黛尔。然而,我的欢快心情仍会时不时地像给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似的冷却下来,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到疑惧、凶险和种种不祥的猜测中去。当我看到上三楼的楼梯门(最近它一直是锁着的)慢慢打开,头戴整洁的帽子,围着白围裙,系着手绢的格雷斯·普尔的身影从那儿出来的时候;当我眼看她穿着布条拖鞋、无声无息地悄悄经过走廊的时候;当我看见她朝忙乱不堪的卧室里探头望望——也许只是告诉打杂女工该怎样擦亮炉栅,或者怎样擦干净大理石炉台,或者怎样从糊有墙纸的墙上拭去污迹——然后又继续往前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这样想。普尔太大就是这样每天下楼来到厨房去一次,去吃饭,在炉边适量地抽上一斗烟,然后提着一壶聊以自慰的黑啤酒回去,重又回到楼上她那个昏暗的窝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个小时是跟楼下的那些仆人伙伴们待在一起的。其余时间,她都在二楼的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橡木板壁的小房间里,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也许还会独自阴惨惨地笑上几声——就像个关在地牢里的囚犯那样孤单寂寞。
最奇怪的是,整个房子里,除了我没有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的怪癖,或者对她的行为感到惊异。没有人谈到她的身份和职务,也没有人同情她的孤单和寂寞。说真的,有一次我倒听到过一点儿莉亚和一个打杂女工的闲谈,话题就是格雷斯。莉亚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只听那打杂女工说:
“我想她拿的工钱挺多吧?”
“是啊,”莉亚说,“但愿我也能拿到那么多工钱。倒不是说对我自己拿的工钱有什么可抱怨的——桑菲尔德从来不小里小气的——可是我的工钱还不到普尔太太拿的五分之一。她正在攒钱呢,每个季度她都要去一趟米尔科特的银行。她要是想要辞工不干的话,她也已经有了足够的钱,尽可以养活自己了,这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不过我猜想她在这儿已经惯了。再说她还不到四十岁,又强壮,又能干,对她来说,放弃工作未免太早了。”
“我想她准定是一把好手吧。”打杂女工说。
“嗯!——她明白自己该干些什么——这一点谁也比不上她。”莉亚意味深长地说,“再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她那份差使的,哪怕付给她拿的那么多工钱也不行。”
“确实干不了!”对方回答说,“不知道主人是不是……”
打杂女工正要往下说,可是莉亚正好回头瞧见了我,马上用胳臂肘轻轻捅了她的伙伴一下。
“她还不知道?”我听到那女人小声问。
莉亚摇摇头,这场谈话自然就这么结束了。我从中所能听出的只是——桑菲尔德有一个谜,而我被故意排斥在这个谜之外。
星期四到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天晚上干完。地毯铺好了,帐子结了彩,白得耀眼的床罩铺在床上了,梳妆台已收拾停当,家具擦拭过了,花瓶里插上了鲜花,所有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手所能,收拾得焕然一新。大厅也擦洗了一番。那座雕花大钟,还有楼梯的踏级和栏杆,都擦得像镜面一样光亮。餐厅里,餐具柜中摆着闪闪发光的餐具,大小客厅里,四周摆满了一瓶瓶盛开的外国鲜花。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子裙服,戴上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迎接客人——引太太小姐们上她们各自的房间,等等。阿黛尔也要打扮起来,虽然我觉得,至少那天她没有机会被介绍给客人。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一件宽摆的薄纱短外衣。至于我自己,就没有必要换什么衣服了,不会有人来叫我离开那间作为我的私室的教室的。教室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私室——“烦恼时刻的一个非常愉快的隐蔽所”。
那是一个温暖、宁静的春日,就是三月末四月初,作为夏日先驱来到大地的晴朗日子,现在,白天即将过去,不过黄昏时分也还是暖融融的。我坐在敞开窗户的教室里工作着。
“天色晚了,”费尔法克斯太太走进来说,身上的缎子裙服窸窣作响,“幸好我吩咐的开饭时间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晚了一小时。现在都过六点了。我已经打发约翰到大门口看看大路上有没有什么动静,从那儿朝米尔科特方向看可以看到很远。”她走到窗户跟前。“他来了!”她说。“喂,约翰!”她探出窗外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他们来啦,太太,”对方答道,“再过十分钟就到。”
阿黛尔飞也似的奔向窗口,我也跟了过去,小心地站在一边,这样可以让窗帘挡着我,我可以看见他们,而他们看不见我。
约翰说的十分钟似乎特别长,不过最后终于听到了车轮声。四个骑马的人沿着车道奔驰而来,后面跟着两辆敞篷马车,一眼望去,车上尽是飘拂的面纱和摆动的羽毛。骑马的人中,有两位是衣着时髦的年轻绅士,第三位是罗切斯特先生,骑在他的黑马美罗上,派洛特跳跃着跑在他前面。他旁边是一位骑马的小姐,他们两人在这队人马的最前面。她那身紫色的骑马装长得几乎拖到地面上,她那面纱在微风中拖得长长的,飘舞着,和面纱透明的皱褶贴在一起的,是一头乌黑闪亮的浓密卷发。
“英格拉姆小姐!”费尔法克斯太太嚷了一声,接着便急忙下楼执行自己的任务去了。
这队人马顺着车道的弯势,迅速转过屋角,我也就看不见他们了。这时阿黛尔吵着要下楼去,可是我把她抱到膝头上,告诉她,除非特地派人来叫她下去,否则,不管是现在还是别的时候,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冒冒失失地出现在那些太太小姐们面前,要不,罗切斯特先生准会非常生气的,等等。听了这些话,“她自然地流下了眼泪”此处作者有意模仿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描写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时的诗句。。但看到我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她也就终于同意把眼泪擦掉了。
这时,可以听到大厅里传来愉快的喧哗声。先生们低沉的嗓音和女士们银铃般的音调和谐地交织成一片。在这一切之上,可以听到桑菲尔德府主人那虽不太响却很洪亮的声音,他在欢迎他的美丽的和英俊的客人们到他家来。接着,轻盈的脚步声登上楼梯,快捷的步履穿过走廊,还有温柔的欢笑声,开门和关门声,接着是一阵寂静。
“她们在换衣服了。”阿黛尔说。她一直留心倾听着,不放过一点儿动静,接着还叹了口气。“跟妈妈在一起时,”她说,“有客人来我总是到处跟着,到客厅里,到她们房里。我常常看着使女给那些太太小姐们梳头,穿衣服,挺有意思的。像这样看看多好啊。”
“你饿不饿,阿黛尔?”
“饿的,小姐,我们有五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好吧,趁这会儿太太小姐们都在自己房里,我冒个险下楼,去给你拿点吃的来。”
我小心翼翼地从我的隐蔽处出来,找了一道直通厨房的后楼梯下去。厨房里炉火通红,到处乱哄哄的。汤和鱼已经快做好了,厨子弯着腰在锅上忙着,全身心都紧张得像要燃烧起来似的。在仆役间里,两个马车夫和三个绅士的随从围着炉火或站着或坐着。
我想,那些贴身侍女此时都在楼上,和她们的女主人在一起。从米尔科特雇来的几个新仆人正里里外外地忙个不停。穿过这一片混乱,我终于走到了放食品的地方。我在那里拿了一只冷鸡、一个圆面包、几块馅饼、一两只盘子和一副刀叉。我拿到这些战利品就匆匆撤了回来。回到走廊里,我刚关上我身后的后楼梯门,就听到一阵越来越响的嗡嗡声,这是在警告我,那班太太小姐们就要从她们的房间出来了。我若不经过她们的房间,不冒一下拿着食物被她们撞见的危险,我是没法回到教室的。于是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这一头,这儿没有窗户,光线很暗,现在天已经很黑了,因为太阳已经下山,暮色变得愈来愈浓。
不一会儿,房间里就一个接一个地走出美丽的客人。走出来的每一个都显得欢快轻松,全身的穿戴在昏暗中闪闪发光。她们在走廊的那一头聚在一起站立了片刻,用活泼可爱的声音轻声交谈着。接着她们全都走下楼梯,轻盈无声,就像一团明亮的雾沿着小山滚动下去似的。她们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高贵和优雅的,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我发现阿黛尔抓住微开的教室门,从门缝里偷偷张望着。“多漂亮的太太小姐啊!”她用英语嚷嚷道,“哦,我多想上她们那儿去啊!你看晚饭后罗切斯特先生会叫我们去吗?”
“不会,真的,我看不会。罗切斯特先生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今天晚上你就别想那些太太小姐了,也许明天你就能见到她们。给,这是你的晚饭。”
她真的饿坏了,鸡和馅饼暂时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幸好我弄到了这点吃的,要不然,她、我,还有索菲娅根本就吃不上晚饭,我把我们的食物也分给了索菲娅一份。楼下的人都太忙,想不到我们。甜食到九点过后才端上来。十点钟,仆人们还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跑来跑去。我允许阿黛尔比平时晚得多的时候再睡。因为她说,楼下门老是开啊关的,人们又在跑来奔去的,她睡不着。此外,她还补充说,说不定等她脱去衣服,也许罗切斯特先生又派人叫她来了,“那该多可惜啊!”
我给她讲故事,她愿听多久我就讲多久。然后,我又带她到走廊里换换环境。这时,大厅里亮着灯,她喜欢伏在栏杆上看下面的仆人们走来走去。夜深了,已经移了一架钢琴到里面的客厅里传来了音乐声,阿黛尔和我在楼梯最高的一级上坐下来听着。不一会儿,有歌声和着悠扬的琴声响了起来,唱歌的是一位小姐,她的歌声非常悦耳动人。独唱过后是二重唱,接着是无伴奏合唱;中间间歇时,则传来一片嗡嗡的愉快的谈话声。我听了很久,突然,发现我的耳朵在全神贯注地分辨那嘈杂的声音,想从这混杂的声音中找出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当我的耳朵很快就捕捉到它时,又想进一步从那因离得远而听不清的语调中,猜出他说的话语来。
钟敲了十一点,我看看阿黛尔,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皮也愈来愈沉重了,因此我把她抱在怀里,送她上了床。等那些先生女士们回自己的房间就寝时,已经将近一点了。
第二天的天气跟第一天一样好。这一天他们到附近一个什么地方去游览。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有几个人骑马,其余的都坐马车。我目睹他们离开,后来又目睹他们回来。英格拉姆小姐跟先前一样,是唯一骑马的女人。也跟先前一样,罗切斯特先生还是在她身旁奔驰着。这两个人骑着马,跟其余的人略微拉开一段距离。费尔法克斯太太这时正和我一起站在窗前,我把这情景指给她看。
“你说他们不大可能想到结婚,”我说,“可是你瞧,和别的女士相比,罗切斯特先生明明更喜欢她。”
“是啊,我想是的,毫无疑问他是爱慕她的。”
“她也一样爱慕他。”我补充说,“瞧,她那样他侧过头去的样子,就像在说知心话似的。但愿我能看清她的脸,我还没看过她一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