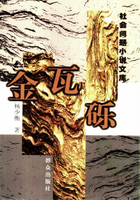坏年景总不是单独来的。艾萨克已经变得有耐心了,逆来顺受。谷物焦干了,干草又收成不好,但马铃薯看起来似乎又能过关——一切都很坏,但还不是坏到不能再坏。艾萨克还有一季的木柴和材料可以到村里去卖,全岸的鲱鱼收获量都大,因此有足够的钱买木头。其实,谷物收成得坏几乎可说是天意——否则他既没有仓库也没有打谷场,怎么打呢?说它是天意呢,有时候这样说没什么不好。
有些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从心里扫掉。那年夏天那个拉普人对英格说的又是什么呢——有什么东西还没有买下来?凭什么买?地就在那里,树林也在那里;他开了、耕了,在自然的茂野里建立了一个家,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挣饭吃,不向任何人求任何东西,却只是独自的做,做,做。每次他到村子里,都想亲自去问问蓝斯曼德这件事,但又总是拖下去;那蓝斯曼德不是好说话的人,他们说,而艾萨克又不是会多说话的人。如果他去,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来是为的什么?
那年冬季,有一天蓝斯曼德自己赶车上了他的山坡。跟他来的还有另一个人,袋子里装了一大叠纸。是盖斯乐本人,即那蓝斯曼德,一点也不假。他看着那宽敞的山坡,开平了树林,光滑的封在冰雪下的田野;或许他以为这些全是耕过了的田,因为他说:
“怎么呢,你有了一整片大农场啊。你总不至于想要平白得这一切吧?”
果然!艾萨克吓得慌了,一句话也没说。
“你总该先到我那里来一下,把地买下来,”盖斯乐说。
“哎。”
那蓝斯曼德说起了估价,边界,税,给国家的税,当他解释了一些之后,艾萨克开始明白这里面毕竟有些道理。蓝斯曼德揶揄地转向他的同伴说,“好啦,你说你是个测量员,这里的已耕地有多大呢?”他并不等那人回答,就靠他的猜测写了下来。然后他问艾萨克的谷子如何,干草收了多少,马铃薯多少蒲式耳。然后再问到边界。在雪深及腰的状况下,他们不可能亲自到边界去一趟。森林和草地的面积,艾萨克自己究竟认为有多大呢?艾萨克根本没有概念,他一向就以为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都是他的地方。蓝斯曼德说政府要求确定的边界。“地方越大,你出的钱就越多。”
“哎。”
“他们也不会把你认为自己吞得下的都给你;他们会让你得到合你需要的地方。”
“哎。”
英格给客人们拿进来一些羊奶;他们喝了,她又拿进来一些。那蓝斯曼德是不好讲话的人吗?他摸摸艾利修斯的头发,看看那孩子玩的东西。“玩石头,是什么?让我看看。嗯,很重。像是什么矿石。”
“山里这种东西很多。”艾萨克说。
蓝斯曼德又回到本题。“从这里向西向南,你最多要多少?我们可以说向南两弗隆吗?”
“两弗隆!”他的助手喊道。
“‘你’连两百码也不开了。”他的上司短短地说。
“那得多少钱呢?”艾萨克问。
“说不确定。要看了。但我在报告上会尽量报低。这里毕竟跟哪里都离得远,不容易到。”
“可是两弗隆!”助手又说。
蓝斯曼德正式地说了一遍,向南,两弗隆,然后问:“山那边呢?这个方向你要多少?”
“我需要一直到人边的地。那边有一条不小的河。”艾萨克说。
蓝斯曼德这一点也记了下来。“向北呢?”
“怎么呢,向那一边没多大关系,大部分是沼泽,只有一点树。”
蓝斯曼德向北定了一弗隆。“东呢?”
“也没多大关系。从这里一直到瑞典,都是秃地。”
蓝斯曼德又记了下来。他迅速地计算了一下之后说:“就算这样,也是很大一块地了。如果离村子较近,不管是哪里,当然都得一大笔钱,没有人会买。我会送一份报告上去,说一百元是个公道的价钱。你看呢?”他问他的助手。
“等于是送的。”那个说。
“一百元?”英格说。“艾萨克,你根本用不着这么大块地。”
“用——不着。”艾萨克说。
那助手赶快接嘴:“我正是这么说。比你需要的多得太多了。你要它来有什么用呢?”
“耕吧。”蓝斯曼德说。
他在那里坐着写,脑子里斟酌着,已经很久了,孩子们不时哭闹;他不想再跑一趟。结果,他必得夜里很晚才能到家,甚至要天亮才行。他把纸张塞进袋子,这表示事情定了。
“套马。”他对助手说。然后转向艾萨克,“事实上,他们应该把地送给你,一文不要,而且还得给你钱,因为你那么努力地工作了。当我送报告的时候,我会尽可能说几句话。然后我们就等着看政府为了地契要多少钱了。”
艾萨克——真难说他的感觉如何。一半原因是他的地在他辛勤耕作了那么久之后,值那么多钱。至于那一百元,无疑的,总有一天他可以还清。他不必再为这个烦恼了;他可以像以前一样工作了。艾萨克不是为将来的事焦急的人,他做就是。
英格谢了蓝斯曼德,盼望向政府报告的时候帮他们说话。
“当然当然。不过我说的并不是自己的意见。我只说我看到的和认为应当的。最小的这个多大了?”
“快八个月了。”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那蓝斯曼德并不是不讲理的人,只是有点肤浅,不十分认真。他不把他的助手布列德·奥尔逊放在眼里,但这个人由于职责所在,在这方面应当是个专家了,但蓝斯曼德却随手靠猜测定了下来。然而对艾萨克和他太太来说,这件事却严重得很——哎,对他们以后的人,或许好几代,都是严重的。但他却随手定下来,随他的喜欢,就在当地立了文件。尽管如此,他却是慈和的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亮亮的硬币,给了小西维特;然后向其他的人点点头,出门走向雪橇。
他突然问道:“你管这地方叫什么?”
“叫什么?”
“对。它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必得给它一个名字。”
没有人想到过这件事。英格和艾萨克你看我我看你。
“塞兰拉?”蓝斯曼德说。他一定是全凭他一时高兴发明出来的;可能这根本就不是名字。但他只是点点头,又说了一遍:“塞兰拉!”就赶着雪橇走了。
又是凭空想定下来的。什么都可以这样定下来,名字、价钱、边界……
几个星期以后,当艾萨克在村子里的时候,听到关于蓝斯曼德盖斯乐的传言。有些人他报不出账来,被调查了,报到了他上司那里。当然,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有些人可以一辈子跌跌撞撞,以此自足,可是有一天他们碰到了走路稳稳当当的人,就不一样了。
后来,有一天,艾萨克运了一车木头下去,回来了,雪橇上除了蓝斯曼德盖斯乐还有谁呢?半路上,他从树林里出来,挥手,只说:“载我,行吗?”
他们坐在雪橇上走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那乘客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喝了一口。又给艾萨克,后者拒绝。“我怕这段路会让我反胃。”那蓝斯曼德说。
他马上说起艾萨克的土地的事。“我立刻把报告送上去,全力推介。塞兰拉是个好名字。事实上,他们应该什么代价都不要,让你得到这块地,当然,话又不能这么说出去。如果我说了,只会引得他们生气,自己订上价钱。我建议五十元。”
“噢,五十,你说?不是一百?”
那蓝斯曼德皱拢眉头,想了想。“就我记得的,是五十。对……”
“那你现在要去?”艾萨克问。
“过去,到维斯特波顿,我太太家人那边。”
“这种季节到那边不好走?”
“我会想办法。你能够送我一程吗?”
“哎,你不能独个儿去。”
他们来到农场,那蓝斯曼德在那里过夜,睡在小屋里。早晨,他又把小酒瓶掏出来,说:“我保证这一程一定会让我反胃。”至于其他,他和上次一样,慈善,有决心,但肤浅,不大关心自己的事。他这样,或许毕竟没什么不好,艾萨克冒险地说,山坡其实并没有全耕,只是这里那里开了一小块而已。那蓝斯曼德的态度倒十分奇异。“当然,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就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布列德,跟我来的那个家伙,他不知道。他没有地产。他们完全是靠纸上作业的。由于我登记了那么大片土地,又只有那么几捆干草,那么几蒲式耳的马铃薯,他们立刻就会说那一定是瘠土,便宜地,你懂吧。我为你已经尽了力,你可以借我的话,这把戏会成功。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二十三万统统像你这样的人。”
那蓝斯曼德点点头,转向英格。“你最小的多大了?”
“刚刚八个月。”
“男孩,是吗?”
“是。”
“但是你一定要尽早把这件事办妥,”他又对艾萨克说。“现在又另有一个人想买地了,在这里和村子之间,当他买了之后,这里马上会涨价,你现在买,先把这块地弄到手,再等着它涨价——这里,你就可以得到一点你辛苦劳累的报酬。毕竟是你先来开垦这里的。原来这里全是野地。”
他们感谢他的劝告,并问是不是他本人在处理这件事。他说他能做的都已做了,现在什么都要看政府的决定了。现在我要过去,到维斯特波顿,我不会回来了。”他没有隐瞒地告诉他们。
他给了英格一小块肉,但这已太多了。“下次你们杀东西的时候,拿一点给村子里我的家人,”他说。“我太太会付你们钱。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乳酪,也带去一些。孩子们喜欢吃。”
艾萨克陪他过山;在高处比在低处好走得多了。他给了艾萨克整整一元钱。
蓝斯曼德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个地方,没有再回来。人们说,这并不是什么大损失,因为他被人看做是可疑的人,一个冒险家。并不是他没知识,他是个有学问的人,研究过这个和那个,但是他过得没有分寸,别人的钱。后者透露出,他是在他的上司、安提曼德普勒姆严词责备之后离开的,但对他的家庭并没有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他们在那里又住了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那笔账目不明的钱不久也就从瑞典送了回来,因此不能说盖斯乐的妻儿是当人质的,他们留着,只因为他们喜欢。
艾萨克和英格绝无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盖斯乐的。至于他的继承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就谁也不知道了——说不定他们要把事情整个重新来一遍呢!
安提曼德把一个职员派到村里,当新的蓝斯曼德。他大约四十岁,地方法官的儿子,姓海耶达。他没有钱上大学,就进了公家机关服务;他拘拘束束地在一个办公室里坐下去,趴在桌子上写文件,整整十五年了。他没有结婚,因为一直养不起太太。他的上司安提曼德普勒姆从前任的郡守把他继承下来,照以前那样给他那点可怜的薪俸;海耶达收下来,照旧趴在桌子上写文件。
艾萨克鼓起勇气,去见他。
“塞兰拉的文件……?在这里,刚刚从部里回来。他们什么都要知道得清清楚楚——整个事情从头到尾都乱七八糟,盖斯乐留下来的就是这个状况。”那当官的说。“部里希望报告农场里有没有出产可供市场买卖的果类。有没有大木材。邻近的山里有没有值钱的矿石或金属。文件里提到了水,但没有说有没有渔获量。这个盖斯乐看起来好像提供了一些资料,但是他不可靠,我必须完全重新整理一遍。我不得不找个时间走一遭,到塞兰拉彻底察看察看,做个估价。到那里去有多少里?部里,当然要求边界划得清清楚楚。对的,我们要把边界打好。”
“这种季节打边界,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艾萨克说,“要在夏天来过一段时间才行。”
“不管怎么样吧,总得做。部里不能等到夏天过了才有回答。我一有空就会亲自去一趟。反正我非走一番不行的,还有另一块地有个人要呢。”
“是要买我跟村子之间的地那个人吗?”
“还说不确定。八成。其实,是这里办公室的,我办公室的助手。盖斯乐的时候他就在。他向盖斯乐要求过,我知道,但盖斯乐推拖,说他连一百码的地也耕不了。所以他向郡守呈了一个申请书,我受命负责处理。又是盖斯乐留下的烂账!”
蓝斯曼德海耶达来到农场,也带了他的助手布列德来。在涉过沼泽的时候,他们弄得湿透了,在融雪中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沿着边界察看,更是在未完之前湿得更透。第一天,那蓝斯曼德工作得非常热心,但第二天他够了,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地站着,喊着,指着方向。再也不说勘察“邻近山丘”的矿藏了,至于可供市场买卖的果实——他们会在叫程的路上看看沼泽区的,他说。
部里要求许多方面的资料——当然,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表格要填的。惟一似乎合理的是木材的问题。不错,有些大木材,而且也是在艾萨克预定想要的地区之内,但并没有多到可以买卖的程度;只不过够保持那块地的水土的程度。就算木材不少吧,但谁又能把它们运到很多里之外可以卖的地方去呢?只有艾萨克,在冬天,像个轮子一样滚动着,把少数几根大木材运到村里,换回厚木板和薄木板来盖房子。
那让人想不通的盖斯乐,看来似乎是送了一份难于推翻的报告。现在,他的继任者在把事情整个重新弄一遍,想找碴子,找显眼的错误——却白费工夫。显然他处处都询问过他的助手,留意了他的意见——而这都全不像盖斯乐一向办事的办法。再说,这个助手可能也变了主意,因为他现在自己想从国家的手上购买这块公有地了。
“价钱怎么样?”那蓝斯曼德问。
“五十元是最高的价钱了,再高就不公道。”那专家说。
蓝斯曼德海耶达用优美的词藻加在报告上。盖斯乐是这样写的:“这个人也必须每年付地价税:为了这块地,他只出得起五十元;用十年分期摊付。政府可以接受他的缴纳,也可以把地和他工作的成果一起取走。”海耶达写道:“他现在谦恭地请求向政府申求如下;允许他保留这块地——在这上面,虽然他没有任何所有权,到现在为止却已经做了相当有效的改善——代价是五十元硬币,以同上建议的期限,分期摊还政府。”
蓝斯曼德海耶达答应尽力而为。“我希望能够为你争取到这块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