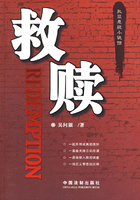艾萨克在降霜以前一直在田里工作,有石头和树根需要掘起、清除,草要割平,以备来年。当土地冻硬,他就放下田里的工作,变成一个伐木人,砍倒大批的树。
“你要这些树做什么呢?”英格会问。
“噢,有一天会有用。”艾萨克当做不在意地说,就像他什么计划都没有似的。但他有计划,不用怕。这里是从未开垦过的森林,长得很密,一直贴近到房门口。挡住了他的田,而他需要空地。再说,冬天也要运一些木头到村里;村里人多,有不少需要柴烧。这绝无问题,艾萨克毫不怀疑。他在树林里不断地工作,砍树,把它们弄成一段一段的。
英格常常过来看他工作。他装作没看到,装作她出来看他不算一回事,一点也没说他希望她这样;但她还是知道他喜欢她在这里。有时候,他们也有奇怪的说话方式。
“你除了跑出来冻得僵僵的没有别的事做吗?”艾萨克问。
“我好得很,”英格说。“可是我不明白你这样把自己累得死去活来的有什么道理。”
“噢!你给我马上把我那件外套穿上。”
“穿你的外套?好得很,真是。我没时间坐在这里了,金犄角要生小牛了,还有别的一大堆事。”
“嗯?生小牛,你说?”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可是小牛你看怎么办呢?让它留着,断奶就好了么?”
“你看着办好了,生小牛这种事不是我的事。”
“好么,把小牛杀来吃了,我觉得很可怜。只留一只母牛在我们这里了。”
“我恐怕也不会喜欢让你这么做。”艾萨克说。
这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孤单的人们,看起来不好看,长得太壮,可是彼此都是对方的福祉,也是家畜的,也是土地的。
金犄角生了。在这荒野之地,是个大日子,是喜悦,是欢乐。他们给它用面粉涂擦,而艾萨克,虽然一路都把面粉扛在肩上,却注意不沾在身上。一只可爱的、漂亮的小牛躺在那里了,红肋腹,像她妈妈一样,可笑的、可喜的因为来到世界上这个奇迹而睁着困惑的眼睛。两年之内,她就会像她母亲一样,自己可以生小牛了。
“她长大了会是一只非常好的母牛,”英格说,“那么,我们管她叫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英格有她特别的像小孩子的地方,怎么也说不上是伶俐。
“叫什么?”艾萨克说。“那怎么办呢,当然叫银犄角了,还能有别的喽?”
初雪降下来了。一有可通的路,艾萨克就出发到村子,还是像一向那样,当英格问他去做什么,他就神秘兮兮的,把个嘴封着。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他回来带来全新的、想也想不到的东西。一匹马,一个雪橇。
“这就是傻劲,”英格说,“偷的,我猜?”
“偷的?”
“那怎么样,捡的?”
啊,如果他能说:“这是我的——我们的马……”是多么好啊。但说真的,他毕竟只是租来的。租来的马和雪橇,用来运他的木头。
艾萨克载着他的木柴下去,带回食物、鲱鱼和面粉。有一天,他在雪橇上带回一只小公牛来,这是他几乎没花什么钱买来的,因为村子里缺饲料,养不起了。毛粗,又瘦,一点说不上漂亮,但架子很结实,只要好好喂一段时候,就会又肥又壮。加上原先的母牛,他们已经……
“下次你又要带什么来呢?”英格说。
艾萨克带回大堆的东西。他用木材换来的原木板和一把锯子,一盘磨,一块铁板锅,还有工具——都是用他的木头换来的。英格暴富了,每次都说:“什么,又有东西?我们已经有了牛和能想到的都有了的时候?”
他们的东西已经足可应付将来一段短时期了,算是小康人家了。明年春天艾萨克又会弄些什么呢?他已经统统想过了,冬天要运更多的木头下去,在上坡上开更多的田,砍更多的树,整个夏天让它们干燥,当下一个冬天,适合雪橇的时候,就运下去。进行得顺顺畅畅。
但另有一件事是艾萨克不晓得想过多少遍的:那金犄角,它究竟是哪里来的,原先是谁的?世界上再找不到像英格这样的妻子了。嗬!野性,任他要她怎样,而且喜欢任他摆布。可是——设想有一天他们来了,要牛,带走了——更糟的是,如果还有更坏的呢?关于那马,英格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偷来的,我猜,还是捡的?”就是,这是她第一个念头。这是她说过的话;谁能说她可以靠得住呢——他该怎么办?他想了不知多少次。而现在,他自己却给母牛找来一只公的——为一只偷来的母牛,或许!
那匹马,他却要归还。可惜——因为它是一个友善的小牲口,两个已经互相喜欢了。
“没关系,”英格安慰他说,“你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了。”
“哎,可是春天来的时候——我正是需要一匹马呀……”
第二天早晨,他安安静静地把最后一堆柴装上雪橇,出去了两天。第三天,走路回来,在靠近屋子的时候,站下来听。屋子里有奇异的声音……一个婴儿在哭——呀,老天爷!……就是在那里了;但他是个可怕的、奇怪的东西。英格又从没有说过一句什么。
他迈进屋子,最先看到的就是那装物箱——他挂在脖子上带回家来的那有了名的装物箱;就在那里了,两端各用一条绳子从顶篷上挂下来,是婴儿的摇篮和床了。英格已经起身,半穿着衣服在屋子里松松垮垮地走——她已经挤完了牛奶和羊奶,像平常日子那样。
孩子不哭了。“你都办好了?”艾萨克问。
“哎,办好了。”
“哼。”
“你出去的那天傍晚来的。”
“哼。”
“我只是把东西清理一下,把摇篮挂上,可是这也觉得吃力,好像,我就不得不躺下。”
“为什么你原先不对我说一声?”
“怎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定它哪时候来。是男孩。”
“噢,男孩。”
“我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我们应该管他叫什么。”英格说。
艾萨克看着那小红脸;长得有模有样,没有兔唇,已密密的长了头发。在他的阶层与地位来说,这些装物箱里的小东西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艾萨克觉得奇怪的虚弱。在这粗壮的男人面前是一个神迹,一个最初在神秘的雾中创造的东西,然后用这带着小脸的生命呈现出来,像隐喻着什么。经过一段年月以后,这神迹就会是一个人类了。
“去吃点东西吧。”英格说……
艾萨克是个伐木人,砍倒许多树,锯成木桩。现在他有一把锯,比以前好多了。他拼命做,木头大堆大堆地堆起来,排成了一条街,一座城。英格现在在屋里的时间比较多了,不像以前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出来看他,艾萨克必须自己找借口溜进房里呆一呆。屋子里有这么个小家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当然,艾萨克是绝不会梦想去注意他的——那只是装物箱里一块小东西而已。至于喜欢他么……但是当他哭的时候,觉得一个小东西有这样的哭,这样小小的哭声,是会心里有点感觉,而这也是人性而已。
“不要碰他!”英格说。“你那手上沾得都是树脂!”
“树脂,真的!”艾萨克说,“可是,我从盖过这房子以后手上就没沾过树脂了啊!把孩子给我,我抱抱——嘿,说多好有多好!”
※※※
五月初,来了一个客人。一个女的,翻过了重重小山,来到这没人来的孤单地方。她是英格的族人,并不是近亲。他们欢迎她。
“我想我只来看看,”她说,“看看金犄角离开我们以后好不好。”
英恪看着小孩,用一种可冷的小声音说:“啊,没有人问过他好不好;只不过是个小东西。”
“怎么呢,谁都可以看出来他很好啊。一个漂亮的小小子。一年以前谁想得到会在这里看到你,又有房子,又有丈夫,又有孩子呢,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坐在那里的那个人不嫌弃,要了我,只是这样。”
“结了婚吗?逐没有?噢,我明白了。”
“我们要看,等这小男子受洗的时候,”英格说“我们本来早就可以结婚的,可是分不出时间,要跑到教堂里什么的。你说怎么样呢,艾萨克?”
“结婚?”艾萨克说,“怎么呢,当然好啊。”
“可是如果你来帮我们,奥莲,”英格说,“空闲的时候只过来几天,帮我们喂喂牲口,可以吗?”
哎,奥莲会来。
“我们会不让你吃亏。”
至于这个,她留给他们办就好了……“我看,你又在盖房子了。做什么用呢?盖得还不错吗?”
英格看这是机会,就说:“怎么呢,你只能问他了。我是懂不了的。”
“盖房子?”艾萨克说,“噢,值不得说。一个小棚子吧,或许,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你说那金犄角怎么样?你想看看吧?”
他们过去,到牛棚,有母牛,有小牛,还有只公牛。客人点着头,看着牲口。在牛棚里,一切都要多好有多好,要多干净有多干净。“照顾家畜英格是一等能手。”奥莲说。
艾萨克提了一个问题:“金犄角以前在你们那里?”
“哎,从小。不过,不是在我那里,是在我儿子那里。不过也是一样。现在它妈妈还在我们那里。”
很久以来艾萨克都没有听过这么好消息了。负担轻下来。金犄角堂堂正正属于他和英格了。说真的,他曾经想过,要把这难题解除:秋天,把牛杀掉,把毛皮刮光,牛角埋掉,这样,这一辈子就把母牛金犄角的影子全都扫掉了。可是现在却用不着这样了。一下子他就为英格骄傲得不得了。
“哎,英格,”他说,“她是个做事的能手,这错不了。找不到比得上她的,也找不到跟她相像的。你可以说,一直到她来以前,我这里都是个可怜的地方。”
“怎么呢,这不过也是自然的事。”奥莲说。
就这样,那个山的彼端来的、说话温和而又聪明的、名叫奥莲的女人就跟他们住了两天,睡在那个小屋。当她要回家的时候,英格给了她一捆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来的。其实用不着藏这捆羊毛,可是奥莲还是小心着,不让艾萨克看到。
接下来又是孩子、艾萨克和他太太三个人了,又是原先的世界,日间工作,有许多小小的欢乐,也有大欢乐。金犄角的奶产得很顺,山羊的小羊羔断了奶,也产奶很顺,英格已经制好了一排红的和白的乳酪,尽存起来,等着晾干。她的计划是储存乳酪,一直到够买一个织布机。噢,这个英格,她知道怎么织布。
而艾萨克盖了一个棚子——他也有自己的计划,当然。他在草根土的一侧搭出一个厢房来,用的是双重镶板,还做了一个门,一扇有四块玻璃的干净小窗子,用板子搭了房顶。这些工作一直做到冰土融化,可以铲草根土的时候。这些都是有用的,而且必须的。没有地板,也没有光滑的墙壁,但艾萨克做了一个隔间,像给马用的,还做了一个马槽。
接近五月底了。太阳把高地的雪也融化了。艾萨克用草根土铺在厢房顶上,完工了。然后,有一天早晨,他吃了一顿可以维持一天体力的饭,拿了一些干粮,扛起了镐和铁锹,到村子里去。
“带三码印花棉布来,如果能够的话。”英格在他后面叫他。
“你要那个做什么?”艾萨克说。
艾萨克已经走得好远了,看起来就像要永远不回来似的。英格天天看天气,注意风怎么刮,就像她在盼望帆船归来似的。夜里她出去听,甚至想要抱起孩子,跟在他后面去了。后来,终于他回来了,带着一匹马,一辆车。“皮特罗!”艾萨克一边走近一边喊,喊得让英格听到才罢休。那匹马也驯良得很,静静地站着,向草根土的小屋点着头,就像它还记得它似的。不过,艾萨克还是喊着说:“嗨,出来把马拉一拉,可以吗?”
英格出来了。“它现在在什么地方?噢,艾萨克,你又租了它来吗?你这么久都在那里?六天了。”
“你想我在哪里?不得不到处钻,找一条可以把我这辆车拖过来的路。把马拉一下,行吗?”
“你的车!你不是说你把车买了下来吧?”
艾萨克像哑巴,艾萨克说不出来的得意。他提出一个犁,一个耙子来,他买的,钉子,日用品,磨,一袋种子。“孩子怎么样?”他问。
“孩子很好。是你买的车吗?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在这里盼望又盼望要一个织布机。”她开玩笑地说,因为他又回来,她高兴。
艾萨克又哑巴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忙着他自己的事,衡量着,考虑该把他那些东西与工具放在什么地方?找空地来放真是不容易了。但当英格已经不打算再问了,而说起马怎样的时候,他终于从他昂然的沉默里破出来了。
“看过一个农庄‘没有’马和车,犁和耙子,和所有这些别的东西的吗?你既然想知道,那好吧,怎么呢,是我买了这匹马和车,还有车里所有的东西。”他说。
英格只能摇头,幽幽地说:“真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艾萨克不再是微不足道,不再卑屈了,他像个君子一样,付了金犄角的钱。“你瞧吧,”他会说,“我带了一匹马来,我们可以叫它让点地方出来了。”
他一反常例,又机灵又笔直地站在那里,把犁又挪了挪,一只手把它抬起来靠在墙上。噢,他可以经营一整片农场!他又拿起了其他的东西:耙子,磨,他买的新叉子,都是值钱的农具,新家庭的宝藏,了不起的展览。所有需用的东西都有了——什么也不再缺。
“哼。那织布机吗,怎么呢,我一样可以想办法,我敢说,只要我身体没毛病。这是你的印花棉布,除了蓝色的没别的,我就要了。”
他带回来的东西是没完的。无底的井,丰富得不得了,像城里的仓库。
英格说:“我恨不得奥莲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她统统看到了这些东西。”完全是女人!完全没道理的虚荣——就像那有什么重要似的!艾萨克不屑地嗤着鼻子。尽管如果奥莲真看到了他自己也并不会不高兴。
孩子在哭。
“进去,看孩子吧,”艾萨克说,“我要照顾马。”
他把马卸下来,牵到马厩里:哎,艾萨克正是在把马牵到厩房去!喂它,摸它,温柔地待它。而现在,这匹马和这辆车又让他欠了多少债呢?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实在是一大笔账啊;但今年夏天一定还得了,用不着怕。他有很多捆的木材,还有去年剥下来的建材树皮,更不用说沉重的树干。时间足够。但过后,当得意与高兴冷却下来,确实焦急害怕了好一阵子,全靠今年夏天的木材和谷子了,不知道今年天气怎么样。
日子全用在田里,越来越多,他开垦了新地,掘出树根和石头,耕,施肥,挖地,用十字镐和铁锹,把土块用手用脚揉细,踩碎,他向来就是耕地的好手,把田耕得像天鹅绒地毯一样。他又等了两天——看起来要落雨的样子——然后下种子。
许多代以前,在那没人记得的时代,他的祖先就下种子;在灰雁刚刚飞过不久,又平和又安静的傍晚,最好下着温和的雾雨,庄严地把种子播下去。马铃薯是新东西,并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神圣的;女人小孩都会种——泥土里的苹果,从外方来的,像咖啡一样。丰富好吃的食物,但又像萝卜和甜菜。种子和面包一样重要,有种子或没有种子,就等于生命或死亡。
凭着耶稣的名,艾萨克光看头播种。是个播种者。他的身体像个有手的树根,心却像孩子。每抛一颗种子都是小心的,用着慈和的牺牲的精神。看!小小的种子活了,长大了,冒出了种子,生了更多更多的种子;全世界凡是播了种子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巴勒斯坦、亚美利加、挪威本国的山谷——广大的世界,而这里是艾萨克,在世界中一个小点,一个播种者。种子的小雨扇形地从他手上撒出去。慈和的多云天,预示着要下最微细的小雾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