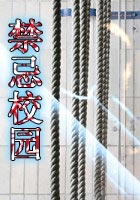他喜爱这到办公室熟稔的路途中每一地区的景物:花岗区的别墅平房,灌木丛和蜿蜒交缠的车道。史密斯街上的单层商宅,厚玻璃闪着炫眼的光,新砌了的黄色砖墙,杂货店、洗衣店与药房供给东区的家庭主妇日用品。荷兰移民聚集的低洼区的蔬菜园,简陋的住屋,补缀着波状铁皮和窃来的木板门。广告招贴板上,一位九尺高深红色的美女,广告着电影、烟草与爽身粉。沿第九街东南的老“公寓大厦区”,似年华老去的纨绔子弟穿着污脏的麻布衣衫;本应是森林城堡,如今却是公寓房子,尘土泥路,红褐色的灌木树篱,四处紧挨着停车间,低廉的公寓,和殷勤圆滑的雅典人经营的水果店。铁道两边是工厂,高高的水塔,高大的烟囱——生产炼乳、纸箱、照明器具和汽车。而后,到达商业中心了,密集匆骤的交通,挤得沙丁鱼般的电车正停下来吞吐着乘客,一些高级建筑的门廊镶嵌着大理石与闪耀着光泽的花岗石。
这一切是伟大的——而巴比特尊敬任何大的事物,高山、珠宝、膂力、财富以及所有相关的字眼。他沉醉在春天的氛围里,对天顶市汩涌着抒情的、几乎无私的爱。他想及偏远的工厂郊区;查尔露莎河及两岸被侵蚀的滩地;华达山上斑驳的果树林绵延向北,以及那一大片肥沃的乳酪农场,大谷仓和优游自在的兽群。他让他的乘客下车,同时大呼道,“喔嘘,我觉得今早真棒!”
3
他进入办公室前,停车又是一出好戏的开始。他从奥贝林大街转过来,绕过街角到第三街东北区,他一路注意着停车线内有无空的车位。有一空位,另个驾驶人争先滑入了,错过这机会令他生气。前头,另辆车正退出边栏,于是巴比特慢下来,伸手出去向后面追逼上来的车子示警,似一位激动的老妇人,制止卡车从他的另一边钻入来。他停下车,前轮碰到前辆车的锻钢保险杠,他狂乱地把转他的前轮,倒车滑入空位,十八英寸大的空间,他费劲地让车子跟边线平行。这是一桩男人的冒险,必得巧妙的技巧才能完成。他满意地在前轮上加了一个保证防盗的钢销,横过街到名人大厦底楼,他的房地产办事处。
名人大厦备有防火设备,似巨石般的安全,又似一架打字机地充满了工作效率;十四层楼,黄色耐压薄壁,明亮,笔直而一点也不优雅的线条。大厦内设有许多行业的办事处:律师、医生、机械代理商,金刚砂旋转磨石代理商,铁丝网筑墙建材代理商,以及采矿代理商。他们的金字招牌在玻璃窗上闪耀着。入口处,十分摩登风格的波浪状线条的柱子,整幢大厦显得静谧、冷峻而整洁。靠第三街马路的是联邦西部电信公司办事处,蓝台夫特糖果店,箫特威尔文具店,和巴比特一汤普逊房地产公司。
巴比特原可以从临街的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像顾客一般,不过为了让自己感觉是这大厦内部的人,他穿过大厦长廊从后门进入。如此,他能受到一些内部员工的招呼欢迎。
这些在名人大厦走廊间活动的小人物——电梯间听差,唤车跑差、机工、管理员。和一个面带狐疑阴郁经营报纸香烟摊子的跛脚男人——他们一点也不像是这城市的启民。他们显得卑陋,生活在这窄逼的钢筋水泥山谷间,仅对彼此和这大厦感兴趣。他们的大街,即是入门大厅,石砌的地板,冷峻的大理石天花板,以及商店的橱窗。这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名人大厦理发店,不过这也令巴比特感到困窘。他自己,只光顾松莱饭店富丽堂皇的庞贝理发店,而每次他经过这名人大厦理发店——一天十次,一百次——他总觉得这儿虚晃晃的不属于他的大厦。
现在,这一位地主阶级的士绅要人,在村民带礼敬的欢迎招呼声中,踏入他的办事处,他感到和谐平静与一种高贵的威严,而一大早的那种不调谐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
随即,又听到那不调适的噪声。
史丹莱·格雷夫,一个跑外头的推销员,正在电话中谈着生意,用那种可谴的缺乏诚笃坚定的声腔,像在教训顾客一般:“就这么说,啊,我认为就只有那房子适合你——那间林顿区的波亚蒙屋子……哦,你看过啦。好,那印象怎样?……哼?……噢,”犹疑地,“噢,我知道了。”
巴比特走入他的私人房间,一间用橡树与不透光玻璃半隔间的囚室,这时他一面想着,要寻一位能有自信去策动销售的职员是多么困难。
除了巴比特和他的岳父兼合伙人,很少过办公室来的亨利·汤普逊外,另外还有九位职员。这九人是:史丹莱·格雷夫,外务员——一个蛮年轻的男人,酷爱抽烟与那种撞球的把戏;马特·柏尼曼老头,负责杂务,收各种租金以及推销保险——显得衰颓、沉默而阴沉,他曾是一位神奇著名的房地产业中的“好手”,曾在傲人的纽约布鲁克林区拥有一家他自己的公司;查斯特·格买·雷洛克,驻在金莺幽谷新社区的售屋员——一个热心的家伙,留着丝密的胡子,有众多的子女;婕儿莎·麦克钟小姐,又敏捷又漂亮的速记员;魏洛波达·潘尼根小姐,肥胖、迟钝但工作认真的会计兼档案管理员;另外四位兼差的代理推销员。
从自己的囚室望向大房间,巴比特觉得丧气了,“麦克钟是个好速记,漂亮的人儿真是一道饭后的甜点心,不过啰,史丹莱·格雷夫和所有那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春天早晨的兴味在不新鲜的办公室空气中窒息了。
平时,他蛮喜爱这办公室,总带着一种惊喜“发现自己竟能创办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地方”,平时,他会被内里一尘不染的器物和那种热喧的气氛所鼓舞,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平淡无味了——地板铺着地砖似间浴室,赭色金属天花板,硬冷的灰泥墙壁,褪色的图表,漆着素色的橡木椅子,钢制的桌子与档案柜则漆成淡绿褐色。煞像一座地底坟墓,一座钢筋殡仪馆,在这儿,游荡嬉笑俱是严重的罪咎了。
他甚至对那新的冷水机也瞧不顺眼!而那是最好的冷水机,最新式的、科学的、正确的思想的化身。它费了不少钱(这也即是它的长处啰)。它有一个绝缘的纤维质冰罐,一个瓷制大口水瓶(保证合乎卫生标准的),一个不漏水不滞塞的卫生龙头,还用两种金色色调漆上这机器的标志。他凝视底下,顺着大片冷苛的地砖,眼光落在冷水机上,他自信这名人大厦内没有一家住户能有比这更华贵的冷水机,然则,他已无能再由此感到那种社交上的优越感了。他惊愕地咕噜着,“我最好马上逃得远远地到森林去。整天游荡个痛快。今晚,得再去杨齐家玩扑克牌,得尽情地痛咒一顿,得喝它一百、九十罐啤酒。”
他叹着气,一面读完他的信件;他喊道“蜜司钟”,它的原意是“麦克钟小姐”;他开始口授信稿。
这即是他第一封信的口述稿:
“奥玛·格利伯,把这信送到他办公室,麦克钟小姐,二十日的尊函收悉,就在这里答复你,格利伯,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犹疑不决,我们可就会丢掉亚伦的生意,我前天已把亚伦仔细考虑了一番,斟酌了各种情况,而认为我可以向你保证——啊,啊,不,改为:所有我的经验都指出,他没问题,诚心做生意,过去调查他财政记录也很好。——这句子好像有点混乱啰,麦克钟小姐,如果你觉得需要,可拿它断成两个句子好啰,句点,新的一段。
“他完全愿意按比例分摊额外的款项,再说我想,我敢说这一点也没有困难的,他会付那笔保险费的小钱,所以啰,现在,看在老天面上,让我们热络起来——不,改成:所以现在让我们马上动手,攻下它——,不,够啰——你打字时,可把句子浓缩得好一点,麦克钟小姐——你诚挚的,等等等等。”
这是当天下午,麦克钟小姐打好送给他过目的信函:
巴比特一汤普逊房地产公司
民众服务之家
名人大厦,奥贝林大街,第三街东北区,天顶市
奥玛·格利伯君
北美大厦576号
天顶市
亲爱的格利伯先生:
您二十日来函收悉。我必须说明,我十分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这般犹疑不决,我们就会失去亚伦的生意。我前天已把亚伦仔细考量一番,斟酌各种情况。所有我的经验均指出,他诚心诚意做这趟生意。我也调查过他的财政信用记录。十分不错。
他完全愿意按比例分摊额外的款项。要他付那一丁点保险费也决无困难。
所以马上着手进行!
你诚挚的
他读完信函,用他那流利的合乎商业学院式的签名签了名,巴比特想:“瞧,多棒,多有力的一封信,像钟声一般清晰。瞧这是啥——我绝没有要麦克钟放上这第三段!天可怜见,她最好甭修改我的口述内容!不过,我倒不能明白的是:为啥史丹莱·格雷夫或查斯特·雷洛克可写不出像这样的信?费尽吃奶之力也写不来!”
这天早上,他口述信稿中最重要的是,隔周一次的广告信函,油印好后将寄给一千位“可能的顾客”。这信稿,仔细模仿了当时流行的最好的文章典型,一种剖心相谈似的广告词,“销售诱引术”般的文字,集中在“意志力的开拓”这题目上大作文章,一种抢着塞给客户的信,似一家新设的商业诗人学校堂皇推出的校内刊物。他艰苦地写完初稿,随后像一个纤美而心神恍惚的诗人一般吟诵起来:
喂,老朋友!
我只想晓得我能否帮你个忙?真的!不开玩笑!我晓得你乐于有间房子,不仅为了有一个你可以挂挂老帽的地方,也为妻儿弄个爱巢——或许也为了你那辆停在老远老远(一定得写成老——远——老——远,麦克钟小姐)的马铃薯园外头的蹩脚汽车。喂,你是否曾想到我们在这里等着解决你的困扰?那就是看我们给你一个活泼的——大家可不须为我们这美意付半毛钱给我们!现在,请注意:
请在你那有着优美雕绘的桃花心木写字台前坐下来,写一张短简投寄给我们,告诉我们你需要的是啥,如果我们能为你找到它,我们即把好消息带到你的府上,如果我们无法效劳,我们就不再打扰你。为了节省时间,请填随函附寄的询问空白。为了你的需要。一并附寄有关花岗区、银树林区、林顿区、贝洛本和所有东区住宅区的询问调查表。
诚挚为您服务的
P.S.——只要给我们一点提示,我们就能为你选择——当今真正价廉物美的房子:
银树林区——四房娇巧加州小别墅,内有车房,名贵的遮荫树木,令你骄傲的名流邻居,方便的车道。总价三千七百元,头款七百八十元,余额付款轻松,巴比特一汤普逊公司的价钱。比租用还便宜。
道查斯特区——精品屋,艺术风味的双并住宅,外层全部橡木,拼花地板,可爱的圆材暖炉燃管,门廊宽敞,殖民风格的,“全天候暖气车房”,每幢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口述时,就得坐下来思考,不必喧喧扰扰真做什么大事地团团转了,巴比特坐在他那把可以旋转发着吱声的椅内,微笑地凝看着麦克钟小姐。他觉得,她还是女孩模样,黑色短发贴在端庄的脸颊上。从寂寞中涌起一种模糊的渴望,他变得敏感纤弱了。她正等着他的话,拿长长的、考究的铅笔心轻敲着写字板,他几乎把她跟他梦中的仙女视做一人了。他想象,他俩的眼睛惊悸地认出了彼此;想象,他又颤惊又虔敬地轻吻着她的唇,而且——她唧唧地说话了,“再来呢,巴比特先生?”他咕噜地:“完啰,我想。”而后,沮丧地掉开了念头。
在他所有飘忽的念头中,没有比这更亲切秘密的了。他常如此省思,“永别忘记老杰克·奥非德怎么说的,一只聪明的鸟绝不在他的办公室或他自己的巢里,搞这些调情的烂玩意。惹麻烦罢了。当然。不过,——”
整整二十三年的婚姻生涯里,他总不自然地窥看每一双逗人的玉腿,每一副柔嫩的香肩;一面想象自己珍抚着她们?然则,他从不会把他的尊严、名誉、地位拿出来冒险一赌。现在,他一面估价样品屋包装用纸需要多少花费,一面又陷入纷扰不安了,事事物物无一不觉得不满意,他为这不满感到羞愧,同时也为了自己内心对那仙女的那种寂寞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