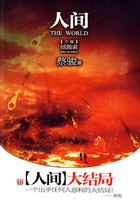1
汽车对乔治·福·巴比特的意义,如同大多数天顶市成功兴旺的市民一般,汽车俨然是一首诗与悲剧,情爱与英雄气概。办公室是他的海盗船,而汽车即是他在陆地上冒险的旅程。
每天在巨大的困扰危机中,没有比发动引擎更富戏剧性的了。冷冽的清晨,引擎显得迟钝,起动马达长久发着令人不安的呼呼声;有时,他得在汽缸栓内滴几滴醚,而妙的是吃午餐时,他会一滴一滴记录着,口中计算每一滴花了他多少钱。
这个早晨,他模糊地觉得想寻些碴来出气,而汽车混合剂一下子便爆出甜蜜有劲的引擎声,他觉得似乎被什么藐视了,倒车时碰着了门柱,挡板刮下许多凹痕和碎片。他迷恍着。他向山姆·道卜布勒大嚷“早安”,声腔里含着过多的、他原并不预备那般的热诚。
巴比特白绿相间的房屋,是詹丹路上某条街三间并邻的房子中的一间。左邻是山姆·道卜布勒的住宅,他是某一生意兴旺的浴室配件批发公司的秘书。山姆的房子也是挺舒适的,只不过没有任何建筑风格:木造尖房子,矮踞的顶塔,门廊宽敞,漆上黄色亮漆。恰似一只蛋黄。巴比特批评道卜布勒夫妇是“波希米亚人”。半夜从他们屋子传来音乐和淫秽的笑声;邻居谣传他们私造威士忌,又有快捷的运送管道。他们让巴比特有许多愉快的扯谈的夜晚,其时,巴比特会有板有眼地宣称:“我可不是过分拘谨的人啰,我并不在意某人偶尔喝个烂醉,不过,他要是有意借种种吵吵闹闹来逃避,像道卜布勒这般,那对我的生命来说可太荒唐啰!”
右邻住的是哈伍德·小野先生,一位哲学博士,住在一间极具现代风味的房屋里,较低的一边是暗红雕绘砖壁,凸出一个铅框壁窗,较高一边则是白苍色灰泥壁,似溅泼了大片污泥,红瓦屋顶。小野先生是邻居中的“大学者”,俗世诸事物的权威,除了婴儿、烹饪和汽车。他是布鲁盖特学院的文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天顶市街车公司的职业经纪人和广告法律顾问。他能在市议会或州议会会场出现,作足足十个小时的评论,用成串的数字和从波兰到纽泽兰的种种先例,坚决证明街车公司关怀大众利益,怜悯员工;而它的股票所有者都是一些寡妇和孤儿,公司因此期望做的是,增加出租的价格让财产所有人获益,同时降低租金来帮助穷人。所有和他相识的人有事无事都来寻小野先生,当他们想知道撒拉哥沙战役发生的日期,“破坏行动”这个字的定义,德国马克的前途,“himcilloe lachrimoe”的翻译,或煤焦油的生产量。他令巴比特感到敬畏,因为他自己说,他常坐到半夜,研读政府公报的种种数字和附注,或是单单阅读(一面挑挑作者的错误以为消遣)最近出版的化学、考古学以及鱼类学的著作。
然则,小野先生的最大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精神的模范。除了他那一套鲜奇的学问外,他还是个严笃的长老会教友和坚贞的共和党员,似乔治·福·巴比特一般。他坚定了这些商人的信心。他们原仅由强烈的感情上的直觉,认定他们生活其中的商业与礼俗制度是完美的,哈伍德·小野博士则从历史、经济和一些改过自新的激进分子的谶言中,为这些商人作了印证。
有如此博学之士做邻居,巴比特颇感骄傲,而且泰德能跟优妮斯·小野亲近,他也觉得与有荣焉。优妮斯十六岁了,对需要计算的东西一无兴趣,除了电影明星的年纪和薪水,不过——诚如巴比特明白地点出——“她可是她那老爸的宝贝女儿。”
一个像山姆·道卜布勒那样容光焕发的男人,和一位真正卓越的人物,如小野先生,二者间的差别隐藏在他们的外表下。就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来说,道卜布勒显得令人不安的年轻:后脑戴一项圆顶窄边丝质礼帽,红润的脸上老是闪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笑。而小野不过四十二岁,却显得老了些:高大粗胖;金边眼镜深陷入长脸的皱褶里;头发是一堆带油腻的黑;吸老式烟斗——总之,是阴郁的人,像个副主教似的,但比起房地产经纪行业和浴室配件销售业,他则多了某种神圣的风味。
这时,他蹲在屋前,检视宽阔的水泥人行道和边石间的蔓草。巴比特停下车,倾身出去大喊:“早!”小野拙重地踱近来,一只脚踏在汽车踏脚板上。
“多棒的早晨。”巴比特说,一面燃上——比平常日子早了些——一天里的第二支雪茄。“是罢,是不错的早晨,”小野说。“瞧这,春天可来得快啰。”“是罢,真是春天了,不错。”小野说。“不过,夜里还冷着呢。昨晚在睡廊上得盖两条毛毯。”
“是罢,昨晚是不太温暖。”小野说。
“不过啰,我可不希望现在我们还会再有啥酷冷的天气。”
“不会罢,只不过,昨天,蒙大拿州第福莱还下着雪,”这位学者说,“你得记得三天前更西边还有暴风雪——科罗拉多,格里雷有三十英寸积雪——再则,两年前我们碰到一次大风雪,就在天顶市这儿,4月25日那天。”
“真的吗?说看看,老朋友,你瞧共和党候选人这事如何?他们会提名谁当总统?你不以为这是我们拥有一个纯粹商业政府的时候啰?”
“我认为,国家所需要的,最先和最重要的,是一种好的、稳健的、对听有事务予以商业化的经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商业体制的政府!”小野说。
“我高兴听到你这样说!我真的高兴听你这样说!我不晓得你怎会也有这般看法的,呵,我真高兴你也那样认为。国家所需要的——就在此时——可不是一位学院派的总统啰,也不是模仿许多外国的东西啰,而不过是一个好的——稳健的——经济至上的——商业化的——政府部门,赐我们一个机会去拥有某些东西,哈,那可像一次适时的人事大变动。”
“是吧。一般人总不能认知,即使在中国,学者也提供方法给广大的实际的人群,当然你就可了解其中的暗示了。”
“真的吗?棒!真棒!”巴比特吐了一口气,感到心平气和了,对于世界上诸事物进行的方式,也乐观多了。“唷,停下来跟你谈一阵子真好。我想得赶去办公室,骗骗几个顾客啰。好,再见?老朋友。晚上见。再见。”
2
他们一直辛勤劳动着,这些可靠的市民。花岗住宅区的这个山坡地,如今有着闪亮的屋顶,洁净的草皮,是令人咋舌的舒适了。二十年前这里原是一片荒野,丛生着原始林破坏后滋长的榆树、橡树和枫树林。沿着现在考究的街道,彼时还是几块长满树木的空地,和一个废弃了的果园败残的遗迹。如今,这儿是光彩夺目的了;苹果树鲜亮的叶子似燃着绿焰的火把。樱桃花开的第一朵纯白轻拂着溪涧,知更鸟成天噪聒着。
巴比特嗅着泥土香味,朝歇斯底里叫着的知更鸟咯咯发笑,就像他一向朝小猫或滑稽的影片咯咯发笑一般。他看来是那种踌躇满志的正要上班的经理主管级人物——一个丰润的男人,戴一顶标准式的褐色软帽,无框眼镜,抽着一根大号雪茄,驾一辆蛮棒的汽车,驰在邻郊区的林阴大道上。在他的内心里,有某种对他的邻居,他居住的城市,他隶属的宗派团体,怀着无可怀疑的挚爱的强烈天性。冬天——将过去,建筑业将活跃起来,可以预见未来的扩展,这些即是他可引为夸耀的成就。他已抛开黎明时的那种沮丧,把车子停在史密斯街,拿那件褐色裤子送洗,又把油箱灌满了油,他赤红的脸显得开朗快乐了。
熟稔的景象和过程,更加深了他的愉悦和信心:高大红色铁制的打油机,空心瓷砖,赤褐色的修车间,窗口吊满了令人愉快的杂碎——磨得发亮的外胎,纯色瓷制保护套的火星塞,金制与银制的胎链。经验丰富但脏兮兮的汽车修理工人希勒贝斯特·蒙恩,走近来殷勤地招呼他。“早啊,巴比特先生!”蒙恩说。这下子,巴比特觉得自己可是位要人啰,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连这样忙的修车工人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不是那种在蹩脚汽车内转来转去的小气鬼啰。他喜欢自动码表的精巧,一加仑一加仑咔啦地跳过去;喜欢广告标语中的机智:“及时加满免得陷入困境——今天汽油一升三十一角。”他也喜欢汽油注入油箱时发出一定节奏的咯咯声,以及蒙恩转动把柄时有规律的机器声。
“今天,打算加多少哪?”蒙恩问,用一种态度,既显示自己是那种自主的重要的专家,够资格亲密地跟对方闲谈,又显示自己尊敬社交场上的要人,像乔治·福·巴比特这类人。
“加满。”
“您支持哪位共和党候选人呢,巴比特先生?”
“现在还太早啰,无法预测。到底,还有整整一个月零两个星期——不,三个星期——该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是啰,离共和党提名大会总共还有六个星期多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给所有候选人一个表现的机会——从头到尾瞧着他们,打量打量他们,再仔细作个决定。”
“那倒是真的,巴比特先生。”
“不过啰,我可得告诉你——我四年前,哦,八年前就同样坚持这个立场,从现在算起四年后,这也将是我的立场——是啰,从现在算起八年后也一样!我常跟每个人说,不过一般人不十分了解的就是,我们首先、最后和所有的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和谐的商业至上的政府!”
“噫嘻,那真不错!”
“你瞧两个前胎情况怎样?”
“棒!很棒!假使每个人学您这般照顾自己的车子,那修车厂可没生意做啦。”
“哟,我不过稍稍用点心罢了。”巴比特付了钞,还适时地说,“喔,余钱免找了,”随即,深陷在一种自我陶醉中开车离去。他以那种“大善人”的姿态,朝一位等候电车看来尚体面的男人喊说,“搭个便车吗?”那人爬进车来,巴比特以一种纡尊降贵的口气说,“上商业区?不管啥时候,我瞧见等电车的家伙,我总习惯让他搭个便车——除非,当然啰,他看来像个小瘪三。”
“希望有更多人对他们的汽车能这般慷慨!”这位在善心之下的受难者尽责地说。
“噢不,说到这慷慨倒是个问题。其实,我总觉得——前几天晚上我就这样对我儿子说——一个人的责任,是和邻人分享这世上美好的事物,而今我感到被嘲弄与生气的是。一个人自我陶醉,到处去吹他的喇叭,仅仅因为他是仁慈慷慨的。”
这位遭难者似乎寻不到恰当的回话。巴比特嗡嗡地继续说:
“电车公司在这些线路上给我们带来许多不方便。跑一趟波特兰路,甚至得费上七分钟。冬天早晨,站在街角等车,冷风刺痛着脚踝,人可会冻坏啰。”
“那倒是真的。街头公司一点也没顾到他们给我们的是怎样一种鬼待遇。应该弄点什么整整他们。”
巴比特可吃惊了。“不过话说回来啰,当然不该只管我电车公司的碴,而不去体会他们私底下的难处,像那些激进分子只想夺内部的控制权。这些工人要挟公司提高工资的方式就是一种罪恶,当然啰,负担还不是落在你我头上,车票涨到七分钱!事实上,他们所有的线路服务上也有显著的改善啰——总而言之。”
“噢——”对方不以为然。
“怪好的早晨,”巴比特解释说,“春天来得快了。”
“是,真是春天了。”
这位受难者没有独到的风味,也无机智,于是巴比特陷入长长的沉默,专心玩起一种游戏,要在交叉口前赶过电车:一种冲刺,街尾的追逐,令人神经吃紧地加速,飞驰在电车巨大的黄线区与一列停靠得歪歪斜斜的汽车间,当电车骤停时,他的车子子弹似的掠过——一种珍奇的、勇敢的游戏。
然则,他始终意识到一种对天顶市的爱。几星期来,他一无所见,除了顾客和那帮带着讨厌的“租”的标记的竞争经纪人。今天,在一种神秘的不安里,他带着同样神经质的敏感,一下子发怒一下子高兴,而今天春天的光色如此迷人,让他不由得抬起头来欣赏着周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