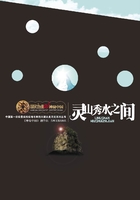但是,杰里柯也有众多的特点,这使它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并自带一种象征性的地位。跟别处已经为人所遗忘的村落不一样,它是值得人纪念的,比《圣经》还要古老,叠在一层又一层的历史之上,是一座城市。古代有甘水流过的杰里柯是沙漠边缘上的一片绿洲,沙漠之泉从史前时代一直流到今日的现代城市。在这里,小麦和水交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就开始了文明。也是在这里,贝都因人到来了,他们围着头巾的黑色的脸从沙漠中显现出来,嫉妒地看着这边的新生活。这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部落直奔应许之地的途中来到这里的原因,因为有了小麦与水,他们就创造出了文明:他们让应许之地成为奶与蜜横流的大地。小麦与水将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池。
当时,杰里柯突然之间就改变了模样。人们到来了,很快成为邻居嫉妒的对象,因此,他们必须使杰里柯坚固起来,将它变成带城墙的城池,并建起了一座巨塔,时在9000年之前。这座塔底部有30英尺之宽,深度也是30英尺。在塔的旁边往上攀爬,发掘物展示出一层一层的古代文明:早期的陶罐前人类,接下来的制陶前人类,7000年前制陶业的出现;早期的铜制品,早期的青铜制品,中期的青铜制品。这些文明都到达此地,征服杰里柯,将它埋葬,然后再建立自己的文明。因此,这个塔本身与其说是埋葬在45英尺的土壤之下,倒不如说埋葬在45英尺的古代文明之中。
杰里柯是历史的缩影。后来还找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发掘地),能够改变我们对文明起源的想像。但是,耸立在这里的力量,沿着现代人攀升的路线往回看去,它引起的思想和唤起的情绪都是同样深刻的。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主宰来自人类对于这个外部环境的控制。现在我们得知,真正的主宰来自理解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就是人类在肥沃新月区开始的情形,这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手放在植物与动物上,在学会了与它们同生之后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当凯瑟琳·肯尼昂予1950年代重新发现这座古塔的时候,她发现里面是空的,而在我看来,里面的楼梯就是一种主根,是一个窥孔,可以看到文明的岩石基础。文明的岩石基座就是现在活着的一切,而不是外部的世界。
到公元前6000年,杰里柯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农业定居区了。凯瑟琳·岢尼昂估计里面曾住有3000人,墙体内有约8到10公顷的土地。妇女用很重的石头工具打磨小麦,这是定居区的一个特点。男子制造泥坯烘制作砖块用,这是已知最早的一些砖块。做砖者的拇指的痕迹仍然留存在那里。人跟普通小麦一样在这里固定下来了。定居村落与死者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杰里柯的居民保存了一些骷髅,并以精致的装饰品盖住这些头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一种表示尊敬的行为吧。
只要是在《旧约》的教育中长大的人,比如我本人,离开杰里柯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提出这么两个问题:约书亚最终是否毁掉了这个城市?这些墙体难道真的是自行坍塌的吗?就是这些问题使人们来到这里,并使它成为一个活体传奇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容易的答案存在着:是的。以色列部落正在拼命进人肥沃的新月地带,这一地带沿着地中海沿岸北上,经过安纳托利亚山南下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这电,也就是杰里柯,它成了锁住他们前往朱迪山的去路的关键,使其无法进人地中海沿岸肥沃的大地。因此,他们必须攻克杰里柯,约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就这么做了,据今约3300年到3400年。圣经的故事直到公元前700年才写出,也就是说,里面的叙述是年代约为2600年的文字记录。
但是,那些城墙是自行倒下的吗?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有一大批城墙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白天一下子夷为平地了。但是,许多城墙的确倒下了,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倒下的。这里有一个青铜器时代,一批城墙至少重建了16次。因为这是一个地震区。今天,这里每天仍然在发生震动,一个世纪里面发生过4次大型地震。只是到最近几年,我们才慢慢明白为什么地震会在这一带的河谷活动。红海与死海都处在东非大峡谷的连续带上。在这里,承载着大陆的两大板块在地球更密实的地幔上飘浮时并肩移动。当它们沿着这个峡谷彼此冲撞的时候,地表会回应地底深处产生的震动。结果,地震总是沿死海所在的那个轴上发生。在我看来,这就是《圣经》里面到处都是自然奇迹发生的记载:古代的洪水,红海干涸,约旦河干涸,杰里柯的城墙倒塌。
《圣经》是一个好奇的历史,一部分是民俗,一部分是记录。历史当中是胜利者写下来的。以色列人冲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成为历史的承载者。《圣经》就是他们的历史:一个不再当游牧者,不再依靠畜牧业,并成为定居农业者的民族的历史。
耕种与饲养似乎是很简单的追求,但是,纳图夫人的镰刀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并没有停滞不前。在植物与动物的驯化过程当中,需要有发明创造,这是从技术用具开始的,科学原理也从中产生。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村落里面,心灵手巧的人都会制作出基本的工具。他们发明的很多小物件都很有创意,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的攀升当中跟核物理学中的仪器设备一样重要:针、锥子、陶罐、火盆、锹、钉子与螺丝、风箱、绳子、结、纺织机、马具、钩子、扣子、鞋——人们可以一口气列出100多项发明来。这样丰富的发明起源于各种发明的相互影响。一种文化就是多种思想的倍增器,每一种新的用具都能加快和扩大其余工具的力量。
定居农业创造了一种科技,所有的物理学、各种科学都可以从中起飞。我们可以从早期的镰刀与最新的镰刀当中看出这个变化来。初一看,它们大致差不多:10000年前的收割者使用的镰刀与9000年前培植小麦时使用的镰刀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培植的小麦是用带锯齿边的东西割断的,因为如果你击打小麦,谷粒就会散落在地上;但如果你只是轻轻地锯它,谷粒就会保留在麦穗上。镰刀自那以后就做成了那样的形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弯曲的镰刀还是带锯齿的样子,那就是你收割小麦所用的工具。那样的技术,那样的物理知识,全都是自发地从我们的农业生活当中的各个部分产生的,我们感觉就好像那些点子自动找到了人,而不是反过来的情形。
农业当中最重要的发明当然还是犁。我们觉得犁是一种楔形工具,可以将土层分开。而这样的楔子是一项重要的早期机械发明。但是,犁还是更重要的一种东西,它是一根杠杆,可以撬起土壤来,也是杠杆原理最早的运用。很久之后,当阿基米德向希腊人解释杠杆原理的时候,他说,有了杠杆的支点,他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但数千年之前,中东的扶犁者只是在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养活大地。”
我在前面曾说过,农业至少又得到了一次发明,是很久以后在美洲进行的。但是,犁与车轮却没有,因为他们依靠拖车的动物。超过中东简单农业的一大步是拖拉动物的驯化。没有跨出这一生理进化步伐的人,就使新世界回到用木棍挖东西和用肩膀扛东西的水平。它甚至都没有想到陶轮。
轮子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000年属于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地区发现的。这些早期的发现都是实心的木轮子,连在更古老的木排或雪橇上拖拉重物,然后又转换成车的形状。从那以后,轮与辐成为二重根,众多的发明从中萌生。例如,它变成了一种磨小麦的工具,并利用自然之力来做这项工作;先用动物的力,然后用风与水的力。轮子成为一个模型,所有旋转运动都可围绕它来进行,并成为解释的常用比喻和天国的象征,说明人类在科学与艺术当中的力量。太阳是一辆有轮的战车,天空本身也是一个轮子,从巴比伦人与希腊人描述天体运动的图谱的时候便开始如此了。在近代科学中,自然的运动(也就是说,不受干扰的运动)是以直线形式进行的,但对于希腊科学来说,看上去自然一些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说,自然固有的运动形式),事实上也比较完美一些的运动还是在圆中。
到约书亚侵袭杰里柯的时代,比如公元前1400年,苏美尔人和亚述人中的机械工程师将轮子变成了一种滑轮来取水。同一时代,他们设计出大型灌溉系统。竖直的保养并仍然留存着,就如同在波斯风景上留下的标点符号。它们往下通到300多英尺以下的坎儿井或地下暗渠,构成一个灌溉系统,到了这个水平以后,自然流出的水就不会因蒸发而干涸了。这些地下灌溉系统修建成功后的3000年后,库茨斯坦的农村妇女还在使用坎儿井里面的水,继续完成古代社区的日常杂活。
坎儿井是城市文明末期的建造物,它们意味着那个时候已经有法律存在,以便管理用水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在农业社区当中(例如苏美尔人的大规模农业耕作),法律的统治跟游牧民族的法治不太一样,因为游牧民族的法律仅仅管理羊的偷窃。现在,社会结构已经为影响整个社区的复杂事务的管理所束缚了:土地的占用,用水权的维护与控制,季节的收获所倚重的各种宝贵设施的轮流使用。
到现在。村庄的匠人已经成为发明家了。他将基本的机械原理应用在复杂的工具当中,这些工具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机器。这些工具在中东成为一个传统:例如弓形梭,那是将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的早期方案。在这里,将一根绳索绕在一个木鼓上,然后把绳子的两头固定在像小提琴一样的弓上。将要加工的木头固定在鼓上,来回拉动弓就可以转动木头,因此,绳子会转动带着木头的术鼓,然后通过一把凿子在上面刻纹。这种结合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了,但我1945年在英国还看到一些吉普赛人用这种方法制作木椅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