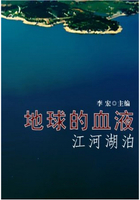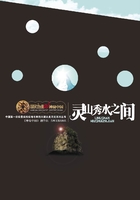《科学进化史》第一稿大纲于1969年7月完成,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人类的攀升》也于1972年12月拍摄完成。
规模如此巨大的一项工程,自然是十分激动人心的,但也是绝非轻易就能动手干的。它要求我们鼓起自己的最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对于这些要求,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是做到了,并且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做到了。同时,我把自己业已开始的许多研究工作推后了。在此我想解释的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我这么做的。
在过去的20年中,科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从物理科学转向了生命科学。结果,科学越来越接近对人本身的研究了。但是有兴趣的观众很少意识到,这在改变经科学塑造而成的人类形象方面,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我本是一个学物理的人,后来却变成了一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中年出现的几次幸运的机会带我进入生命科学的话,我也许同样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一些变化。我有幸在一辈子的时间里进人了科学的两大最有生命力的领域,因此,我也欠下了一笔债务;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欠谁的。但是我构思了《科学进化史》这本书,就算是对他们的回报吧。
英国广播公司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写一写科学的发展,用一系列电视节目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便符合洛德·克拉克就人类文明制作的节目。电视从多个方面来看都是极令人赞叹的展示方法:能够对人的眼睛造成快速有力的冲击,可以让观众对所描述的地点与过程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并且形成足够强的对话感,让他明白他所目击的一切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人们采取的行动。上述几个好处当中,在我看来最好的一个就是最后一条。考虑再三之后,我发现以电视散文的形式把个人的思想史表现出来是最合适不过了的。我这里的意思是说,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和特别意义上的科学并非由抽象概念构成的,而是由人为的思想构成,从最开始到现代以及特殊意义上的模式都是如此。因此,必须首先说明揭开自然奥秘的基础概念,因为它们最早诞生于人类基本和特有的天赋,并出现于人类最简朴的文化当中。而科学的发展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与人类纠缠在一起,所以也一定要以同样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发现是由人而不仅仅是思想进行的,因此这些发现是活的,而且带有个性。如果不利用电视把这些思想变成具体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浪费。
思想的揭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隐秘和个人的行为,因此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电视与书籍的共同点。电视跟讲演或电影不一样,它不直接面对一个人群。它表述的对象是一个房间里的两三个人,就如同面对面谈话一样,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单边的对话;就如同书籍一样,但它又有家常或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意味。在我看来,因为陶醉在知识的哲学潜流中,那是电视给人的最有吸引力的礼物,而通过电视,它极有可能在以后变成跟书本一样具有说服力的知识力量。
除此之外,书籍还有另外一个自由:它不受时间永不回头的令人遗憾的限制,而任何一种口头的语言都有这样的缺点。读者可以做观众和听众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以停下来,可以考虑问题,可以把书翻回去,可以重新看一遍作者的论据,把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拿来比较,而且从总体上讲,还能够欣赏证据的细微之处,但又不会为细节所分心。只要有可能,我本人经常是利用这种更休闲的思维长征方式,总能够把电视屏幕上现在说的一些话写到纸上去。对已经说过的话进行的大量研究,最终会牵动很多联系和奇异之处。而在本书中若不捕捉住这样丰富的内容,那可真是一件憾事。的确,我本想做得更多一些,并把细节的文本与背景材料与作为这些材料的基础的引言交织在一起。然而,如果真像那样做的话,就会使本书成为学生用书,而不是一本给普通的读者看的书。
撰写电视文本时,我因为两个原因而严格遵照口语的习惯行事。其一,我希望将思想的自发性保留在口语当中,这是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尽一切力量努力培养的。(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在任何时候都尽量选择那些在我面前看来跟在读者面前看来一样新鲜的地方。)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同样也希望保护论点的自发性。口头的论点不那么正式,但具有启发作用;它能把事物最核心的部分挑出来,并以最关键和新鲜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使解决方案有一个方向和线条,这样,尽管经过了简化,但其逻辑仍然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种论点的哲学形式是科学的基础,而不能允许任何东西使其隐晦难懂。
这些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比科学领域更广泛一些,我本不应该称其为《科学进化史》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里不得不考虑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的其他方面的进步。我在这里的理想跟在其他书中的理想是一样的,即:为20世纪创立一门哲学,而且必须是一体的。跟那些书一样,这个系列同样展示出的是一门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是一门自然的哲学而不是科学。它的主题是过去称为自然哲学的现代版。在我看来,我们今日处在更好的一种思维框架里,可以孕育出与过去300年来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尽相同的一门自然哲学。这是因为,最近在人类生活学方面的发现成果,给科学思想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也就是从普遍走向个别的转移,这是自文艺复兴打开了通往自然世界的大门以来的第一次。
如果没有人性,就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也不可能有一门像样的科学。我希望这种确认感能够在本书里体现出来。对我来说,在对自然的理解过程当中,是把对人性的理解当作自己的目标,也把处在自然之内的人类的处境当作自己的目标。
要在这个系列的篇幅内表现对于自然的看法,它跟一场探险活动一样属于一项实验,而且我对使这两种活动成为可能的那些人充满感激之情。我首先欠下了索尔克生物研究学院的债,该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就人类特殊性进行的研究工作,并给了我一年的公休假,让我参与拍摄这些电视节目。我还特别感谢英国广播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奥伯雷·辛格,他设计了这个庞大的主题,在我动笔之前一直催促了两年。
参与并支持本书工作的人不计其数,容我在此一并致谢。
雅·布伦诺新基
1973年8月于
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