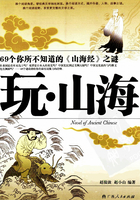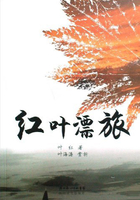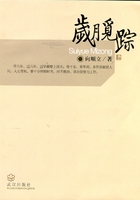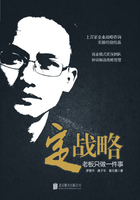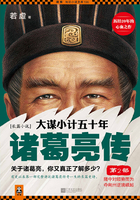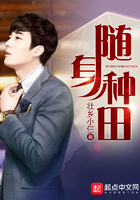这是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种种惨状,另外还有灾民之间仗义互救的感人场景,在熊熊大火的无情烧灼之下,这一切行动虽然收效甚微,却富有感天动地的悲壮情味,作者由此把题目中一个“哀”字落到了实处。汪中此文用笔细腻,描绘逼真,既有夸张之笔,又有含蓄之致,把描述和抒情融为一体,可谓“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同六朝骈文中的抒情名篇大有神似之处。汪中写出这样一篇精彩文章的时候,竟然还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他的老师、著名学者杭世骏读到了汪中的这篇文章,非常赞赏,还专门为此文写了序,称赞它说:“采遗制于《大招》,激哀音于变徵,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
三、近代散文:惊雷响处闪新光
乾隆统治的六十年,号称盛世,然而盛世之下的危机,在乾隆后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很多官员贪污腐败到惊人的程度,和珅就是典型的代表;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农民在重重盘剥之下无法维持生计,如果遇上灾荒,只能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的边缘。阶级对立越来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白莲教等民间组织的反抗行动让朝廷大费心机。到了嘉庆、道光时代,危机重重,愈演愈烈,破败的局面已经让大清国的皇帝和官僚们难以收拾。这个时候西方各国却相继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实力飞速发展,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到处寻找海外殖民地。地域广大的中国自然被他们看成一块大有油水的肥肉,于是很快就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大清帝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清朝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统治的力度,压制言论,禁锢思想,文字狱有增无减,希望通过这些手段阻止一切变革。全国一片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此后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虽然都属于正义的自卫性质,却多半以失败告终。清朝的统治者在长期的封闭之下,习惯了自高自大,竟然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一旦被迫打开国门,就变得束手无策,只好任人宰割。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早已出现了变革的呼声,龚自珍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率先觉醒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用他的诗歌和散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表现出昂扬的战斗精神。虽然在腐朽势力的残酷打压面前,他的呼声还显得那么孤单,那么微弱,却是掀起近代思想世界燎原巨焰的星星之火。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曾经担任过内阁中书、宗人府和礼部主事等职,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的时候病死在江苏,以一个地位卑微的下品京官终其一生。龚自珍明显受到明代中后期张扬个性思潮的影响,反对压制和束缚,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倾向。他虽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却极富政治敏感性,在清王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深刻觉察到这个帝国危机四伏和即将全面崩溃的命运。如果就生存条件说,龚自珍远比一般百姓优越,但他在精神和思想上却是一个非常苦闷的人,他的命运是很悲苦的,因为他是那个没落社会中极为罕见的觉醒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联结在一起,在万马齐喑的时候,他在孤独地摇旗呐喊(图2-14)。
龚自珍是个思想上早熟的人,在二十五岁以前,他已经写出《明良论》、《尊隐》、《乙丙之际箸议》等富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揭露时弊,呼吁变革,闪烁着耀眼的锋芒。正因为耀眼,所以特别容易引起腐朽势力的忌讳,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龚自珍在中年以后,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加上生活阅历的增长,文采锋芒收敛了不少。不过无论给他怎样的打击,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绝不会改变他见识的深刻和锐利,只是在文章的风格上变得更加深沉,更加讲究迂回曲折的斗争策略。《病梅馆记》就是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文章讽刺病态文人为了自己矫揉造作的特殊癖好,刻意将健康的梅花加以芟剪、扭曲,造成“病梅”。文人画士以扭曲为美,龚自珍却认为是一种病态。实际上是采用比兴的手法,拿梅花来作比喻,说明一个走向没落的社会对自然人性的种种压迫和扭曲。他誓言要解开所有“病梅”的束缚,让其恢复自然的生态,循着本性自由生长。文章首先描写梅花的病态道:
江宁之龙蹯,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一般老百姓没有扭曲梅花的心思,也没有这个能力,作孽的正是那些有知识又有特殊癖好的文化人。这就是在暗喻,摧残人性的正是那些社会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接下来,作者写下自己治疗病梅的过程,以此申明对制造病梅者的抗议,实际上就是表达了改造社会制度、恢复正常人性的决心:
予购三百瓫,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瓫,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又广贮江宁、苏州、杭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泣之三日”,可见痛惜病梅之深切;“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可见抗争、改造现实的愿望之强烈。通过《病梅馆记》,可以窥见龚自珍散文的核心思想,那就是揭露专制统治的腐朽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表达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抗争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龚自珍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重新唤起了经世致用的文风,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志在经邦济世,深切地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虽然龚自珍的散文中还经常出现儒家经义内容,形式上还没有脱离骈散相间的句法,仍然带有古典散文的特质,没有超越传统散文的范围,但他首先开启了晚清的经世文派,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冯桂芬、王韬等人继之而起,逐渐打破了“古文辞门径”的束缚,也不再把“代圣人立言”作为为文的宗旨,这是古典散文转化为现代散文的关键一步。龚自珍短暂的一生,恰好结束在中英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无数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把无数具有进步思想和高度觉悟的知识分子从迷茫中唤醒,他们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放眼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吹变法图强,同时也一步步把散文向通俗化和社会化推进。龚自珍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交会点上,世界大潮风起云涌,一个剧变的时代终于到来。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创立一种半文半白的“报章体”、“新民体”散文,龚自珍的散文对这种新的散文体式的形成起到了启迪作用。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交上一直遭受挫折和失败。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败给日本,全国要求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终于引发了戊戌年(1898)的维新变法运动。领导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戊戌变法前夕,形势发展极其迅速,思想上出现的都是新问题、新内容,要表达这些东西,传统的古文、骈文都难以胜任。所以新文体的出现,梁启超文章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时势使然,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催生出来的。
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那里跟随康有为学习,后来又追随他参加政治活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他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要求满清朝廷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来又赞助康有为创立强学会,次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这时期的文章以《变法通议》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倡导民权。这些活动也激发梁启超决心把文学变成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不仅成为散文革新的倡导者,也成为诗歌、小说、戏曲革新的全面倡导者,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流亡日本的经历说: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自从清代中期以后,散文领域就为桐城派古文所领导。桐城派所建立的古文写作规范,虽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长此以往,就难免限制散文的活力。所谓新文体,就是一种打破古文规矩,扩大用词范围,不避俚语、韵语、外国语法的新型文章。它平易明晰,读者容易理解,也容易效法;它的文笔又带有情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便于描述新事物,表达新思想,容易对维新变法起到一种鼓舞和宣传动员的作用,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比如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有一段说: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斯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这种文体其实并非梁启超无端的发明,它的渊源是中国古代佛教经典的翻译文体,这种文体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层层铺开,不避相似逻辑结构的频繁重复,能够起到强调的作用,艺术上也颇显气势。特别是类似“何以故?以……故”之类的设问句式,在汉译佛经典籍中极为常见。所谓报章文体,很多情况下都是那边等着出报纸,这边才开始动手写文章,如果按照一般文章一板一眼的写法,多半会来不及交稿,这种佛经翻译文体里面相同文字的高重复率,非常适合这种应急文章的写作。梁启超在佛教经典上造诣颇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特殊文体的影响。所以无论对这种文体的出现有多么冠冕堂皇的解释,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新闻生产的实际环境里面去考察、研究。梁启超自己说:“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除了仓促草率、来不及构思之外,报章文体对这种语句多有重复的特点的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清代桐城文派的奠基人方苞主张写文章要“雅洁”,首先就要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梁启超的新文体把这些古文禁忌一扫而空,熔合多种文体于一炉,在散行的古文中,夹入许多整齐的类似八股文的排比句、骈文的对偶句。而带有浓重异国语法色彩的文句,更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大胆突破。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为躲避清廷的追捕逃亡日本。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他同日本人交往还需要借助笔谈。随后的几个月他集中学习了日文,达到可以随意阅读书报的程度。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梁启超开始大量撰写文章,日本文体的影响从此显现出来。不过当时刻意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比如在1899年6月,梁启超应日本某政党机关报《大帝国》的征文,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的“撰者自志”中就明确指出该文仿效了日本文体。比如“欧人中国分割之议”,按照汉语语法,应该是“分割中国”,但日文语法中宾语放在动词之前,所以会这样表达。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
梁启超的散文,在同时代人的眼里就已经树立起极高的威望。近代学者钱基博在1930年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
如果说龚自珍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改变了古典散文的路数,那么梁启超的新文体则进而在形式上打破了古文的传统家法。借助广泛发行的报章的力量,新文体的影响更加广阔、深远。从龚自珍到梁启超,一代一代的思想家兼散文家正在逐步瓦解着中国古典散文的旧规范。
时代的脚步很快迈进了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变革大潮开始荡涤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散文领域更是发生了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新民体文章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接踵而起,白话文应运而生,上千年言、文分离的时代宣告结束,言、文合一的新时代从此开启,中国古典散文舞台上的种种精彩和辉煌,到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