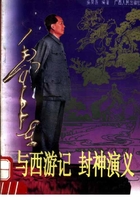公元前221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指挥着秦国威武之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他和他的儿子胡亥把暴政用过了头,本来企望自己的帝国能够万代相传,没想到只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偌大一个秦帝国就在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继之而起的,是由刘邦领导建立的西汉王朝。随着国家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结束了,热闹一时的诸子百家已经没有了争鸣的舞台,诸子散文的黄金时代因此告一段落。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阶段,一种吮吸着《诗经》、楚辞这先秦时代两大文学源头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文体——赋,从此粉墨登场。它包罗万象,气势恢弘,俨然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角;它生命顽强,深受喜爱,经历魏晋六朝和唐、宋、元、明,直至清代,常变常新,多姿多彩,算得上是中国散文这万园之园中的一处奇异景观。
一、在铺陈中娓娓道来
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龙》中专门开辟了一篇《诠赋》,对赋这种文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诠赋》开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就一下抓住了这种文体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赋,就是通过铺叙、描写以见文采,来形容事物、抒发情感。刘勰又说,赋是由《诗经》和楚辞两个渊源发展而来的,即所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赋,就其本义而言,乃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古人有所谓《诗经》“六义”的说法,见于《周礼·春官》和《毛诗序》,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诗经》中的内容按照体裁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类,国风一般是各地方的歌谣,而雅、颂则是朝廷宗庙的歌诗、舞诗。发展到后来“风”便有了教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则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而“赋”就是铺陈和直接叙事、言情的意思;“比”者比喻,用别的事物来比喻想要描写的事物;“兴”有联想的意思,触景生情,由一种事物引起、感发所要抒发的感情。这是《诗经》中具有标志性的三种基本艺术表现手法。“赋”的作用更为基础,可以描写,可以抒情,运用最为广泛和普遍。
汉代作家一方面模拟楚辞,一方面把《诗经》中用于铺叙的“赋”法变成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表现方法,逐渐扩大篇幅,句子也明显散文化了,有了自己特殊的描写对象,汉代大赋就形成了。
散文化的关键一步,是去掉配乐,不再演唱。《诗经》中的歌谣和“楚辞”里面的大部分篇章,都是配合着音乐来演唱的,汉大赋就不同了,它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不歌而诵”,只用于朗诵和阅读,而不去歌唱。这个特点对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篇幅大大扩展了,《子虚赋》、《上林赋》加起来3523个字,《两都赋》4702个字,《二京赋》7696个字,字数不断地增加,若是继续保持演唱的方式,非得把歌手给累坏了不可;其次是表现的范围扩大了,因为有足够大的篇幅作保证,因此汉赋的内容几乎能够包罗万象;再一个,这么大的篇幅都用来抒情就比较累,用于描写和铺叙就容易协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特殊表现手法。屈原的《离骚》篇幅就比较长,将近两千五百字,虽然它总体上是用来抒情的,可是主要的表现手法就是描写和铺叙,把情感寄托在这种叙写当中。汉赋作家干脆抛弃了抒发情感的成分,完全用充满感官刺激和抑扬顿挫的铺叙来弥补没有音乐配合的不足。
汉大赋几乎不抒发个人的感情,它追求气势,语言夸饰,内容简直无所不包。天文、地理、鸟兽虫鱼,举凡当时世上所能见到的物象,大赋作家都想囊括进去。这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汉帝国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经相当富庶,经济的繁荣和疆土的广大,可以说前所未有。这大大增强了当时人的自信。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自然容易引发文人的激情,为了迎合帝王的爱好,他们更要用赋来歌颂,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歌颂帝国的强大声威,凡是赋里面所描写的东西,无不要表现它的大,体积上要广阔雄伟,色彩上要光彩夺目,整体上就显示出一种崇高、巨丽的美。这是那个时代共同的艺术追求。再者,汉武帝开疆拓土,通过一系列战争开通了通往西域和西南方向的交通要道,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交流频繁起来,西方的珍奇之物不断进入长安,进入中原,大大开阔了士人的眼界,于是他们把从西方进来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统统写进大赋,简直像是开了博物馆,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目的,仍然不外乎润色帝王的雄才大略,汉王朝的无所不有。
二、用文章来修饰政治
本来大赋铺张的目的在于讽谏,要阻止帝王不合理的政治举动,可是铺张过度,赋的作用就变质了,反倒助长了帝王过分的欲望。汉武帝喜好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司马相如写了《大人赋》去劝谏,但他的赋用了多半的篇幅去描写神仙的种种美丽生活,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明了劝阻的意思,结果适得其反,没有起到劝阻的作用,反倒弄得汉武帝飘飘然,更加沉醉于化为神仙的美梦了。其实这并不是司马相如的错,大赋就是这么个写法。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与“辞人”的不同,就是前者具备儒家的讽谏精神。失去了这个精神,铺张就成了漫无主旨的诙谐逗趣和文字游戏。扬雄早年热衷于作赋,晚年却笑话它是“壮夫不为”的儿戏,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初奠定汉代大赋基本格局的,是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作家枚乘所写的《七发》。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他给吴王刘濞做过郎中。吴王怨恨朝廷,策划谋反,枚乘曾经上书劝阻,可惜吴王不听。枚乘很聪明,他怕吴王谋反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跑到梁孝王那里去了。他心地还是很好的,始终没有忘记吴王,后来刘濞发兵谋反之后,枚乘又一次给他写信,劝他不要做傻事,吴王刚愎自用,还是不听,结果失败被杀。枚乘就因为这两封信出了名。景帝让他做弘农都尉,可是枚乘在诸侯王门下时间比较长,习惯了那里闲散的生活,不太喜欢做地方官,就借口有病辞了官,又跑到梁孝王那里。梁孝王好文艺,他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辞赋作家,形成了一个创作群,枚乘是里面水平最高的。梁孝王死了以后,枚乘就回了老家淮阴。汉武帝即位,他喜欢辞赋,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枚乘的大名,于是让人用安车蒲轮——这是当时比较高档舒适的车——去请枚乘到长安,可是枚乘年纪太大,就死在路上了。
《七发》首先说楚太子有病,久治不愈。吴客前往探病,找到了病根,指出太子的病是由日夜无度的纵欲和享乐造成的。这病就是让神医扁鹊、巫咸来治也难以奏效,只有请博学多闻的君子经常给予启发、诱导,改变贪恋享乐的情志,才能得以痊愈。然后,赋的主要部分,都用来描绘太子享乐生活的境界:用最好的琴,请最好的琴师,演奏天下最美的音乐;选用天下最上乘的肉和菜,烹调味道最美的菜肴;乘坐坚车宝马,让最著名的勇士驾车,同人比快争胜;登上高台,置酒高会,同时有高才文人写作美文,又有美女在身旁侍奉。这些都是太子平日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太子屡见不鲜,听来听去,没有丝毫兴趣。接着,吴客又给太子描述宫墙之外的游猎活动,场面之宏大、景象之热烈都是太子很少经历的;又讲述江边观涛的宏伟景观,较之游猎更加激动人心。说着说着,太子有了兴趣,阳气出现在眉宇之间,可惜此时身体有病,还不能参与其中。最后,吴客建议延请博学高人为太子讲述天下之道、万物之理,太子听了,竟然霍然病愈。
《七发》采用了对话的形式来组织整篇文章。它的写作目的在于劝诫,可主要的工夫都用在了铺叙宏大的场面上,而且气氛层层递进,逐渐推至高潮。这些特点,都为后来的大赋所继承。枚乘的创造天才在散文史上是应当给予充分敬意的。可惜他多少有些生不逢时,文帝、景帝都是提倡俭朴和节约的君主,对文学,特别是辞赋没有多少兴趣,枚乘的文采只有在藩王那里发挥,一旦等到喜好辞赋的汉武帝掌握权力,枚乘却老病而死了。否则,他在汉武帝时代中央的文学侍从之臣里面也会是最杰出的作家,会有更好的条件从事辞赋创作,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汉武帝当政时期,是大赋的黄金时代。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到长安,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都因为文辞出众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可谓人才济济。东汉班固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还透露着无限的向往和羡慕。他在《两都赋序》中说,武帝、宣帝时代,“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儿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是大赋作家群星璀璨、扬眉吐气的时代,是汉代盛世景象的最动人一幕。司马相如的经历在这群作家里面最为典型,水平最为杰出,担当着一代文坛的主要角色。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因为仰慕战国名士蔺相如的为人,改名叫相如。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他本不愿意做这个官,景帝又不喜欢辞赋,难免有些不得意。后来梁孝王进京朝见,司马相如见到了梁孝王的门客邹阳、枚乘、庄忌等人,都是些写作文章、辞赋的高手,很合得来,相如便借口有病辞了官,也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门客。当时的辞赋专家多集中在东方藩王的门下,梁孝王、淮南王那里都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对推动辞赋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孝王死后,相如回到老家成都,穷得一无所有,还找不到谋生的职业,就去投奔好友——临邛的地方长官王吉。王吉对相如极为尊重,临邛巨富卓王孙、程郑大概因为王吉的关系,邀请相如吃饭。相如没来,王吉就不敢动筷子,这让两个大财主很惊讶。席间,在王吉的恳请之下,相如弹唱了两首曲子,倾动四座,更倾动了卓王孙守寡在家的女儿卓文君。相如本来风度翩翩,儒雅多情,文君在相如唱歌时隔窗偷看,不禁春心荡漾,爱上了他。相如也心有灵犀,弹琴时有意挑引文君,真可谓两情相悦,一拍即合。卓文君思想比较“前卫”,当晚主动跑到相如家里投怀送抱,就此结为连理,真个成了琴瑟和鸣。两人一起从临邛到了成都,相如一心当作家,不擅长赚钱养家,终于穷得过不下去。卓王孙为此大发雷霆道:“我这个闺女忒不争气了!我虽说不忍心杀了她,但她也甭想得到我一分钱!”
卓王孙确实很有钱,所以动辄拿“钱”说事儿。卓氏从战国时代起,就是有名的富户。其祖先本是赵国人,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当时的移民都贿赂官僚,希望留在近便的地方,唯独卓氏眼光长远,躲开人多地少之处,自愿到偏远的临邛,靠着冶铁很快发家致富,有家僮(奴隶)近千,还拥有大量的田地、山林、池沼,平时以射猎取乐,财产、享受都可以同帝王相比。富可敌国的卓王孙想对女儿实行“经济制裁”,却没想到女儿女婿技高一筹,让他赔了银子还要丢人。
相如夫妻卖了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酒馆。卓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着形如牛鼻子的短裤,同佣人们混在一起刷盘子,他们大概是故意给老爷子找难堪。果然,卓王孙觉得丢人丢得不得了,连门都不敢出。亲戚们劝他说:“你有儿有女,又不缺钱,文君同司马相如已然生米煮成熟饭,这年轻人虽说穷了点,人还蛮不错嘛,又是父母官的朋友,你何苦让他们这么为难呢?”卓王孙也觉得丢不起这份儿人,无奈之下,干脆把上百个家僮、百万资产,连同给文君准备的嫁妆,一起送给了小两口儿。相如夫妻拿了钱,立马儿赶回成都,买田置地,摇身成了大款。
这故事其实同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大有关系。他的赋铺张华丽,大气磅礴,如果他一直不名一文,穷得吃不饱、穿不暖,怕是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写赋,更写不出那种气势。后世那么多穷酸潦倒的文人,写了无数穷愁牢骚之词,艺术上自然成就非凡,可是同司马相如辞赋的情调比起来,那真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时代不同、内容有别之外,个人经济基础的作用绝对不能小看。
司马相如学识渊博,他本身就是个语言文字学家,写过《凡将篇》,是一本与字典相似的小书。他的赋使用文字范围极广,奇字僻字满纸都是,即便在当时也很少有人能在不借助字典的情况下顺顺当当地把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通读下来。
这两篇大赋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子虚盛称楚王游猎云梦,场景极为壮观;乌有先生进而夸耀齐王游猎的盛况,竟然能够“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曾不芥蒂”;最后亡是公又极力铺张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阔气派,更是远非楚王、齐王所能比拟,以此说明天子威严压倒一切,相比之下,诸侯之事微不足道。赋中的文辞就像是起了七级台风的大海,层层递进,一浪压倒一浪,身临其境,真有些惊世骇俗的效果。今天的读者乍看起来,就像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吹牛,不过作者却是真心实意地夸:“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排山倒海的气势里面,其实无不表露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对天下一统的真诚向往,还有对帝王权威的无限崇拜。这种作品,今天读起来多半读者会感觉枯燥乏味,但在当时,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是乐此不疲。我们如果能够想象,在春秋战国长久的战乱和贫敝之后,又经历了数十年倡导黄老思想的知足保和与休养生息,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繁华世界,也就不难领会汉大赋中所洋溢着的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