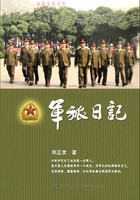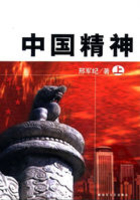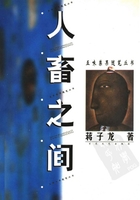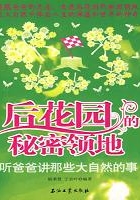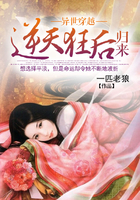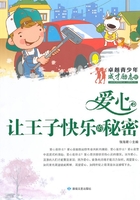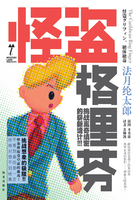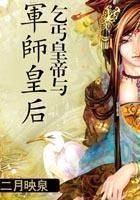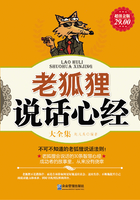他的那些“主人公”真是包罗万象,奇形怪状,尽是些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世上本来没有大鹏,大鹏就是他编造出来的,而且还随着海水的巨涛从北到南、由下而上地飞越三千里;在他的书里,鳖和青蛙还可以对话;蜗牛的触角上竟然发生了两个国家的战争,而且居然“伏尸百万”!故事虽然离奇,形象尽管古怪,道理却往往能够惊世骇俗。庄子的文笔,也如同他的精神那样不受拘束,天上地下,时真时幻,忽起忽落,摇曳多姿。有的评论家说庄子的文章就像是微风吹拂在水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纹理。以苏东坡之学养深厚、多才多艺,眼界自然极高,但他对庄子的文章佩服得实在是五体投地。他说:“我原来心里有些朦胧的想法,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读到《庄子》,才感觉到他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苏东坡写文章,经常会用到《庄子》书中的典故,而且他一生被卷在政治风波里上下跌宕,受尽了打击和折磨,曾经被贬到当时还十分荒凉的海南岛,这说明他的政敌希望置他于死地,可是他后来竟然健康地回到北方,《庄子》的哲学无疑帮了大忙。
庄子看上去真是潇洒,超脱得无可比拟,不过庄子的内心实在又是愤激得不得了。他对世上荒谬不合理的事看得太多、太敏感,比一般人体会得深刻得多。他说,当时偷了金钩的人要判死刑,可是偷盗了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儒家喜欢讲礼乐、仁义,很多人不过是拿这些东西作幌子,尽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强盗们让人骂得一钱不值,却还有些真道义。他大骂那些追求富贵的人是钻在裤裆里头的虱子,挖苦曹商的发迹是因为替秦王舔了痔疮,还讽刺满口仁义诗礼的儒生尽是些个挖墓盗宝的贼人。正是因为世上的很多是非都是颠倒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都是虚假的,庄子才在愤激之下主张泯灭是非;正因为他深切感觉到真实世界的荒谬,才试图用想象中的荒谬说明他自己的真理。庄子散文了不起的艺术成就由此才得以生发出来。
庄子在根本上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所以前人把他们都叫做“道家”,但庄子和老子的文章风格却有所不同。老子的议论比较抽象,只是告诉你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庄子则很少抽象的东西,他总是靠想象、幻想来构思、编造一些小故事,把他要说的道理融化在这些具体可感的故事和形象里,显得趣味横生。
庄子家住在齐、楚和三晋交界的地方,生活非常贫穷,他同下层平民多有接触,在学问上广收博采,所以能够从平民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差异,看透富贵之人的虚伪和吝啬。《外物》里面讲了庄子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向监河侯借钱以解燃眉之急,监河侯表面上大方,慷慨答应借给庄子三百金,但是要等到发了工资以后,这明显是在糊弄庄子。庄子回答的巧妙,在于并不直接抱怨,而是讲个小故事,把监河侯的为人放在故事里面加以讽刺:小鱼困在车辙里面的一汪水里,将要困死,向路过的庄子求救,庄子说我到吴越国把西江之水给你引来好不好?小鱼大怒道:“我现在只要斗升之水就能活命,等你把西江之水引来,我早就成了鱼干了!”这故事当然是庄子编造出来的,但编造得那么贴切、幽默,富有情趣,把人性中的丑恶给放大了,你不能不佩服庄子揭露现实的深刻。
同老子一样,庄子特别看重自然之道,认为朴素的美才是天下无可比拟的真美,所以他反对人为的雕琢和虚伪的修饰,主张摆脱一切世俗的教条,抛弃名利权势的束缚,尽情抒发真实的心灵感受。《应帝王》里有个“浑沌开窍”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就是“自然”的代表,本来没有什么“窍”,这是他的自然状态,可倏和忽偏偏要多此一举,硬要给他凿开七窍,虽然出于好心,反倒把浑沌给害死了。办事违反自然规律,必然事与愿违,遭到规律的惩罚。这正是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发挥和具体化。
庄子的散文,就像庄子的哲学一样,浑浩博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文人去阅读、研究和回味。我们虽然不知道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是无论经过多少年,总是不乏慧心的读者,通过阅读庄子的散文,去贴近他的心灵,去体悟战国时代的那一份飘逸和潇洒。
四、《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逻辑论辩的不祧之祖
随着诸子争鸣的开展,论辩之风越来越盛,孟子就得了“好辩”之名。荀子提出“君子必辩”的口号,他的书中《非相》、《正名》、《解蔽》等篇,都花了不少工夫探索思维规律、逻辑方法和辩论艺术,追求语言的形式美,并在这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墨子名字叫做墨翟,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最初学习儒术,后来自开宗派,门徒众多,到了战国,这个学派同儒家并称“显学”,就是最为人所重视的学问(图2-5)。墨子坚决否定文采,主张取消一切音乐歌舞,认为这些都是奢侈浪费的举动,劳民伤财,耽误政治和生产。当时不少上层人物的享乐生活非常过分,建立在广大民众的痛苦和血泪之上,墨子对这些现象尤其敏感,所以有这样极端的主张。《墨子》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集中探讨辩论方法,被称为“墨辩”。《墨子》对假设、比拟、譬喻、类推等论说方法有专门的具体分析。他还在《非命》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自己解释说: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用今天的话说,“三表”就是文章要有历史根据,要重视结合现实,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实际生活的检验。这是判断事物真假的三条标准,也是论文写作的三条标准。荀子的论辩方法就从“墨辩”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战国初年的某一天,又有一位老师,带着他的徒弟,乘着牛车,走在从齐国通向宋国的泥泞道路上。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对天下大势和治国方略颇有一套见解,他前几天曾经把这套见解推荐给齐王,齐王对他深表尊重,接待如同上宾,却没有接受他的“礼物”。旅途的劳顿,丝毫没有削弱他的雄心壮志,他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后来又游说了宋、鲁、滕、梁等国,他虽然舌灿莲花,雄辩滔滔,却屡经挫折,最后还是像孔子那样回到故国,以授徒、著书终老于家乡。这就是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图2-6)。他是战国初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传说孟子的母亲是一位特别擅长儿童教育的专家,她知道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巨大影响,所以为了给幼年的孟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曾经不厌其烦地搬过三次家。“孟母三迁”的故事后来成了成功家庭教育的典范。当我们提起孟子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母亲。
孟子一生以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自许,似乎远比孔子自信。司马迁说,当时天下诸侯都忙于混战和杀戮,在他们眼里,谁擅长打仗和争夺利益,谁才是人才;孟子张口闭口不离尧、舜、禹,不离仁政,到处宣扬什么人性本善,尽跟人家拧着劲儿,所以根本没人理他那一套。从这一点说,孟子还确实像是孔子的“翻版”。孟子和孔子一样,生前到处碰壁,被各国君主所轻视和抛弃,可是一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战火纷飞和秦朝的暴政,到了统一和平的西汉、人心都巴望着安定的时候,孔、孟的学说便遇着了生机,被学者们重新给予解释,接着就受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重视,将它捧上独尊的地位,这地位竟然一下维持了两千年,影响之巨大、深远,恐怕是孔、孟本人始料未及的吧!《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孟子》里的文章则几乎都是孟子本人所写,他的徒弟万章、公孙丑在编书时做过助手。
孟子大概在生前就得了“好辩”的名声,而且在当时似乎还不是什么好名声,对此,孟子无奈地说:“我难道好辩吗?我实在是不得已啊!”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们只要翻翻《孟子》原文,就不难发现别人说他“好辩”,其实真的没有冤枉他。不过我们这样说,却并不是要贬低孟子的辩论,而是发自内心地表示钦佩和尊重,因为他的辩论里充满了气势,充分表现着他道德修养的圆满和自信,又极讲究技巧,艺术水准非同一般,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滕文公》记载孟子同陈相的一段对话,孟子上来就问陈相:“许子必以种粟而后食乎?”“必织布然后衣乎?”是啊,你想啊,许行当然不能自己亲自种了小米才可吃饭,自己织布才有衣服穿,当然很多事都不可能不仰仗他人,由此可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进而引古证今,慷慨陈词,强调了社会分工的必要,以此来说明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观点。当然,孟子的结论未必正确,但他善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每一步推断都会让对方觉得无懈可击,加上气势磅礴,滔滔不绝,特别容易让人折服。又如《告子》中有一段孟子的议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真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令人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但是音节铿锵,意义连贯,很多人竟然特别轻松地就把它给背诵下来了。难怪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说,孟子的文章,就像是熟练的舵手始终把船保持在河流中最有利的位置,借着水力飞速前进;那些外行费力不少却寸步难行,自然相形见绌。
孟子曾经说,你如果打算说服王公大人,你首先得藐视他。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在辩论中无疑就多了几分胜算,容易处在主动、有利的地位。其实,战国时代,很多游士就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诸侯王公讨生活,他们的很多说辞未必合理,并不一定可行,却颇有煽动性,搞得对方意乱神迷,崇拜不已,迅即主动就范。他们很可能就是把孟子的论辩文章当中这种行文艺术,变成了煽风点火、混饭吃的“忽悠”经验。这大概也是孟子没有想到的事吧。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但他的思想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图2-7)。他写过一篇《非十二子》,对儒、墨、名、法各家学者都有所批评,并激烈抨击“子思、孟轲之罪”。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学术总要发展、变化,儒家的继承人本身对孔子的思想就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又会结合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不断修正学说的内容,儒家思想当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同最初的面貌产生距离。荀子对孔子以后儒家代表人物的批评,其实也不过代表了他自己一家的看法而已。他对孟子学说的意见很大,比如孟子讲“性善”,认为人性本善,但荀子就讲“性恶”,认为人性本恶,那善的一面都是通过人为修饰出来的,都是假的。又如孟子讲天命,荀子就认为万物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不是因为有了尧帝这样的贤君才有了天地,天地也不会因为夏桀这样的昏君的出现而消失。他是很客观、很现实的,看重人为的重要性,相信人定胜天。
总起来说,战国后期,各种学说已经大略具备,荀子对其都有所吸收,所以他的思想比较驳杂,有集大成的味道。同孔孟相比,荀子思想偏于理性,更切合当时的实际,后来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不是偶然的。荀子的散文畅达善辩,条分缕析,却不像《孟子》那样滔滔雄辩、气势磅礴;他说理透彻,但多是单刀直入,不像庄子那样想象瑰丽,汪洋恣肆;他的语言已经相当犀利甚至有些尖刻,不像孔子和老子的语言那样优游、温和。他能够把每一篇文章都分成若干论辩专题,相当有条理,层次感很强,这标志着论辩艺术的进步。
荀子在中年的时候,曾经在齐国首都临淄主持过“稷下学宫”,这是齐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代表着整个战国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晚年的荀子,到楚国做了兰陵令,地点大致在今天山东苍山一带,后来就死在那里了。他模仿楚国民歌写了《成相篇》,是一种三言和七言混杂的歌谣,还写了《赋篇》,对后世辞赋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韩国人,在论辩方面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不过只是在著书方面,论口才韩非就不太好,因为他天生口吃。韩非的遭遇相当悲惨。他看着韩国在秦国的压制下一天不如一天,就给韩王上书,韩王没有理会他。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他效力。韩非在秦国备受重视,引起了李斯的嫉妒,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其为韩国宗室,未得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李斯逼其自杀。
韩非要求著书、立法都必须说得明白确实,通俗易懂,论说周详。他比较讨厌文学之士,所以自己写文章也不重文采。他的思想属于典型的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他的文章也如同他的思想,尖刻无情。《韩非子》中有《难言》和《说难》两篇,汲取了当时诸子纵横游说的经验,对论辩艺术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考虑得很细,强调在向君主展开游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君主能不能愉快地接受,惹得君主不高兴,脑袋搬了家,就是巧舌如簧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就像是传说中的龙,脖子下面有三尺逆鳞,也就是说这些鳞同一般的鳞正好方向相反,如果稍一疏忽,摸了逆鳞,就有性命之忧。这说明韩非不像其他辩论家那样,只顾着自己说,他还考虑到了听众的接受能力,这是韩非对论辩艺术的重大贡献。可惜他自己却连展开游说的机会都没能真正得到,幸好有他的书传下来,才让后人领略这位法家大师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