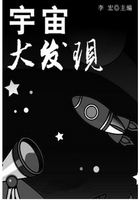接下来再谈中国散文的发展道路。遥远的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为其肇端,属初步形成期,就业已约略镌刻了先民们最早的情感波澜与心灵渴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期,诸子勃兴,涌现出主张各异的众多思想流派,却也造就着缤纷灿丽的不同风格面貌,遂一并凝结成为中国的文化—文学原典,垂范百代。秦至西汉,是中国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成熟时期,气势恢弘昂扬、词句华艳夸饰的大赋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的光辉。另一现象是,从秦及汉魏,于逐渐苏醒而趋强化的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刻意讲求对偶、用典、音调、辞藻而兼纳对称和谐之美和诗歌韵律的骈文;殆到六朝,骈文已独霸文坛,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章纯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尚。
中唐和北宋中期是中国散文的鼎盛阶段。它以“八大家”为标志,其间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在先,鼓吹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明白畅达的传统,振兴儒道;欧阳修、苏轼等则承继光扬于后,更具社会优势也取得更广泛的成就,从此散行文字的“古文”便确定了它再未被动摇的主流地位。明清两代的中国散文仍在变创中继续前行。晚明的“童心”、“真趣”说促发了形式自由、手法多样的小品文风行,它确也最适宜性灵意趣的表露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进入清代后期,近代传媒报章的发达,冲决开士大夫“雅”的观念,使古典散文语言转向大众化、通俗化,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状况。时势使然,随后便该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登场独胜了。
说起中国戏曲,历经千余年的孕育,产生过许多包含戏曲因素的艺术样式,至元杂剧始骤然耸作顶峰,形成高度繁盛的局面。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戏曲文学,就严格意义上,只是为戏曲演出所创作的剧本样式,其出现已经是元杂剧形成后的事情了。所以,在时间上比作为综合艺术表演形式的戏曲要晚许多,而且也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构组部分。至于另外结构部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当然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但是,戏曲文学却兼纳并取了它们的精华与诸多优长,故其开端便是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展露,同时昭示着俗文学大发展且成长为文学主流的新时代的到来。
元杂剧因以北方音乐曲调歌唱而称名“北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产品。当它盛行之际,原生江南本土的用南方音乐曲调演唱的“南戏”也已成熟,元亡后更是蔚然勃兴,后来即演化为“传奇”。明清两代便是戏曲文学的传奇兴盛时期,面貌已与元代迥然各异了。如果说,中国戏曲文学在元代还只是下层失意文士、书会才人们的创作专利,那么,明清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亦有意于此,甚至不少的皇亲贵戚、达官显宦乃及地方官员都多所染指。于是,戏曲由市井民间升堂入室,跻身庙堂艺术行列里;而戏曲文学也呈现出名家名作不同风格、流派的纷彩竞艳、众美汇集的盛况,并归纳出多种理论。总之,中国戏曲文学凭借它非常宏阔多元的视野,表现了十分广泛的题材内容。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有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又诸如英雄侠义、清官断案、爱情婚姻、伦理道德、世情风俗、神魔鬼怪等,不烦枚举。
关于中国小说,外在形式上就有文言与白话通俗、短篇与长篇之分,包括了神话、寓言、逸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可谓繁复纷杂,而且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三千余个春秋的洗礼,才逐步走向成熟,造就成那一派辉煌。先秦两汉的漫长时期,只是孕育、萌生并明确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内涵。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显现出其日益清晰的面貌和特色,初具规模,即含有“志怪”、“志人”二类的笔记小说。唐宋两代是重要的形成、演变时期。一是文言小说中“传奇”的勃兴,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小说的独立文学品格的完成与自身的高度成熟。二是出现在唐说经、俗讲基础上的白话小说,从此两大系统如春兰秋菊,各具不同的风貌情味,分流并驰。宋代白话小说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而以“话本”为最胜。
明和清代前期进入到中国小说的高潮极盛时期。明代白话小说的长篇章回与短篇皆堪称空前繁荣,前者的标志是作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体现着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俗人情等题材类型的小说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有“拟话本”的“三言”和“二拍”,显示了这方面的最好成绩。清代前期又是双峰屹立,《红楼梦》突起,高耸出白话小说再也无法超越的极巅,然后便逐渐走向衰落;《聊斋志异》自属文言小说继唐传奇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高潮,或许还更加灿烂多彩。其他再如《儒林外史》,它以众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长篇的特殊结构形式出现,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正式成形。清中期再至晚近,尽管数量繁多、流派纷呈,诸如狭邪、杂家、谴责等品类也间出杰作,然而,都不能解救中国小说日过中天之后业已无可挽转的倾颓走势,这情景恰似黄昏时节犹存的那抹晚霞斜晖,只供聊慰长夜的寂寥落寞而已。
最后言及史传文学。实际上,无论是采用前面诗歌、散文、戏曲文学、小说的传统四分法,抑或按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三分法,它都不能算做一种同等级的真正独立文体。若以宏通发展的目光去看,史传文学以历史为内涵,表现为文学的形式,是实虚交会,或者说兼纳文史两端于一身,并由文学和历史两方面互融衍生出来的准文体。这样一个跨界的边缘性质文体,竟又同时具载散文与小说的因素特征,而且它只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的生长、演进过程,生命轨迹既古老也相对短促。但史传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久长,虽然作为准文体的外在形式已经消歇了,但其内在艺术精神却始终活跃、融汇于后世文学的多个体裁样式之中,另有一部分质素则分流到史学里。要之,在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发展嬗变道路上,史传文学因其文体的特殊性,凸显出由混沌的不自觉而渐至自觉意识苏醒张扬的转化过程,这标本意义是为别种文体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将回到史传文学本题上来。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是为其最初萌芽,文学色彩还相当淡薄幼稚。但随之进入了战国的空前繁荣和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以《左传》、《战国策》的面世为标志。史官们虽坚守历史真实,却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故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意故事的情节渲染与细节描写;于刻画历史人物时,突出其音容举止等个性化特征。总的说来,史传文学在强调录实求真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史学品格的同时,再引入想象、细小处虚构等文学手法,力求生动形象,使理性认知与感性激发并重兼具。史传文学作为经典,一直被后人所借鉴继承。
汉代是史传文学的最后一个辉煌发达时期,主要是产生了高耸极顶的绝唱之作《史记》。它于结构体式上锐意创新,突破先秦史传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的编年体格局,而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去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达到高度典型的文学性和历史科学的有机完美统一。其次则是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一代”的《汉书》,但它已开始显露着消解弱化文学色彩而朝历史学靠拢认同的倾向,而且之后的列朝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制。魏晋或可视做史传文学的终结期,尽管还间有杰作面世,然文学与史学分割剥离的趋势渐强愈炽,乃至终成为定局共识,结果是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返原回归,两者歧途而各行其道。从严格意义上说,自此后便不复存在真正的史传文学了。只不过其余波犹未消歇,如杂传散传文学随之继兴,皆沾溉浸润着史传文学的艺术传统和美学理想;至于在散文、戏曲文学、小说诸文体的成长演进过程中,更一直起伏流贯着它的形影精神。
通过前面的述论,我们基本上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和根本。其实,放大些来看,本书又何尝不如此?换个说法,因为主流的腾涌喧荡,才导引注定了中国文学长河的指向走势和壮观景况。另一方面,相关的梁架节柱或主流,也时时给人开启一扇扇窗口与新视点,从这里可以饱览各样艳丽缤纷的美好风光,触发起您继续详细了解、深入探索的兴味。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再因为这幅素描图卷的粗枝大叶、浅尝辄止而感觉遗憾抱歉了。
二○○六年岁末
于济南玉函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