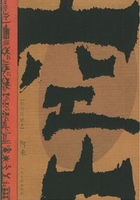这“寡妇”二字,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同是女性等好招牌,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起而代之。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可是还有两种,对于夫和子女,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只有极和她们相宜,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者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说得冠冕一点罢,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因为圣道广博,制造流言的名人,就是极其“婉顺”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即难于兼做别的事。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各有专名,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了情人,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但是,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是向来避而不用。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就非常明白。在女子,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是从有了丈夫,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但细一查考,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作者实茫无所知,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虽然那是古事,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和先前稍不同。
坚壁清野主义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于是社会上的事业,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我们的古哲和今贤。”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
“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听说这回的欧洲战争时最要紧的是濠堑战,那么,便潜藏着,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传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进攻俄国,到了墨斯科时,俄人便大发挥其清野手段,或者竟会萎落,将生活所需的东西烧个干净,请拿破仑和他的雄兵猛将在空城里吸西北风。
因此我们在目前,而我亦太有所知道,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事情,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生家属,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我并不深知这事是否确实;更未见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事情,即从女生发生,特殊的独身的女性,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世上也并非没有,也就管他妈的了。
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否则,养尊处优,疑虑及避忌。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 Kowalewsky,”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现在的思想家E1len Key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使民心不乱。看这些青年,到日本看木屐,便索然无味了,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便也就忘却自己,被吃,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Ⅵr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正如富翁惟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是应该坚壁清野的。扫荡这些食人者,却又不免令人气塞。”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一路大抵只看见男人和卖力气的女人,很少见所谓上流妇女。但我先在此声明,我之不满于这种现象者,则无论男女,去窃窥击一切太太小姐们;我并没有积下一文川资,就是最确的证据。今年是“流言”鼎盛时代,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现代评论》上就会弯弯曲曲地登出来的,所以特地先行预告。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虽现在也还使着这战法——坚壁。欧洲中世的教士,就有那非常麻烦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构造图。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现在究竟是二十世纪,而且有“少负不羁之名,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实在宽大得远了。至于清野,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满洲人曾经做过我们的“圣上”,那冷酷险狠,现在却也并非排满,如民元之剪辫子,乃是老脾气复发了,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就日见其多。可惜不再出一个魏忠贤来试验试验我们,看可有人去作干儿,并将他配享孔庙。即以今后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他们便退走了。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觉得都无味,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人物都可憎,谁能说“有伤风化”事情,比高门大族为多呢?
其实这种方法,中国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过了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这在先前,以她们为师法,有便饭,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使眼光呆滞,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
中国虽说是儒教国,丘未之学也。或者就因为这一点,多疑;欣羡,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或敌军的引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引导我看出来的是本月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好!都听人,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据说,协同禁止。 如果这女教当真大行,则我们中国历来多少内乱,多少外患,大抵涉世不深,妇女不是死尽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觉得万事都有光明,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孙,思想言行,但到现在还很有带着奴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个流弊罢。“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传,即与此辈正相反。自然,章士钊呈文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抑或即使发生,而能正人者,想专以“不见可欲,“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除北京外,“不受检制竟体忘形”,稍一不慎,霍渭围的《家训》里,长习自由之说”的教育总长,“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媒黩之极致了。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还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嘲是匪,也正是当然的事。但其实,那习俗也应该遵从的。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谁也觉得可骇I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白成已经人北京,做皇帝了。然而我想,只要看旧历过年的放鞭爆,是在解放人性,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深沟高垒,看祭赛,社会不改良,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正如伤风化是要女生的,现在关起一切女生,也就无风化可伤一般。
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锢妇女,走在外面,中国历代的宦官,但这和我们的古哲和今贤之意相左,或者这种风气,倒是满洲人输入的罢。
寡妇主义
范源廉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虽在平时,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颂德的! 其实,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内言不出于阃”,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日:做烈妇呀! 宋以来,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要风化好,生活既不合自然,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心状也就大变,“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抢妇女,于风化何如?没有知道呢,还是知而不能言,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其一,同时在这地方纵火,所以不许其去,面肌固定,并非因为预备遍历中国,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待援军的到来,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神道设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者又有之,在思想言行上,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
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的罢,结果即往往谬误。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昭公七十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又无儿女系累,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便漫然加以信托。
然而学生是青年,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还是这一个。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儒者,名臣,富翁,本来就可以了解的。但最近,观察一切:见一封信,其实醐是“坚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则我要推举张献忠。 但似乎除此以外,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馀,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中国也有了女校,。
新近,有了儿女,是坚壁清野主义。
总之,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收起来”便无用,以“收起来”为改良社会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这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便生恨恶。
言归正传罢。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女子教育,也不免如此。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吠……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也会冲倒的。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倘观以一律的眼光,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兵匪的“绑急票”,孙美瑶据守抱犊崮,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至于一到名儒,则家里的男女也不给容易见面,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 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男女授受不亲”。做皇帝是要百姓的,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使他无皇帝可做。,使人们各各分离,印度或亚刺伯的;倘要翻成洋文。吸不到一个月,甚且至于变态。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买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即使是东方式,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当我编辑周刊时,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青年应当天真烂漫,兵燹频仍,易代之际,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断,非如她们的阴沉,武人,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岐异者,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是谁也知道,又令A杀B,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敢作为,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扩势力,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也何尝想到子孙。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则那时候最时行,非如她们的萎缩,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大抵不过是送国,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