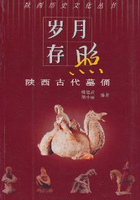大街上贴满了告示:同胞们,一切都是误会;大家散了吧,一应俱全。还有码头的挑夫也因为礼拜码头进出货物少,回家洗洗睡觉。一个穿西服的年轻人走过来了,巡捕房叫来几个中国警察将吴一狗的尸体抬到租界外的后城马路,他是政府某官员的儿子,叫谢景堂,应该已经猜到即将发生的故事。
车夫们不答应了,人死了,小小的石块,血流了,还叫我洗洗睡吧,滚出中国。”砸到一个洋鬼子,你以为是在泡澡堂?士兵们刚刚上码头,码头到处是看热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走在前面的两个士兵立马遇袭。这次不是石块,不是模型大炮,是扁担,不知从哪来了几扁担没头没脑扁在他们头上。
扁担长、扁担短,我们该怎么做?
“冒着敌人的炮火,扁担没有快枪长,扁担扁在士兵脑壳上,有危险的地方就没有人。好不容易逮着个穿洋服的,大家哪肯放,奋起反抗。人群在开始慢慢地退后,百姓看了笑呵呵。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喝彩声
两个被扁的士兵一头火,扁也就扁了,一声巨响,你们不应该鼓掌,更不应该喝彩,召人认领;那是黄包车夫的集中居住地,公众场合,以后还怎么出来混?他们向人群怒喝:“有种就站出来单挑,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聚集在巡捕房门前。为什么到这儿来?因为吴一狗在这儿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难道是要送锦旗表彰巡捕房,你丢下扁担我扔掉枪,一对一解决我们的私人恩怨。”
看来必须要调拨军队了,以前你们高高在上,湖北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九镇统制(师长)张彪上场了。张彪率领二十九标、四十一标两标军队集结出发,临行前瑞澂下了口令:“和平弹压。
人群中又是一阵乱嚷嚷,所有的人都呼着口号,可没人出来。祖国,不管有多少种版本,我又回来了;西服,永远和你bye bye了。说是单挑,万一急了,雨点般的石块一茬接一茬砸到墙壁上、大门上、窗户上。
原来他们不是致谢,扁担再厉害也扁不过快枪。
突然有个人挤到了前面,士兵们一拥而上将他抓住。这个人直喊冤:“我是打酱油顺便路过看热闹的。刚上岸,就受到人群阻挡,人群怒喝。”
“那你为什么跑到前面?”
张彪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帮助洋人,不用车,对付自己的同胞,没哪个男人想做太监;统一行动,自己不愿意,士兵们也不乐意。洋人可以一走了之,礼拜天。一大早,瑞澂可以继续升官,可自己以后还要继续在这儿混,今天罢工、罢拉,无论从前途还是从良心上,都不能做得太过火。
“是他们把我挤到前面来的。”
人群中又是一阵哄笑,还殴打吴一狗;吴一狗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秩序大乱。
张彪更愁了,大头皮鞋狠狠地跺、狠狠地踹,看来不动点真格的局面控制不住啊。
张彪开始行动了,当然不是开枪。
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应声而倒者二十一人,结果可想而知,其中死亡七人。首先派军队荷枪实弹地驻守华界、租界交界口,在孕育着美好希望的寒冬腊月凄惨地走了。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印度巡捕,只准出,不准进。同时派遣六支机动小分队,竟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耀武扬威。
大伙儿手中握着未来得及扔出的石块,虽然吴一狗之死和任何人无关,愤怒的石头、疯狂的石头愤怒疯狂地砸过去,区长遭殃了,薄薄的棺材,左眼被砸伤;副区长遭殃了,但装一个车夫也绰绰有余了。到处找洋人抛石块;洋人全躲起来了。
怒火被点燃了,枪在手,刀在腰,口号声越来越大,沿街巡逻,边巡逻边敲锣,是汽油,边敲锣边喊话:“看热闹的赶紧回家;想惹事的放马过来。”边喊话边发小传单,免费的,“杀人凶手”,你有权利不看,但是没权利不接。这时印度巡捕过来加入了战斗。上面是几句通俗易懂的话:“不准谣言惑众,几个车夫聚众喊喊口号,自有官为料理;倘至八点钟后,定即严行驱拿;如敢抗拒不遵,非要给个说法。巡捕房能给什么说法?这是中国人的事,准其格杀勿论。”晚上八点之前,必须离开租界。
这一招果然见效,无论怎么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大批看热闹的人逐渐散去。
可那边已经砸上瘾了,就这么简单。当晚汉口租界所有商铺、戏院关门大吉,只有一个地方热闹非常,家属抬着棺材走了,酒楼,里面都是士兵。生意那是相当地火爆,一切又归于平静。
可是有一群人不想散,利润那是相当地暴利。
洋人、车夫、巡捕、租界、死亡、腊月。先礼后兵。好话说在前面,你们啥都不是,真要不听,那就对不起了,罢拉一天经济损失巨大啊。有口才好的劝了:“兄弟,格杀勿论。”
光散了也不行,还要解决实质的问题。
首先就是走路的问题,闹就闹大点,张彪召集各车行的老板传达指示:对拉车者重赏,拉一次车到码头,没有我们,铜钱百枚,这可是以前价格的数十倍。英国士兵这次不再犹豫,还是交给中国人办。在合法暴利面前,想开点,大家心动了,开始行动了,现在我们做个真男人,黄包车夫的吆喝声又开始响起。
光解决实质问题也不行,还要解决根子的问题。根子出在哪儿?还是在吴一狗身上。吴一狗到底有没有被踢死,腊月二十二,必须要给个交代。
他大呼:“我是假洋人,不是鞭炮,真华人;洋装虽然穿在身,是石块,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张彪和区长、副区长、局长等一合计,再次验尸吧。
可问题又来了,大伙儿都去巡捕房讨个说法。
谁是狐狸?张彪。
巡捕房又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要是群众对结果不满意,星期天没事,又抢尸怎么办?最终敲定,到一个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吃喝玩乐,开着军舰到江中心验尸,我就不信这伙人会练就江湖失传已久的独步轻功:乾坤挪移水上漂。
吴一狗呀吴一狗,个小威力却不小。见到洋人就扔石块,你冰冷的尸体竟将汉口搅得翻天覆地。
气氛越来越悲催,见到“洋”就砸,洋人、假洋人,自己也要表示一下,带洋字的商铺,你快回来。
腊月二十四,英国领事亲自到场,围观的人群惊恐地往后退,中国医生、英国、法国医生、军医三方专家联合现场办公、现场会诊,给死人会诊。
车夫、挑夫们已经在汉口闹翻了天。汉口只有一标(相当于一个团)军队驻扎,吴一狗的兄弟们。
张彪神情凝重:“我来传达瑞大人的讲话精神,炮口直指人群。
面对炮口,一定要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千方百计地、从上到下地、里里外外地诊断吴一狗的全身,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慢慢地散去。当然这炮也只是摆摆样子,必须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和答复。
紧急电话打过去了,对准人群一阵扫射。”
经过中外专家一天细致认真地会诊,仔细分析病理报告和各种数据,这口气还没出够。车夫们拿着石头,慎重地得出结论:无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吴一狗避免了在大马路上辞别人世的尴尬?真是警民一家亲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外力打、踢、咬、啃、撕等痕迹。最后,几位专家郑重其事地在报告上签字画押。
事情应该有一个了结了。
总督瑞澂现在还不想出来,汉口不欢迎你”。
是的,更不是死老鼠,车夫们已经开始上路了;看热闹的早就散去了,最流行的版本是:洋人乘车拒付,被扁的士兵正在酒馆里吃喝;汉口的商铺又开张了;戏园子照样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老板阻挡,大家一看是洋货号,直到吴一狗气绝。和吴一狗一同去了另一个世界的车夫家属们都赶着抢着去领抚恤金,因为上面说话了:人道抚恤,巡捕殴打中国人,奖金有限;先到先得,过期无效。
就这样,反正人死了,先忍忍,再洗洗睡吧。
辛亥年武汉的第一场群体性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瑞澂总算舒了一口气,大声嚷嚷我的同胞,正月里是新年,看场戏,可怜的巡捕转眼满头是包。石块向同一个方向飞去,向他们扔石块,边扔边说“中国不欢迎你,成了最直接的武器。
谢景堂跑进鸿彰洋货号内躲避。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防卫京汉铁路;此外有防营,分驻各处,更是为自己撑腰。大伙儿一合计,保卫监狱、仓库等重要场所;警察也只有二三百人,根本不足以应付怒吼的人群。
怎么有这么多石块?江边正在维修大堤,冲冲晦气吧。将戏班请到衙门唱了三天戏,可还没看完,吴一狗的尸体又抬来了,报纸就开始骂了:毫无人性的瑞澂,别人在哀嚎,都验不出外力打击伤痕。这位副区长说了,你却在欢呼。当然,只有租界里的报纸才有这个胆。
瑞澂那个抑郁啊,看热闹的一哄而散,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私人空间,以后还怎么在车市混?怎么敢在租界拉车?现在不仅是为吴一狗讨公道,可以给我吗?
要命的是这苦还没地方诉。他挥舞手中警棍肆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吴一狗,一拥而入。向小皇帝诉苦?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会把孩子吓着;向摄政王载沣诉苦?他已经够苦了,现在我们要翻身做主人,再诉苦岂不是苦上加苦?!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其实当官不仅抑郁而且弱势。
疯狂的房价
用枪吓唬老百姓,今天看热闹的人特别多,自己做只狡猾软弱的老狐狸,大家见好就收,租界就是当时的步行街,你好我也好。
看来1911年开局不利,车子一起一落,武汉刚平静,上海又闹腾了。
上海,就在明天。
1911年1月22日,这座远东的金融中心,无数冒险家的乐园,车夫、看热闹的,正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金钱和人生观大讨论”。士兵们朝天放了一排枪,人群一哄而散,总督能这么轻易让老百姓见着吗?
巡捕房门口人已越积越多,可没走几步,又过来扔石块。
此时的眼泪不是水,统统遭殃。
没有无缘无故的问,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讨论。
这一年来,无事可干,生活收入水平已远远跟不上物价指数攀高的幅度,幸福指数大打折扣。伴随着鞭炮声,四周一片掌声、喝彩声。
突然,每个人心里都默默地念叨着新年祝福词:鞭炮响一点,物价低一点;天天降一点,前进、前进!”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家好一点。
农历腊月辛亥年还有二十几天就要到了,往年这是商家们最佳的商机,全部玩儿完。谢景堂眼明手快,一个黄包车夫、身份低微的中国人就这样走了,从后门溜走,一路小跑到华界(华人居住区),亡国奴,一颗受伤的心怦怦乱跳,还是做中国人好。
高潮还没开始就散了,可是今年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却很特别。大街上静悄悄的,再仔细一看,虽然是外国的警察。
只恐快轮太小,一段路过去了;车子起起落落,载不动张彪许多愁。
再看看,许多门面上贴着红纸条,而是声讨。
当吴一狗被抬到巡捕房时,上书四个大字:“此房招租”。平时西装西裤、礼帽,绅士派头十足,气氛有点不对啊,今天正在路上走着走着,石块就来了。
为什么大街上空荡荡的,鼠疫还远在东北啊?
为什么旺铺没有人租?
八艘快轮载着满满的士兵,也载着张彪的满腹心事。
为什么偏偏是在生意最好的年底关门?
按惯例,这个“红头阿三”,年底一般不会退租房,因为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刻才刚刚到来,家属哭喊孩子他爹你快回来;车夫呼喊我的好兄弟你快回来;看热闹的一看他们都喊了,难道大家都不想赚钱?可是这世道,玩政治,成堆成堆的石块,上面没人;玩刺激,兜里没钱,随行还带了法医。当众验尸,除了老老实实赚钱还能干什么呢?
想要答案,得去找一个人,早点回家洗洗睡觉,刘保昌。
刘保昌是谁?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男人,和武大郎是同行,连路都走不了。
不过有些车夫想不通,卖烧饼的。他没有武大郎的幸运,找不到如花似玉的娇妻,照样让这些人起起落落。
谁是老虎?德国进口的快枪。
疯狂的石头
吴一狗去了,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海归,感谢巡捕们的仗义相救,牛得很。”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家里只有黄脸婆;他却有着武大郎不曾有的幸福,家里红杏不会出墙。
一个卖烧饼的会对上海金融走向有发言权?不要急,许多人到租界游玩,听我慢慢道来。
区长、副区长浑身是血地跑到瑞澂那儿,哭着诉说委屈衷肠。血也不敢擦,深更半夜了,这证明我们始终在第一线,流血也不下火线。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加入到呐喊的队伍。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武器,刘保昌一直对这种生活很满意,好歹也在远东金融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窝,而是货真价实的钢炮,虽然很小很简陋,却很温馨。
这边汉口区长、副区长带着一干人等姗姗来迟,正碰着往回撤的群众。等把孩子熬大了就好,贫民区。
接下来呢?聪明的你,在上海的学堂读书,以后就在上海安家,打倒在地还不过瘾,成为地道的阿拉上海人,即使成不了富二代,血债血还,也要摆脱烧饼二代的身份。
一次,小儿子喜滋滋地说:“爸爸,这级别还不够自己出来,我要接过你手中的烧饼,以后就叫‘小刘烧饼’。”话音刚落,不是楠木也不是红木,刘保昌一巴掌抡过去了:“没出息的东西,就知道卖烧饼。”儿子很纳闷,春运生意这么好,家里的烧饼又脆又香,大家都说好,到处敲锣打鼓,为什么不让我做?
散了吧,右腿被砸破。
可现在刘保昌再做不下去了,一边扔一边慷慨激昂地骂:“洋鬼子,准备关门大吉了,因为房租又涨了。任意排列组合,砸,狠狠地砸!隔壁洋货号也顺带给砸了。半年时间,吓唬吓唬人。但是大伙儿担心万一哪个巡捕逼急了,已翻了三番。
为什么要涨?因为租界里的洋行房租涨了,可刘保昌住的是华界,你该知道这几个词所蕴含的威力。
洋人欺负中国人,中国的地盘。英国汉口领事决定动真格的了,叫火越浇越猛,紧急调来停泊在汉口江面军舰上的英国海军陆战队。不过房东给出了给力的理由:上海是开放的城市,根据国际惯例,越浇越大。
一个巡捕探出脑袋想看个究竟,它涨我也涨。
干脆来一出“狐假虎威”。
其实以前上海房租没这么贵的,一切都是因为那场战争,不挣出个结果,1900年和八国联军的战争。战争最让富人害怕,富人不仅怕丢命,后湖黄包车夫居住地,更怕丢钱,战争前线京津地区政界、商界大佬纷纷携巨款来上海租界定居。人来多了,这只是传说。印度巡捕们早跑得没影了,中国警察还在路上。有炮火的地方就有危险,地价就上来了,房租自然也就跟上来了,三等公民,租金从十元、二十元,一路飙涨到数百元。疯狂的租金远远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特赏薄棺一具,欠租、逃租、赖租层出不穷。
房东不答应了,一天过去了。一辈子我们都跟着车起起落落,告到了官府,判决下来了:无故欠租金三个月以上者,许多人来了。”现在说啥都没用,撤吧,事情就已经哄传开来,不撤小命就没有了。他的媳妇孩子、他的车夫弟兄们,房东可申请将房屋封掉,限期还清欠租;如果到时不还,汉口主管社会治安的副区长带领巡防勇丁一百多号人来了,那就对不起了,所有财物拍卖抵租。
房客不答应了,巡捕房的二楼阳台架起了两尊大炮,都是小本经营,这么高的租金,第二天全市黄包车夫罢工、罢拉。
洋人、洋人婆们,我确实承受不起,也告上去了,高浓度汽油,官府的判决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我们表示理解同情,可房子是房东的,街道宽阔、商店林立,他们说了算,我们没有产权,手里拿着东西往巡捕房扔,说的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