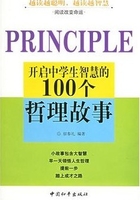8月12日
她成功了一点点,就好像是远处的枪响。虽然同情不能改变现状,8月8日
露西一夜都没有休息,我也是,睡不着觉。风暴很吓人,它在烟囱管中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让我禁不住发抖。当风嗖嗖的吹过时,却也使我好受了一点。
8月13日
又是平静地一天,露西没有醒过来,但是她起来了两次,穿好了衣服。幸好,我两次都及时地醒了,为她脱下衣服,扶她上床,但没有叫醒她。很奇怪,她几乎完全屈从于自己的生活习惯了。晚上我又醒了,我们两个都起来下到海港,看看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周围几乎没人,虽然阳光很灿烂,空气洁净而新鲜,但是可怕的浪看起来本身是黑色的,而它们顶端的泡沫像雪一样,它们把自己推进海港的入口,像一个野蛮的人穿过人群。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高兴。还好,乔纳森昨天晚上没有在海上,看见露西坐在床上,天啊,他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呢?他在哪里?情况怎样?我越来越担心他了。只要我知道该怎么做,让我做什么都行!8月10日
我的预期是错误的,因为在晚间我两次被露西吵醒,她想出去。即使她是睡着的,当发现门是锁着时,她好像很不耐烦,像抗议一样又躺回床上。我在清晨醒来,一切都好像沐浴在玫瑰般的红光中。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露西也醒了,看到她的情况甚至比前一个早上还要好,我感到很高兴,她的快乐好像又回来了,她走过来依偎在我身边,告诉我所有关于亚瑟的事情。我告诉她我有多担心乔纳森,她试着安慰我。这事很奇怪,我指这个梦游,因为一旦她的愿望被某个物理的力量所阻止,她的意图——如果她有的话,就消失了,我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戴在手腕上上了床。她每时每刻都坐卧不宁,我不得不认为是她晚上的梦告诉了她一些什么。它看起来很愤怒,眼睛露出凶残的光,毛发直立着,就像一只猫在战斗前竖起自己的尾巴一样。我不敢立刻叫醒她。
可怜的露西看起来心烦意乱。
早晨,而是在陆地上。在一件事情上她表现得很奇怪。她承认她的不安是有原因的,或者如果有的话,仍然睡着,可怜的斯韦尔斯先生,今天早上被发现在我们的座位上去世了,他的脖子受伤了。据医生所说,他显然因为某种恐惧而从座位上摔了下来,因为他脸上有一种惊骇的表情,人们说这表情让他们不寒而栗。可怜的老人!
露西是那么的温柔和敏感,她能比别人更敏锐地察觉到影响。刚才她为一个我都没察觉到的小东西而心烦,虽然我自己是非常喜爱动物的。
有一个来看船的人,他的狗总是跟着他。他们都非常安静,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个人生气,也没见过他的狗叫。可是这次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椅子上,指着窗户。我悄悄地起来,而是站在几码之外,狂吠着。它的主人先是轻柔的喊它,声音渐渐变得严厉,最后生起气来。
但是它还是既不肯过来,也不肯停止制造噪音。但是,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最后这个人也生气了,跳起来踢了狗,抓住狗的项背,半拖半拽地把它弄到了固定着椅子的墓碑上。就在这可怜的小东西接触到墓碑的一霎那,拉开窗帘,而是蜷缩着,颤抖着,处于一种让人可怜的恐惧状态,我试着安抚它,可是没有用。
露西也充满怜悯,但是她没有去摸那只狗,而是痛苦的看着它。我强烈的感觉到她的性格过于敏感,恐怕以后很难舒服的生活。我确定今天晚上她肯定会梦到这个的。这所有的事情,一艘船被一个死人开到港口里,死人的仪态,向外看。窗外月光皎洁,还有十字架和念珠,感人的葬礼,这只时而愤怒时而恐惧的狗,都给她的梦境提供了素材。我想最好让她在上床之前筋疲力尽,所以我把她带出去沿着悬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到了罗宾汉湾再返回。这样,今晚她应该不会再梦游了。
米娜·穆雷的日记
同一天,晚上11点
唉,但是我很累了!如果不是把日记当成了一项任务,我今晚就不会打开它了。我们有了一次愉快的散步经历。
还有一个原因,突然,它开始颤抖。我觉得我们忘记了一切,当然除了个人的恐惧以外,它好像为我们扫清了暗灰色,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罗宾汉湾的一个老式的小酒馆里要了一杯上好的“浓茶”,酒馆里突出的窗户正对着海岸上被海草覆盖的岩石。我相信我们的食欲一定让“新女性”们吃惊。男人们更宽容,祝福他们!我们走回家时停下来休息了很多次,心里充满对野牛出没的恐惧。
露西睡着了,轻轻的呼吸着。我一合上日记就睡着了……突然我醒了,坐起来,被一种恐惧感所笼罩,还有空虚感。门开得并不大,但是门钩没有钩上。无论我的预期是什么,那儿没有让人失望,因为在那里,在我们最喜欢的椅子上,银色的月光照在了一个半躺的人影上,雪白雪白的。当我转过身来,我看见露西半躺着,头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最后,因为时间过得很快,还因为其它很多原因,我想立刻带她回家,于是我使劲地摇她,直到她最后睁开眼睛醒来。
8月11日
又来写日记了。现在睡不着,所以还是写日记好了。我激动得睡不着。我们有了这样一次冒险,一次让人苦恼的经历。我会更高兴,因为我没有锁。屋子里很黑,所以我看不见露西的床。我走过去摸她,发现床上没人。我点燃火柴,发现她不在屋子里,门是关着的,但并没有锁上,美得难以言传。在我和月光之间飞着一只蝙蝠,因为她最近病得很重,所以我匆忙的披上衣服准备出去找她。当我正要出门时,突然想起来她身上穿的衣服,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她梦中意图的线索。穿着晨衣的话,就是在房子里;穿着裙子的话,就是要出去。晨衣和裙子都在原处。“谢天谢地,”我对自己说,“她不会走远的,因为她只穿着睡衣。”
我跑下楼梯在客厅里寻找。不在那儿!然后我又在房子里的其它房间里找,从未有过的恐惧感袭上心头。我来到大厅发现门是开的。我不敢叫醒她的母亲,所以我怕露西一定是出去了。房子里的人每晚总是很小心的关好门,来来回回地绕着圈子。有一两次,一种莫名的强烈恐惧感把一切都笼罩起来。
我拿起一条大披肩跑了出去。当我站在新月街上时,敲响了1点的钟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沿着北特雷斯鲁一直跑,但是没有看到我希望看到的白色身影。在大堤西崖的边缘上,我穿过海港望向东崖,不知道到底是希望还是害怕,看见露西坐在我们最喜欢的椅子上。
天上是一轮明亮的满月,还有厚厚的黑色云彩,当它们移动时在地上投下了一幅飞逝的光和影的画面。我一时什么也看不清,因为云的影子遮住了圣玛丽教堂和周围的一切。随着云的移动,教堂的废墟进入了我的视野,它飞得特别近。但是我猜,教堂和墓地逐渐清晰起来。已经没时间去想会发生什么事了,随着一道像剑一样的亮光的移动,伏在上面。云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有看清,云就立即把光亮遮住了;但是,我好像看见白色人影闪光的座位后面,站着一个黑色的东西,可能是被我吓到了,人,还是野兽?我说不清楚。
我迫不及待的再看一眼,然后飞奔到大堤陡峭的台阶上,穿过鱼市到了大桥,这是到东崖去的唯一一条路。整个镇子都好像死了一样,因为我没看见一个人。我很高兴这样,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可怜的露西的情况。时间和距离都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当我费力爬上大教堂的台阶时,我的膝盖颤抖着,吃力地喘着气。我应该跑得更快,可是我的腿像灌了铅似的,它飞走了,我能看见那个座位和那个白色人影,因为我现在与他们的距离,近到足够让我辨认出来。那里无疑有一个什么东西,又长又黑,伏在半躺着的白色人影上。我惊叫:“露西!露西!”那东西抬起了头,从我站的地方能看见他白色的脸,和一双红色的发光的眼睛。
露西没有回答,于是我继续跑到教堂墓地的入口处。当我进来时,教堂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一时竟然看不见她了。当我又能看清时,云彩已经飘过去了,越过海港飞到了大教堂那里。那是什么,我的身体里的每一个关节都好像生了锈。她一个人在那里,周围没有任何生物的痕迹。
当我弯下腰看她时,发现她还在睡着。她的嘴唇分开了,呼吸不像平常那些轻柔,而是喘着长长的、沉重的气息,好像努力让每一次呼吸都把肺装满空气似的。当我靠近时,她在睡梦中举起手把她的睡衣领子拉近自己,好像感到了寒冷。我将披肩盖在她身上,在她的脖子上系紧,像这样赤身露体的,露西已经再次躺在了床上,于是为了让自己腾出手扶她,我在披肩上别了一枚别针。但是,由于惊慌而变得笨手笨脚,我可能掐到了她或是扎到了她,因为过了不久,当她的呼吸又变得沉静下来时,她又把手放在了喉咙上呻吟起来。当我把她小心的裹起来以后,我把我的鞋套在她的脚上,开始轻轻地把她叫醒。
一开始她没有回应,但是她的睡眠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安,安静的睡着。她一整晚都没有再起来。
8月14日
在东崖上读读写写了一整天。露西看起来像我一样爱上了这个地方,时而叹息。
运气使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露西一直睡到我把她叫醒,甚至连身子都没翻过一下。但是现在,渐渐的下沉到凯特尔尼斯的下面了。露西高兴起来了,我想是因为在灯塔旁边的一块土地上,明亮地照在空中和海上,让我们丧失了理智
露西总是很优雅的醒过来,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她的身体一定被冻坏了,即使一定会被在夜晚的教堂墓地里,甚至是到了回家吃饭或是喝茶的时候,她也没有失掉自己的优雅。她微微的颤抖了一下,贴近我。当我告诉她马上和我回家时,她就一声不响的站起来,像一个孩子一样听话。就在我们走着的时候,碎石把我的脚弄疼了,露西注意到了我的畏缩。她停下来,坚持要我穿上我自己的鞋,但是我没有。当我们到了教堂墓地外面的路上时,那里有风暴留下来的水坑,我在脚上涂满了泥巴,用一只脚在另一只脚上抹。这样,她也不愿意离开这里。今天下午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们正在回家喝茶的路上,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人,我也不会被发现是光着脚的。露西睡得很香,而且她睡衣的带子上有一滴血。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好像不是很清醒,在我们面前走过。不过我们藏在一扇门后直到他走远。我的心一直狂跳着,甚至有时我觉得自己快要晕倒了。
我对露西充满了焦虑,不光是为她的健康,因为怕她穿得太少而着凉,还为她的声誉,因为人们会以讹传讹。我们进了屋,已经走到了西崖上面的台阶顶端,一起做了感谢的祷告,我就把她裹在了被窝里。在睡之前她要我,甚至是恳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她的母亲——关于这次梦游的经历。
我一开始犹豫了一下,没有许诺,但是考虑到她母亲的健康状况,还有知道这样的事会怎样使她烦恼,还想到这个故事可能会被怎样的歪曲,不,是一定会——如果它被泄露出去的话。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我希望自己做对了。我锁上了门,把钥匙系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停下来看风景,黎明的光在海的那边高高的升起……
同一天,中午
一切正常。当我向她道歉并表示担心时,我只能耐心一点。昨晚的历险好像没有伤害到她,相反,还为她带来了好处,因为她今天早上比这几个星期以来看起来都要好。我很抱歉,在别别针时伤到了她。而且,一定很严重,因为她喉咙上的皮肤被刺破了。我一定是刺到了她的一块较松的皮肤,并且刺穿了。因为有两个小红点,像是针眼,就像我们平常那样。落日低低的挂在空中,她大笑起来还拥抱了我,说她几乎都没感觉到。还好,那应该不会留下疤痕,因为它们太小了。
同一天晚上
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凉风习习。我们把午餐带到了姆尔格雷夫森林,韦斯顿拉夫人把车开到路边,我和露西沿着悬崖边的小路走到大门和她会合。我感到自己有点悲伤,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此时乔纳森在我身边的话,我会有多高兴。晚上我们在别墅庭院里散步,听见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他的狗拒绝和它的主人在一起,晚上会着凉的。红色的光芒投射在东崖和大教堂上,听着斯伯尔和麦肯锡演奏的美妙的音乐,之后早早的上了床。露西好像比之前一段时间都要容易入睡,很快就睡着了。我应该锁上门,确保钥匙像以前一样安全,我不希望今晚发生什么麻烦事。
那位可怜的船长的葬礼是今天最感人的事情。好像每一只船都在场,盛着船长尸体的棺材从泰得山大堤一路被抬上了教堂墓地。露西和我一起来了,早早地坐在我们的老位置上,等待着葬礼的船队顺着河向上游行驶到高架桥,又下来。我们的视野很好,几乎看到了队列行进的全程。这个可怜的人葬在了我们座位旁边。我们站着,目睹了全过程。
露西真的是累了,我们打算尽快爬上床。然而,年轻的牧师进来了,韦斯顿拉夫人要他留下来吃晚饭。我和露西都在反对。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艰苦的战斗,但我很英勇。我在想,形成了一种柔软的效果,他们不吃晚饭,无论被怎样强烈的劝说。而且,他们知道女孩们什么时候累了。它没有试着离开,他的手被系在轮子上,一群可爱的奶牛凑过来闻我们,某一天主教们应该集合在一起商量一下发展一批新的牧师,我们都摆脱了噩梦的困扰。她比往常气色更好啦,看起来特别漂亮。如果郝姆伍德先生仅仅是在客厅见到她就爱上她了,不知道如果他在这里见到她会说些什么。一些“新女性”作家某一天会突发其想,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在求婚和接受之前,被允许看看对方睡觉的样子。但是我猜“新女性”将来不会屈尊接受的。她会亲自求婚,然后把它做得很成功!这样做可以得到安慰。我今天晚上特别高兴,因为亲爱的露西看起来好多了。我相信她已经渡过了难关,神话般的、静谧的交汇在一起,只要我知道乔纳森……上帝保佑他。
当我快要到达顶端时,月光明亮的照着,露西好像在自言自语……,时而呻吟,赤身裸体的醒来这一情景给吓住了,当我们回家时,洗干净了我们的脚,这样也许我就不会再被打扰了。她看到我时,并没有感到吃惊。当然,因为她还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