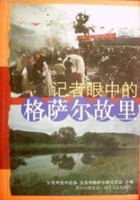黑格尔把战争看做是国家强大的内在活力。他写道:“在和平时期,市民生活不断扩展;一切领域闭关自守,久而久之,人们就腐化堕落了,他们的特异性也愈来愈固定和僵化了。但是,健康需要躯体的统一,如果一切部分各自变成僵硬,那就是死亡。”“战争的结果,不但人民坚强起来,而且本身争吵不休的各民族,通过对外战争也获得了内部安宁。”在黑格尔看来,战争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它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在战争这一环节中,特殊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平静使潮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或者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黑格尔承认“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他看来,历史巨人在前进时会踏坏无数无辜生命的小草,但它义无反顾。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划分为四种王国即四个阶段: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
罗马帝国灭亡后,世界中心转移到日耳曼世界,世界历史达到了“最高精神”,不再向前继续发展了。日耳曼民族的使命就是做基督徒原则的使者。基督教中超感官的自由精神和基督教教义所体现的“绝对自由”的原则,只有到了日耳曼阶段才能实现,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内部成熟之后,才全力向外发展。日耳曼人刚好相反,他们从自身涌出来,弥漫泛滥于世界上,在前进途中使各文明民族的那些内部已经腐朽和空虚的政治构造屈服。然后他们的发展才开始,被一种外族的文化,一种外族的宗教、政治和立法煽动起来”。“因此,在表面上,日耳曼世界只是罗马世界的一种继续,然而其中有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由之而必须更生。”在黑格尔看来,在他生活的时代,从日耳曼“自由精神”的原则产生了“理性”的各种普遍规律,成为世界的“旌旗”,将人类“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黑格尔的最后结论是,路德教是一切宗教的最高形式,德意志的浪漫艺术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的顶峰。因此,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其他民族只能起从属的作用。
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至上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对后来的**主义产生深远影响。对此,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中写道:“德意志上帝,大德国悲剧的这个阶段出现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国家学府的大课堂里,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刻在19世纪的进门柱上。由于有这样的传统,今天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徒子徒孙们,为什么不能欢呼他们的条顿领袖呢?”
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开设的一个课程。他把宗教看做一种认识方式,认为它是以表象认识绝对。他排除人格神,排除对神的盲目崇拜和对神的依赖感,而要求用思维把握神。黑格尔从来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的欺骗,认为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决。人对神的观念同人对自己的观念相应,这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
黑格尔集以往西方伦理思想之大成,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伦理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黑格尔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部分,其中心是揭示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他通过对法、道德、伦理、自由理念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证,表明了自己的义利观。
他承认行为的目的是利,但利与法的结合才是善。他的结论是:
“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关怀自己的福利,而且关怀普遍性质的福利。”他还论证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现实活动表现为需要、劳动和享受三个环节,个体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既是自己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是对其他个体需要的满足,每一个体满足自己需要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因此,他人和社会离不开个体,个体也离不开他人和社会。黑格尔论证了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转化和统一,强调了“他们为我,我为他们”的精神,“一条往东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往西的路。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这就是典型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认识论哲学正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为核心的。黑格尔认为,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感性、知性、理性。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端,是对事物的直接的低级性认识,得到的还只是关于事物的混沌表象;知性认识是对事物的间接性抽象认识,是经由推论对事物各部分进行的单独认识,其特点是“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理性认识则是整体的把握事物的方法,其特点是认识到概念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对立双方是共处于统一体之中的。
黑格尔认为知性认识虽是通向理性的必要阶段,但却是一种不足取的孤立的、片面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而只有理性认识才能得到真理,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只有达至理性阶段,认识才能超越知性,由片面的、抽象的认识上升到全面的、具体的、普遍性的认识。如果说,知性认识看到的还只是事物的矛盾,而理性认识的目的正在于化解矛盾。
黑格尔还明确指出,与知性思维方式相关的是独断论,“独断论坚执着非此必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玄思的真理包含有这些正面的规定自身联合进来的全体,而独断论则坚持将各分离的规定,当做固定的真理。”“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主要在于坚持孤立化的、片面的思想规定;反之,玄思哲学的唯心论则具有全体的原则,表明其自身以统摄抽象的知性规定的片面性。”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玄思”即理性思维,也就是被马克思赞誉为黑格尔思想精华的“辩证法”。
黑格尔内容深刻而又被客观唯心主义思辨结构严密束缚的哲学经历了历史的长期消化过程。20世纪以来,黑格尔哲学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黑格尔研究成为国际现象。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发挥,一直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对立的倾向,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学派都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黑格尔那句最著名的名言并不是说,凡现存的,一切无条件地都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属于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恩格斯举例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君主政体的存在已是不现实的,不合乎理性的。这就必然要发生革命,革命成为“必然”的东西,这才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
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出生于欧洲的走廊——但泽。他行为粗鲁,早在年轻时就因为他祖母的疯死和父亲的自杀而看破红尘。他虽然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母亲(一位那个时代颇有点名气的小说家)的智慧,但没有享受到什么母爱。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纵情于声色犬马,消耗了大量的才气和精力,影响了他作为哲学家的事业和发展。他对自己的天才一直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称颂而耿耿于怀。他一生中的不少时光,都是在一种没有祖国、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关怀、没有爱的孤独中痛苦度过的,他的有关“世界就是意志”的哲学便是在他的痛苦的心灵折磨中诞生的。
他高扬起意志的大旗,对长久以来盛行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理智、理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说:“意志就是长期寻求而屡寻不获的‘物自体’,即一切事物内部终极的实在和隐秘的本质”,“性格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性格也是意志和态度的持续,而这些就是意志。甚至肉体也是意志的产物”,“意志仅仅是我们心灵的外表,我们对于心灵正如我们对于地球一样,不认识内部,只认识外表”,“理智有时似乎可以引导意志,但是仅仅像一个向导引导他的主人一样”,“逻辑是没用的,没有人靠逻辑说服过任何人,连逻辑学家也只是把逻辑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已。要说服一个人就必须迎合他的自身利益,他的欲望,他的意志”,“连记忆力也是意志的奴仆,最容易犯错误的人莫过于仅凭思考行事的人”等等。
叔本华从小孤僻、傲慢,喜怒无常,并带点神经质。一次,一个老妇人在他门外与人聊天,打扰了他的安宁,他竞于盛怒中将老妇人推下楼,跌成重伤。他是一个极度自尊,以自我为中心,孤芳自赏的人。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安静,竞终身未娶。叔本华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仰慕康德。在他的书斋里,有一个康德的半身雕像和一尊铜佛。除起早这一点而外,他在生活方式上尽力模仿康德。他对自己的哲学也极为自负,声称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会震撼整个欧洲思想界,然而他的著作却常常受人冷落。在柏林大学任教时,他试图和黑格尔在讲台上一决高低,结果黑格尔的讲座常常爆满,而听他讲课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超过三人,最后不得不暂时离开大学讲坛。
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而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他为这部悲观主义巨著做出了最乐观的预言:“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其他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他竟至于说其中有些段落是圣灵口授给他的。然而,该书出版10年后,大部分是作为废纸售出的,极度失望的叔本华只好援引别人的话来暗示他的代表作,他说这样的著作犹如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你不可能在镜子里看见天使。
叔本华哲学是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过渡的最后一环,也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端。叔本华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他对黑格尔大加抨击,甚至曾把黑格尔骂作“江湖骗子”,并创立了与之抗衡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来寻求新的出路,提出了生存意志论。
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主要源于康德,特别是康德的关于意志高于理性的思想。和康德一样,叔本华把世界分为“自在之物”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不过他认为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即是“意志”,整个现象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在他看来,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的根源就是求生意志。这种意志是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的基础。人和动物的肢体、器官和皮毛,植物的根系和枝叶等都是意志的表象。
意志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质,它以自然力的形式表露于外。他认为这个身体的全部存在,以及它的各种机能的总和,只不过是意志的客观化。意志在各种无机物中表现为各种盲目的自然力,在动植物中表现为生命和繁殖,在人类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理念或观念。叔本华指出,康德分裂现象和物自体是错误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就是表象同意志的关系,都是不可分的。
叔本华把理性看做意志的奴仆和工具,认为人的认识是生而为意志服务的。但人也可以作为纯粹认识主体摆脱认识为意志服务的桎梏,而进入无我(即失去了意志)的审美境界。叔本华认为:世界的一切都为着主体而存在,现象的世界与人的关系是表象和表象者的关系。意志没有可见性,也没有客观性,只是一种“不能遏制的盲目的冲动”。
叔本华断言,是意志决定行动,而不是理性决定行动,理性是阻止不了行动的;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即意志),只有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惟一的途径;只有依靠神秘的洞察,才能领悟意志的本性。叔本华曾说过:“人类虽然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许多事情,不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叔本华研究过印度哲学。他认为,不是依靠科学或哲学,而是依靠神秘的洞察才能领悟意志的本性。
在伦理思想上,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求生意志,其表现是不可遏制的、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和欲求。个体意志排斥和力求摧毁其他一切障碍,人间必然发生竞争,由竞争发生永久性的相互仇视和残杀。在他看来,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求、竞争和痛苦,不幸是一个普遍法则,现世的享乐是虚幻的,人生只是一场梦。悲剧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能改变人生的不幸,而在于把人生的不幸揭示出来,使人认识到人生是一场噩梦,无可留恋。
在叔本华看来,生育是罪恶,而性欲是最大的耻辱和罪恶。一个人所感受的痛苦与他的生存意志的深度成正比。生存意志越强,欲求越多,人就越痛苦。同时,随着认识的日益明显,意识愈益加强,痛苦也随之增加。
一个人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他就愈痛苦;天才人物最痛苦。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落在痛苦的手心里。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解脱痛苦之道有三:一是佛教的涅磐,二是哲学和道德,三是艺术。
遏制欲求——尤其是情欲,否定生存意志,是摆脱痛苦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哲学沉思和艺术欣赏来暂时解脱精神痛苦,尤其是音乐。音乐的曲调显示了意志的最神秘的部分,音乐刻画了激情、企求和意志的运动。他最崇拜贝多芬的交响乐,认为贝多芬的交响乐是世界本质的忠实而完善的反映,从中可以领悟到人类的各种痛苦和感情。但叔本华认为,最根本的解脱痛苦和不幸的办法是信仰宗教或死亡。
通过宗教的神明否定个人意志,弃世绝欲;通过死亡达到“不可动摇的安宁”和“寂灭中的极乐”。他反对一切理想观念和普遍义务,强调同情心是道德行为的最坚实和最可靠的保证,是最重要的德行基础。
只有遏制私欲和发扬同情心,才能遏制人类的相互残杀。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对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成为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思潮的重要渊源。
尼采对生命本身的肯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就是他自身。思想在他的话语中,他的话语保存在他伟大的著作中。尼采的思想在如下几个问题中得到了体现。
一是酒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