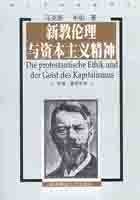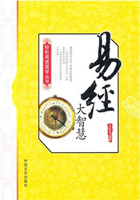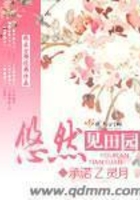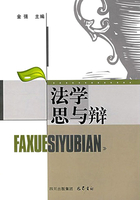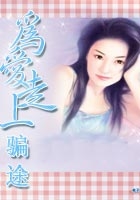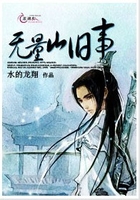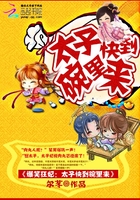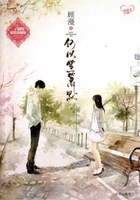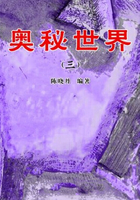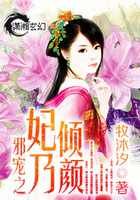这个神话以隐喻的方式暗示,灵魂是一些不纯粹的理念,包含着向往身体的因素(“顽劣的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虽然是一种堕落,但却是符合灵魂状况的堕落,具有某种必然性。灵魂在未跌落之前,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包含着天赋的知识。灵魂在附着身体之后,由于身体的干扰或者“污染”,忘记了过去曾经观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只有通过学习,它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理念。
柏拉图说:回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由观看、触摸或其他感觉来引起,尤其是观看。因此,虽然我们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理念,但是认识理念却又必须依靠感觉经验。换言之,感觉在对理念的回忆中具有某种诱导的作用。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分为突发与渐进两种形式。突发形式表现为疯狂,那是一种忘我的直观状态。当灵魂看到尘世的美,便回忆起真正的美,它感到翅膀正在生长并且急欲展翅高飞,把下方的一切置之度外,全然不顾,于是被世人认作疯狂。其实这是最高级的最佳状态,爱美的人分有这种疯狂,便被叫做钟爱者。渐进形式表现为理性的进展。它的步骤是这样的:“从显而易见的美开始,继而为了最高的美而上升,就像在梯子的阶上一样,从一进到二,从二进到所有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最后从学问到那支研究美自身的科学,最终知道美的本质”。
柏拉图是西方理智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灵魂回忆说,却是要通过“疯狂”来拯救人类。而“疯狂”,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实现的。具有讽刺性的是,直观,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最终导向了神秘主义。我们前面说的毕达哥拉斯,这里的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到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寻找。
在西方,理性总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要前提正确,论证过程严谨,得出的结论肯定就是正确的。因此,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但是,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就这样,在西方的理性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会立即坍塌。
就这样,理性走到尽头,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信仰。而科学传统,也最终屈服于神秘主义的宗教传统。这个命运,好像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上帝根本就无法认识,唯有通过神秘的体验才能去亲近。
七、花园里的奇迹
奥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在信仰的基础上去理解”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把对上帝的信仰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但我们所不了解的是,这位基督教的圣徒,在早年的时候却是一个恣情纵欲的浪子。据说,他17岁的时候就交了女朋友,18岁就有了私生子。
奥古斯丁虽放纵于情欲最早,但追求真理也觉悟最速。他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是哲学史上有名的“花园里的奇迹”。他在《忏悔录》里回忆说,某日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散步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罪重重地压在心上,便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之下,不住地叹息流泪。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喃喃自语:“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过了会儿,他呼喊起来:“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他的哭声在空旷的花园里回荡。
正在这个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好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候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正击中了自己的要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暗笼罩的疑云”。
几天后,奥古斯丁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米兰国立修辞学教席,离开他年轻的未婚妻,决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上帝。公元387年复活节,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了基督教。此后,他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公元395年升任主教。在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组织修会、反驳异端异教。奥古斯丁在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死于希波城沦陷之前。他去世之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从此不再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奥古斯丁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在他这里,古希腊以思辨为主导的理性哲学开始与以信仰为标志的基督教教义发生融合。而且,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信仰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个“花园里的奇迹”。奥古斯丁,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投向上帝,靠的不是理智的思辨,而是《圣经》的启示。所谓的启示,也就是佛教上讲的“顿悟”,恍然开悟,放下屠刀,浪子回头,立地成佛。在这里,思维是跳跃的,而不遵循理性和逻辑的严格推理。
信仰和理性的联姻,哲学和宗教的结合,在西方社会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基督教中的“天堂”,还是哲学家思辨出来的“理念世界”,都是现实此岸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彼岸世界。只不过,前者是灵魂朝向的地方,后者是理性寻求的对象。对基督教而言,灵魂是永恒的,肉体是短暂的,因此灵魂高于肉体。而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智主义者而言,理念是永恒的,现实是短暂的。因此,理念高于现实。不同的领域又对应不同的认识能力,所以,理智又高于感觉。基督教宣扬的是“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基本教义是:“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而柏拉图主义强调的是理智的高贵和感觉的低贱。他的基本主张是:要获得真理,必须抛弃意见;要运用理智,必须抛弃感官。
如此一来,肉体与灵魂、天堂和地狱、此岸与彼岸、今世与来世、有限与无限、感觉与理智、理念与现实之间就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人,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唯有靠信仰和理智才能不断地朝向那个圆满的世界,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因如此,后来的很多教父哲学家干脆要求放弃理性。理性能做到的事情,信仰也能做到。而且,神启的知识比理性的知识更简洁,更直接。何况,信仰总归是没有错的,一旦理性和信仰发生冲突,出问题也是人的理性,而不是信仰。
八、世界竟然存在
有人曾经让维特根斯坦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维特根斯坦没有说话,沉思之后,他在纸上画了两个符号:一个是“?”,另一个是“!”。
这个人不得其解,让维特根斯坦解释这两个符号的意思,维特根斯坦于是说了那句非常绕口但又非常著名的话:“令人感到惊讶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世界是如何存在的?这是一个“?”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科学家的事情。科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研究世界上的事物怎样关联,怎样相互转化,并从这种关联和转化中总结出规律,而后再进行一种理性的描述。正是科学,让我们眼前这个繁杂纷乱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正如诗人薄柏对牛顿的评价:“自然和自然律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
但是,无论科学如何发展,知识如何延伸,人类永远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竟然是你知道得这个样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让我们永远感到神秘的是:世界竟然存在!
“竟然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身,不是指一种种现象、一个个事实,而是指所有现象、事实的总和,即世界或宇宙的整体。把世界当做整体,设问世界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就已经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变成宗教问题了。因为它超出了科学的理性限度,超越了空间和时间,涉及到从无生有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我们的认知之外了。对于这个问题,人类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对整个世界仍然需要一个态度或者信念。相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仅此而已。
很多事情到了终极处,最后也许只能是一个态度、一个承诺。因为我们认知是如此的有限,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相信有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外在客观世界,是一切科学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立、客观的世界存在?这个问题是我们回答不了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人的眼睛。如果没有人类,没有这双眼睛,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荒诞的。因为没有人类,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出承诺,而无法去论证。
今天的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科学精神,把科学程度的高低看做文明的标志,把科学看成是迷信、宗教这些死敌。也许看了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我们才真正知道科学和宗教在源头上还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翻开西方的科学史,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科学的发展历程总是伴随着宗教的庇护。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莱布尼茨也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正因如此,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大多也都是宗教徒。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
正是出于对这个神秘世界的敬畏,正是出于“这个世界竟然存在”的惊讶,西方的科学家们总是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转变成对科学的献身精神。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利亚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安徒生在其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毁灭,否则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皈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因为有了那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西方的文明史上才演绎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这种智力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乐趣,更多的还是一种安身立命的非理性信仰。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人有思维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种的根本所在。但是,人不但是社会的人,还是自然的人,因此,人和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人和自然中的其他物种都是从同一个遥远的祖先那里进化出来的,它们都依靠“自然母亲”的哺育才得以成长;在进化的过程中,它们不仅相互竞争,也相互支撑;只有那些能够对其他物种的生存产生助益的物种才被“自然母亲”选中并得以生存下来。因此,从起源上看,人并不比自然中的其他物种高贵。从更宽广的宇宙观点看,地球不过是茫茫宇宙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类和其他物种都只是这叶扁舟上的乘客或过客,它们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存则同存,亡则俱亡。人类只有与其他物种同舟共济,才能使地球这叶小小的扁舟长存于宇宙海洋中。
一、宇宙大,还是人的思想大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科学家在进行一场关于天文学的演讲时,一个老妇人站起来反驳说:“你说的不对,这个世界是由一只大乌龟驮着的。”科学家问她:“那么,这只乌龟又在哪里呢?”妇人微笑着说:“是由一只大些的乌龟驮着,当然,它的下面又会有一只更大的乌龟……”
故事里无限乌龟的说法虽然让很多人觉得很可笑,但它却是人类最初最朴素的一种宇宙观。人们对宇宙的探究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个宇宙是一个水晶球,地球则位于这个水晶球的中心,各种行星、太阳和月亮都镶嵌在水晶球上。之后的托勒密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和提高,完善了“地心说”并使之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直至哥白尼“日心说”的出现。在东方,人们也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宇宙观,从“盖天说”到“浑天说”再到“昼夜说”等等。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认识宇宙的热情始终不减。